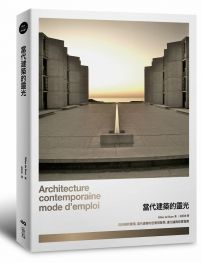作者序
凡事總有第一次。
我十歲那年,偶然間晃到巴黎的弗日廣場(Place des Vosges),當時是1950年代初,地上還舖著鵝卵石,車痕斑斑,龜裂處處,一副快要倒塌的模樣,還沒變裝成今日的雅緻小廣場,但我不知怎麼搞的,竟然對它一見鍾情、癡迷著魔、無法克制。一次永生難忘的經驗。特別是,當時我根本還不知道有「建築」這個字眼存在。
要到後來,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後,令人敬畏的亞克塞南皇家鹽場(Saline Royale d’Arc-et-Senans)那位同樣令人敬畏的建築師克勞德―尼可拉斯‧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才為我提供了解答:「建築用不可思議的誘惑將旁觀者緊緊包裹住。」
在那之後,類似的相遇還發生過很多次,感受也同樣強烈。首先是在巴黎,被恩典谷教堂(La Chapelle du Val-de-Grâce)的巴洛克奇景和法蘭西學院(Palais de l’Institut)的古典宏偉電到,接下來的驚豔名單還包括(沒按照任何特定順序):埃及的阿布辛貝神廟(Abu Simbel)、羅馬的萬神殿(Pantheon)和麥第奇別墅(Villa Medici)、西班牙哥多華(Cordoba)的大清真寺和格拉納達(Granda)的阿罕布拉宮(Alhambra)、北京的天壇、京都的禪庭、斯里蘭卡的獅子巖城砦(Sigiriya)、貝南的亞伯美王宮(Abomey)、伊斯坦堡名建築師錫南(Sinan)設計的諸多圓頂、猶加敦半島的金字塔、英國巴斯(Bath)的新古典主義願景、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va)的巴洛克展望、摩洛哥塔魯丹特(Taroudant)的城牆,以及路易十四首席軍事工程師沃邦(Vauban)設計的城堡內廓。就像巴枯寧(Bakunin) 大聲宣布的:「這是一場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的盛宴!」
然後,同樣是以亂七八糟的順序,我開始和現代與當代建築相遇。畢竟,從葉門沙那(Sana)的「摩天大樓」直接跳到芝加哥的鑄鐵大廈,實在是令人愉快又充滿啟示。其他後續包括:紐約和香港的天際線;從上海浦東拉回到特拉維夫的包浩斯風格;總是有辦法插進東京「牙縫」裡的超當代「迷尼屋」,以及芬蘭、美國、法國和澳洲的各式夢幻住宅;倫敦的牧歌風情和智利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的大片天空;聖彼得堡的遼闊廣場和約翰尼斯堡的煙塵瀰漫;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運河;莫斯科的地鐵以及五花八門的未來主義機場。
世界各地,建築林立,硬是把自己變成旅行的地標(包括字面的意思和隱喻的意思),喚醒記憶,激發情緒感知,賦予歡樂,或暗示更深刻的謎。雙眼來回梭巡,心思四處漫遊。
「告訴我(既然你對建築的效應如此敏感),在這座城市遊蕩時,難道你沒注意到,那些住了人的建築裡,有些沉默,有些說話,有些最稀罕的甚至會唱起歌來?」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在《尤帕里諾斯,或建築師》(Eupalinos, ou l’Architecte) 一書中如此寫道。多麼了不起的建築定義,無與倫比,這門藝術除了其他種種功能之外,也形塑了我們的時間和空間觀念。
上古的或古典的,現代的或當代的,自發性的或計算性的,直覺性的或概念性的,這些多重多元的建築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因為它是一種藝術,一種創作活動,一種語言。想要了解建築,就得學習如何破解這些「石頭之書」(book of stone),來自所有時代所有地區的這些書籍,構成了一座超越時間的寰宇寶庫,像極了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所說的「理想圖書館」。
還有這麼多人沒提到,還有這麼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和盲點,就算只把範圍局限在當代,想要道盡我們的所有情感和發現,也是不可能的任務。即便有人願意做出犧牲,根據功能、目的或風格將它們分門別類,這工作也不會比較輕鬆。想用斷章取義、沒有來龍去脈的方式展現它們的性格和獨特,自主和差異,套用尚‧克雷(Jean Clair) 和哈洛‧史澤曼(Harald Szeemann) 最愛說的,就像是展出一系列「單身漢機器」(bachelor machines) 。
凡事總有第一次,這當然沒問題。但是,如果你能保持同樣強烈的渴望、好奇和熱情,那麼,每一次都可以是第一次。
吉耶‧德布赫(Gilles De Bure)
註:1巴枯寧(1814–1876):俄國革命家和無政府主義理論家。
註:2尤帕里諾斯:古希臘工程師,西元前六世紀在薩摩斯(Samos)島上開鑿出著名的尤帕里諾斯隧道。
註:3克雷(1940–):法國知名藝術評論家,曾擔任巴黎畢卡索博物館館長多年。
註:4史澤曼(1933–2005):瑞士策展人和藝術史家,策劃過許多革命性的展覽,帶動表演藝術和偶發藝術的興起。
註:5「單身漢機器」最早是於1913年由達達主義藝術家杜象(Marcel Duchamp)提出,用來形容他的作品《大玻璃》(Large Glass)下方的裝置元素,上面包括巧克力研磨器、九個單身漢的蘋果模子、滑輪和其他圖像的機械圖示。
前言
拒絕或接受?Reject / Accept?
「政客、婊子和醜建築,只要撐得夠久,就能得到尊敬。」─美國導演約翰.休斯頓 John Huston
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抗拒進步、發明和想像力,抵擋語言(不論是文學、音樂、藝術、電影、舞蹈或詩的語言)的浮動和流變,幾乎是一種普世不變的頑強現象。建築這種藝術因為會衝擊到每一個人,所以特別容易成為反動的犧牲品。但是這類抗拒者很容易忘記,他們其實是以當時的建築傳統做為比較基準。他們沒有考慮到,自己所維護的建築傳統本身,在它還沒變成傳統之前,也曾經激起同樣的抗議、抵擋和拒絕。此外,他們也沒察覺到,這些所謂的「歷史珍寶」,當初也都是推動「進步」的工具。
法國詩人何內.夏爾(Rene Char)說:「來到世間,卻未掀起波瀾者,既不值得尊敬,也不值得忍耐。」同一時間,怪才作家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也向我們透徹分析:「限制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被超越。」
艾菲爾鐵塔
提高我們的感知,拓寬我們的視野:這或許就是建築的真正本質。特別是因為,拒絕的下一步往往就是接受。1887年,為巴黎世界博覽會興建的艾菲爾鐵塔落成。一群藝術家隨即在2月14日的《時代報》(Le Temps)上刊登一篇宣言,連署者包括作家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巴黎歌劇院建築師夏勒.加尼葉(Charles Garnier),以及詩人方斯瓦.古比(Francois Coppee)、勒孔特.德.李斯勒(Leconte deLisle) 和蘇利.普呂多姆(Sully Prudhomme)。宣言中大聲怒吼:「我們這些熱愛巴黎純潔之美的作家、畫家、雕刻家、建築師,聚集在此,竭盡一切力量,以法國品味之名,以面臨威脅的法國藝術和歷史之名,抗議艾菲爾鐵塔這個毫無意義的醜陋怪獸,矗立在我們首都的正中心。」
這份文件也被稱為《莫泊桑宣言》(Maupassant Manifesto),因為連署者之一的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對艾菲爾鐵塔尤其惱火,他經常在鐵塔上用餐,「因為那是唯一看不到它的地方」。另一位作家里昂.布洛瓦(Leon Bloy),則是把艾菲爾鐵塔稱為「悲慘的街燈柱」。不過到了今天,艾菲爾鐵塔已成為巴黎的標誌,每年吸引將近七百萬人付錢上去參觀,也就是說,它是全世界同類建築中造訪人數最多的一個。
龐畢度中心
九十年後,1977年,龐畢度中心開幕當天,密密麻麻的群眾擠滿了前方廣場。這次沒有報紙宣言,改換成一波又一波的示威活動,情勢火爆到憂心忡忡的中心人員,不得不架設層層拒馬來保護建築物。針對它的外牆,當時最常出現的攻擊字眼是「Meccano」──一種以螺絲、螺帽和鐵片為零件的模型玩具。直到某個自作聰明、對艾菲爾鐵塔還看不順眼的傢伙,發明了新的諷刺妙語:「繼鑽油井之後,現在又多了煉油廠。」不過,就跟艾菲爾鐵塔一樣,過沒多久,我們就看到民眾成群結隊湧入龐畢度中心,進行探索發現之旅,他們或許是想給自己一點時間和機會,讓自己愛上它。
這類案例層出不窮,建築史上的每個里程碑幾乎都經歷過。和巴黎一樣,舊金山也有兩座「從拒絕到接受」的代表建築。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興建期間(1933–37),一直是眾人唱衰的對象;1972年威廉.佩雷拉(William L.Pereira)設計的泛美金字塔(Transamerica Pyramid),同樣激起強烈的反對聲浪。但是到了今天,大橋和金字塔雙雙變成舊金山的兩大象徵。就像對人生見多識廣的美國導演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老愛掛在嘴上的:「政客、婊子和醜建築, 只要撐得夠久, 就能得到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