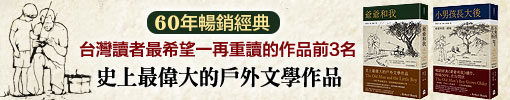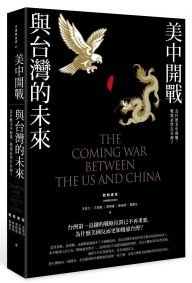導論 美中長期戰略競爭與台灣的選擇
杭亭頓認為:「歷史上,美國一直反對歐洲或亞洲由某一個大國來主宰。我想美國的政策仍會如此。假如中國企圖主宰東亞,美國會反對。」這是美國長久以來的國際政治的觀念。
戰略競爭所帶來的對抗
自2017年川普(Donald John Trump)就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與中國的衝突愈來愈白熱化,這其實有「戰略競爭」上的原因。川普治國的思想核心在於讓「美國再度偉大」,操作的重心在「美國優先」;習近平執政之後,強調「中華民族復興」,實踐的中心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美中之間雖各有目標,卻同步以「民族榮耀」為訴求,可以想見,「美國再度偉大與中華民族復興」碰撞,兩方進入國際領域的「戰略對抗」必然難以避免。
台灣居於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是中國大陸進出太平洋的門戶,是美國西太平洋預防安全前沿的焦點,命運註定台灣將進入這次中美戰略競爭的領域中,而結果也將決定台灣未來道路的吉凶。
2017年12月18日,川普在雷根大廈公布了他上任以來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報告,川普在發布會上,直接說出,「中國和俄國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中俄兩國皆為美國的競爭對手。」隨後,美國防部發布2018年《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報告,開宗明義即指出「美國首要國家安全不是恐怖主義,而是國家間競爭。中國是一個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2019年1月2日新代理美國國防部長夏納漢(Patrick M. Shanahan)在主持第一次主管會報時提醒與會者,「既要專注於正在進行的行動,也要記住中國、中國、中國。」稱中國是「大國競爭中的一個關鍵優先考慮項。……不存在公平競爭這樣的東西—只有競爭。」這證實了在美國國防部門的心中,也已認知到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假想對手。競爭戰略不包括公平與否的競爭概念存在,競爭戰略一旦等同於戰爭戰略的範疇,也就沒有道德的意涵,而且是兵不厭詐。
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艾許頓.卡特(Ashton B. Carter)曾對什麼是「戰略競爭者」做出說明,「我們(美中)的目標應該是成為夥伴,沒有任何理由必須成為競爭對手。……只有雙方犯下大錯時,美中才可能變成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夥伴。」卡特解釋地非常清晰,戰略競爭者只是「敵人」的含蓄表達,中俄同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然而「中國」卻是主要的對手。
1999年,位於南斯拉夫貝爾格勒(Belgrade)的中國大使館被炸,中國的民族情緒極度高漲,美國國內分析中國大陸輿情,便出現了將其視為「戰略競爭者」的呼籲。2001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執政初期,受到2000 年《國家安全利益》報告書的影響,宣稱「美國應該與可能成為戰略對手的國家—中國與俄羅斯」一改柯林頓(Bill Clinton)「接觸―交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成為戰略競爭者關係。但後來因為「911恐怖攻擊」改變為聯盟戰略的影響,才取消了戰略競爭者的方案。
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認為,「冷戰時期……是一種在戰略競爭條件下的軍事全球化。而冷戰後……這些行動更多的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而非戰略利益的驅動。」足見,戰略競爭的意義是明確的國家「戰略利益」競逐。
戰略利益乃是國家利益的別稱,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和國際關係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生死攸關的國家利益,包括了「確保得到美國盟友的積極合作;防止美國的鄰國衰落;確保美國的四鄰沒有敵對大國存在;確保主要全球體系的活力與穩定。」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也認為「歷史上,美國一直反對歐洲或亞洲由某一個大國來主宰。我想美國的政策仍會如此。假如中國企圖主宰東亞,美國會反對。」這是美國長久以來國際政治的觀念。
如今,川普團隊認為中國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修正主義者,快速崛起的大國,正透過經濟誘惑、懲罰,軍事威脅、強化地緣政治等手段,在排擠美國力量,影響到區域盟友合作的態度。
競爭對手就是競爭敵手
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事實上也就是敵手—國家可以集中力量,將資源與目標作優化配置,保障美國國家利益而不受侵擾。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中國大陸問題專家葛來儀(Bonnie Glaser)更明確地說,「本屆政府一致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因此,美國努力……(置於)更有效的競爭戰略上。」
川普「戰略競爭」政策的調整,也帶動了學界認知的轉向。2018年3月在美國外交事務協會網,貼出科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伊萊.瑞特納(Ely Ratner)的文章〈估量中國〉(The China Reckoning),指出,1967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強調對中國大陸採取「誘導變革」,主張「深化商業、外交和文化關係將改變中國內部發展和外部行為的假設,一直是美國戰略的基石。」他認為「美國的權力和霸權可能很容易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喜愛。」
這樣的假設正如同美國政治學家艾倫.弗里德伯格教授(Alan Friedberg Pr.)所言,「沒有充分認識到向中國這個新興戰略競爭對手,開放經濟和社會後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長久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將中國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但中國的實際發展愈來愈不符合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預期。」如今勢必到了重新估量「中國政策」的時刻了。
2018年初,美國國內發起對調整中國戰略的大辯論,通過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科技等廣泛專業人士參與,形成了三大共識:「一、過去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失敗的;二、中國具有在全球成為美國主要競爭對手的實力;三、未來五到十年是中美戰略競爭的關鍵期。」這三大共識說明美國的「中國政策」必須調整,且要在符合「戰略競爭」的定義下轉變。
除了重新評估中國意圖之外,美國還要對自身自由民主開放的原則,保持高度的警惕。2018年11月29日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公布一份《中國的影響與美國利益:增進建設性的警覺》(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研究報告,指出自習近平上台以來,「重新定義中國作為全球參與者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還提出了中國選擇的概念,據稱這是一種比自由民主更有效的發展模式。」針對模式的競爭,報告建議「捍衛美國民主體制的完整性,需要堅持我們開放和自由的原則,更加密切地協調機構部門內部的反應,……通報中國和其他外國參與者可能產生的有害影響。」這份報告有32 位作者,其中不乏對中國大陸較友善學者、專家,如傅高義(Ezra Vogel)和謝淑麗(Susan Shirk)、夏偉(Orville Schell)。
對中國的基本態度,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已經不僅僅是「仇中者」的意識,而是美國學界、智庫、政府部門視中國大陸為修正主義者,甚至危害到美國民主政治的體制了。
中國學者、專家們雖然理解美國安全戰略的「指涉」,但仍認為從川普的商人性格來看,美國的目的應只是交易談判,初期仍未激起對美的共識心防。但隨著時間發酵,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了,川普的政策並不僅僅代表彭斯(Mike Pence)、蓬佩奧、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納瓦羅(Peter Navarro)、波頓(John Bolton)等政府部門不友善決策者的態度,還已經包括了立法機構與學界、智庫獻策者的態度。
例如,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袁鵬認為美國國內已形成共識,認知到「(中國)已成為美國未來必須全力應對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而且這個對手已超越經貿領域和亞太區域,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而王文則認為:「對中國社會及各層組織、機構、企業而言,懷有最好的預期,做足最壞的打算,準備最全的預案,恐怕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中國已經認知到美國不僅僅是針對貿易、關稅問題,還包括了抑制中國崛起的意圖。
事實上,美國政府依據「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NDAA 2019)的要求,制定「整體政府對中國戰略」(a 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 on China),其中,「全面競爭」已成為美國對中戰略的基本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