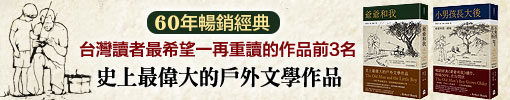作者序
開場白:你想過嗎?你可以這樣想!
蘇拾平
每次演講時最不會開場白,除了寒喧客套外,要不要、想不想交代選擇講題及演講的動機、因緣等,總讓人躊躇再三。
這次,一股腦子把兩年前進行的系列演講「出版經營的十二堂課」,重新整編匯集起來。一方面,自我統合感覺良好,對交代出書動機已無猶豫;另方面,身為出版人,起碼該為讀者找到閱讀的理由吧。就來個開場白:說清楚,講明白。
其一,為什麼文化創意產業與表面以為的很不一樣?
喜歡讀書買書,關心文化創意活動,你對相關行業會有什麼印象?以出版業來說,這是媒體、作家名人、文化學界人士互動圈,還是國內外熱門話題書?集地?
你以為出版經營會是怎麼回事?樂觀的,也許想到暢銷書動輒數十萬冊,既受矚目又利潤可觀,實在令人嚮往;悲觀的,也許看到新書出得目不暇給,懷疑哪來那麼多人看書買書,出版業肯定很難生存。你有興趣進入出版業嗎?積極的,因為可看好多書而躍躍欲試;消極的,因為得讀好多書擔心不能勝任這些印象,這些觀察,都是一般常識所以為的出版業,也的確有其部分真實性,但從常識印象到專業經營,外行熱鬧與內行門道之間,畢竟相差甚遠。
以我個人為例,進入出版業多年,甚至成了資深出版人,愈來愈覺得出版經營沒有頓悟,只有領悟;出版經營是持續的、進展的:與當初,與上次,想的做的都很不一樣。在我看來,文化創意產業或出版業,既是又不像是製造業,也是又不能算是服務業。談到經營,若能不只停留在常識觀感與文化印象,而開始設身處地專注而常態去想去面對時,這一產業當然會與你表面以為的很不一樣。
其二,是經營祕笈也是思考技術,對策從這裡來,創意從這裡來,本事從這裡來,想法做法從這裡來。
在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或出版的教科書很少見,即便有一些理論與實務專書可供參考,實際經營時,還是要面對兩方面困難:
一方面,書上提到的典型已知案例,很少與你將面臨的未知處境相符,你需要能解決問題的判斷與決策時,原理原則也不知如何適用。
另方面,如果真有所謂專業判斷,判斷力到底從何而來?或者說,某些文化事業經營者總能採取創新策略,總能提出突破性的想法與做法;而另一些經營者看似依常理判斷、行動,為什麼總是導致進退失據的結局?
這兩方面困難其實也可以改從兩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層次,如果有所謂的經營祕笈或祕訣,不論是由有利的對策產生,由有效的創意構成,或者由多種想法做法組合,必定能預見能應對本業各樣處境,正是專業本事所在。關鍵在於,這些祕笈祕訣,為何達人用來得心應手,而常人用來勉強生澀?關鍵也在於,這些祕笈祕訣,為何總是很難學習不易傳授?怎樣才能跨越鴻溝?
另一個層次,這顯然與以已知想未知的能力有關,與個人思考技術有關。在我看來,思考技術包括「想」(Think)與「想像」(Imagine)兩部分:前者,就是策略思考,就是掌握問題,經由假設進行邏輯推演;後者,就是創意思考,就是開放問題,找到可能的想法與做法。想想看,經營祕笈不都是這樣來的嗎?也就是說,如果你自己對問題已先行思考過,他人的經營祕笈或專業本事就能才能讓你如虎添翼,你才抓得到它!
其三,你想過了嗎?你可以這樣想!有哪些線索?該怎樣思索?
這樣說就對了吧!對於出版業或文化創意產業,我所累積的經歷經驗算得上經營祕笈的話,那麼,將「出版經營的十二堂課」系列演講的講綱重新整編起來,不只等同於我這些年來有關出版經營的思考過程全紀錄,也可以做為他人及我自己經營思考的練習題。不是嗎?
對於讀者,對於經營,這或許是不錯的閱讀理由:我想過的,你想過了嗎?我曾經這樣想,你也可以這樣想,甚至不這樣想。我所提供的,是問題的線索,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我所提醒的,是可能的思索,在已知與未知之間。至少,可做為筆記備忘、要領提示;可免得想起來找起來漫無邊際、無所依循。
其四,反覆練習,找到自己的答案,找到自己的可能。隔行如隔山,是嗎?
有一次,在某文化創意產業講座系列中,我以「出版經營的幾種性格」為題與同好分享,課後就有幾位急切表示,其實所屬行業也有同樣的經營性格。另一次,在向同業報告「未來在等待的出版」的場合,一位電子業的朋友告訴我,我所提到的,啟發他想起很多自己那一行的問題,讓我十分驚訝。
我相信,經營是可以移花接木的,思考是可以觸類旁通的。但我更認為,經營祕笈要不斷考驗才能與時俱進,思考技術要反覆練習才能分出高下。這些練習題是開放的,每一次,你都有機會找到不同的答案,想到其他的可能,這就是進展。
說完了,謝謝!
推薦序
主觀的選擇、未知的結果與理性的操作
林載爵(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聯經出版發行人兼總編輯)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讀到有關出版的專業書籍是在1985年,這年英國的一位出版人Anthony Blond出版了《有關書的書》(The Book Book)。他以自己所經歷的故事和相關軼聞,用幽默、愉快的筆調,描述了這個行業從作者、經紀人、出版人、編輯到合約、印製、書評、行銷、書店、圖書館、書獎、書展的全盤面貌。這一年,巨型出版集團尚未出現。出版,這個行業仍然在傳統的軌道上持續發展。像Anthony Blond這種對出版充滿熱情的人,對出版業當然懷著希望與憧憬。
他在書裡對出版人的描述是,一個真正的出版人永遠保持熱情,擁有特別的好奇心。他渴望知道放在他桌上的每一份稿件裡面蘊藏了什麼,並且希望它是一本傑作。知識、時間與經驗都不能減損他的樂觀。他選擇出版他喜歡的書,也想像那些書都會成功,他的選擇當然是主觀的。有些出版人會自大一些,總是口口聲聲「我」的作者、「我」的書,但這個行業裡比較誠實的人則承認,他們只不過是印刷、裝訂、公關和促銷別人創作之間的中介人。書屬於寫作的人,那是作者的書,出版人所做的只是幫他行銷。所以,從商業的角度看,出版人彼此之間都不會以攻擊性的態度相待。
出版是最多樣性的商業,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有很大的發展範圍,這種多樣性讓投入這個行業的人都能表現各自的個性和品味,在寬闊的舞台上盡情演出。你可以從家裡開始這項工作,所要做的是自己寫一本書,或者剛好一個朋友寫完一本書。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項大企業,自己當起大老闆。但是成為出版人意謂著進入一個高度冒險的境地,假如你的品味碰巧遇到許多同好,你就可能賺錢,但這很像賭博,並且是非理性的。買書大眾的口味的變化無常,使出版變得讓人非常興奮。總之,這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多樣性、非理性、風險極高但令人振奮的行業。
這是二十二年前一個出版人的觀察與自我剖析。二十二年後的今天,出版業已經產生了巨變。二十二年前,《魔戒》以平穩、累積的方式征服全球,今天,《哈利波特》以疾風迅雷的凶猛之姿暢銷全球。透過併購,巨型出版集團的規模愈來愈大,占據了暢銷書排行榜的大部分。在很多國家,連鎖書店控制了通路,甚至超越國界,構築全球網絡。網路書店興起,改變了讀者的購買行為,讓實體書店遭遇空前的挑戰。網路時代來臨,改變了書寫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在網路世界中傳遞訊息與內容,這是一個「內容的世代」(the generation of contents),只要你願意,都可以製造內容,傳播內容,甚至販賣內容,不再需要依賴傳統的出版行為。數位出版開始出現,儘管還在摸索正確的模式與載體,但已經預言在未來幾年之內將取代紙本書籍,成為閱讀的主流。
十年來產生的巨變,改變了出版這個行業的本質嗎?
2005年美國勞動節的那個週末,亨利?后特(Henry Holt)出版社社長史特靈(John Sterling)在家裡開始閱讀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魯班費(Jed Rubenfeld)的第一本小說的稿本。魯班費現年四十八歲,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傑出教授,專研憲法與刑法,已經出版了兩本法學專著。憑藉著才華,他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為主角創作了第一本小說:《謀殺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Murder)。佛洛伊德曾經偕同容格(Carl Jung)於1909年8月29日抵達紐約市曼哈頓,停留了一星期。魯班費便以此為背景,構思了佛洛伊德在曼哈頓陷入一樁謀殺案的經過,將心裡分析與謀殺情節結合在一起。
五十四歲的史特靈讀完稿本後,堅信他非出版這本小說不可。在他看來,魯班費的小說具有複雜的角色、誘人的情節,兼含怪異性癖好的插曲,一定能吸引讀者。加上這是一本歷史推理,而歷史推理又是最近當紅的文類。他認為這本小說有潛力成為下一本《達文西密碼》。然而,在史特靈提出正式報價之前,華納出版社(Warner Books)已經提出了預付120萬美金擁有全球版權的報價,華納的主意是打算從出售海外版權中撈回一些成本。但是魯班費的經紀人威廉?莫理斯公司(William Morris)卻另有盤算,他們知道本書具有強大的國際潛力,所以決定自己處理海外版權。在這個背景下,史特靈為了避免公開競價,提出了預付80萬美金只擁有北美版權的報價,這是亨利?后特從來沒付過的最高預付款,威廉?莫理斯接受了。之後,威廉莫理斯出售了31種海外版權,總計100萬美金,加上史特靈的80萬美金,總共獲得180萬美金的預付款,這還不包括華納兄弟公司(Warner Bros.)所付的沒有公開的電影版權費。
亨利?后特是一個小型但聲譽卓著的出版社,以非小說和兒童文學為主力。每年新書出版量約150本,年收入大約4500萬美金。史特靈是資深編輯出身,在1998年亨利?后特陷入財務危機時接掌總裁兼社長的職務。他極想從非小說的領域進入小說,因此,《謀殺的解釋》將是亨利?后特進入新領域的敲門磚。史特靈說:「我們需要走出下一步。假如獲利是巨大的,冒險也是巨大的。這個行業已經變成了這個樣子。」
史特靈瞭解到出版已經變成「贏者通吃」(winner-takesall)的局面,在年新書出版量高達十七萬兩千冊的狀況下,出版人必須找到一本具有巨大潛力的書,全力出擊。假如時運俱佳,其成果將無可限量,假如失敗了,就如墜深淵。於是,在低毛利的這個行業裡,出版人不得不玩起賭博的遊戲。利特?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 Co.)以220萬美金取得剛出道作家寇斯透娃(Elizabeth Kostova)的《歷史學家》的版權,儘管評價不一,但在全力促銷下,幸運地銷售了一百多萬冊。
2005年秋天,這本書的競價結案。史特靈馬上與魯班費見面,要求更改原來的書名:《行動之名》(The Name of Action),史特靈希望改為一個更聳動,更有力的書名。他還向魯班費指出,有些角色太軟弱,某些轉折的敘述不夠精確,某些情節要更清楚。魯班費完全同意,立即修訂。史特靈接著獲悉另一家出版社也將在同一個時候出版一本重量級的歷史推理小說,因此決定投入50萬美金作為行銷費用,在出版前七個月開始各種宣傳活動。
史特靈傳遞的訊息很清楚,他要讓《謀殺的解釋》成為一股出版旋風。他花費一萬七千美金印製了一萬冊試閱本,廣泛發送,以求先聲奪人,又花費了一萬美金設置專屬網站。他也開始安排作家午餐,與媒體見面。所有的反應都很好,讓史特靈有理由相信這是他出版生涯中最好的決定。其他出版社對他表示羨慕,行銷人員的回報也都信心滿滿,這本書一定大賣。雜誌的介紹也是一片贊揚之聲,認為這本書「引人入勝,以精巧手法描述謀殺奇案」。獨立書店聯盟更是大力支持,把《謀殺的解釋》作為九月選書,聯盟下的1200家獨立書店將在九月主推這本書。於是,史特靈決定首刷量185000冊,對於作家的第一本小說來說,這個數量是罕見的。
《謀殺的解釋》在2006年9月5日上市,史特靈的期待能否成真馬上揭曉。九月二十四日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謀殺的解釋》名列第18名,這讓史特靈有點失望,他知道一開始如果氣勢打不開,以後就忙煩了。到了10月1日,排名滑落到第20名,情勢已無可挽回。包括版權與行銷,亨利?后特總共投資了130萬美金,這需要賣出150,000冊才能打平。到了10月份,史特靈只能期待《謀殺的解釋》雖然不能暢銷,但至少還能持續銷售,接著的平裝本也還能獲益,然後就是等待未來電影上映,再重新宣傳一次。
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宣傳太早?喜歡佛洛伊德的人沒那麼多?九月同時出現太多大書?福爾摩斯式的推理小說已經過時?所有事後的解釋都言之成理,但就是無法預見。出版業的本質還是維持著一向的不確定性:主觀的選擇,未知的結果。主觀的選擇來自出版人的個人品味與喜好,未知的結果來自複雜的市場條件,特別是很難捉摸的讀者口味。當史特靈已經察覺魯班費的小說在市場的表現不如預期時,9月20日,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手上拿著杭士基(Noam Chomsky)的《霸權或生存:美國對全球霸權的追求》(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大加贊許。很快的,這本書馬上登上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的暢銷書排行榜,出版社緊急加印了5萬冊。杭士基大作的出版者是誰?答案:亨利?后特。然而,這個行業就不需要理性的操作嗎?當然不是。這個行業裡還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屬於企業的經營與管理的層面,只是很少人將它整理成一門專業知識,甚至出版人也無法掌握全貌,深入瞭解。拾平自1980年代投身出版界以來,累積了長久而豐富的經驗,並且對出版產業的運作做了深入的思考。這些長期觀察與思考的結果,就發展成了這本專著。
拾平以條列的表達方式,針對閱讀、行銷、通路、經銷、定價、庫存,以及策略與管理等出版產業的各個環節,做了詳細的提示與建議。對出版產業的從業人員,或是想要瞭解這個行業的人,這本書無疑是最佳讀本。讀者可以從每一個提示出發,進入更深刻的反省與思考。
拾平透過這本書讓我們知道,理性的操作畢竟是出版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沒有了這部分,這個行業就不能成為一種健全的商業。期望這本書的出版對台灣出版產業的發展帶來積極的助益。
奇愛博士第二章 ──我如何學會停止憂慮轉愛行銷兼序蘇拾平的新書
詹宏志(PChome網路家庭董事長)
1982年的某一天,高砂紡織周家的兩位兄弟突然邀請我吃飯,席中他們拿出一張設計圖給我看,客氣地詢問我的意見,那是一家計畫中的大型書店平面規劃圖,地點就設在台北公館原來高砂紡織廠房預備改建的大樓裡。
兄弟當中的哥哥周正剛先生,我是通過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有幸認識的,弟弟周傳芳先生則是通過哥哥而結識的。王榮文向我介紹周正剛先生是一位愛讀書的企業家,家族原有的高砂紡織至今仍是世界最有實力的燈芯絨與牛仔布的供應廠之一,然而他對日本社會的讀書風氣與豐富充實的大型書店特別推崇,工作之餘常愛帶著幹部往日本書店跑,他尤其喜歡東京車站前的「八重洲Book Center」,常常期盼台灣的出版界也能有相同的魄力,能打造和日本一樣明朗多彩的大型書店。也因為愛屋及烏,周家兄弟當時也成為許多出版家的友人,有時候還對出版者扮演私下協助和經濟紓困的角色。
沒想到他時常掛在嘴上的夢想,現在卻來到由他自己實踐與兌現的時刻。我看著那張設計圖裡理想遠大、面積驚人的新型書店,覺得有點目眩神迷,也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好拿起鉛筆在角落圈了一個位置,說:「書店太大了,讀者逛累了要如何休息?不如在這裡開一家咖啡店吧?」這個想法,不用說,也不是什麼新鮮構想,日本書店不都是這麼做的嗎?
但我那時候只是在報社工作的一介小編輯,周家兄弟為什麼要這麼鄭重其事地請我吃飯呢?原來他們不只是為一個大書店的構想徵詢意見,他們還希望來邀我去為這家書店工作(那也許也是來自王榮文的推薦)。大書店對我當然是極具誘惑力的,但我幾天之前才答應了報社老闆的好意,決心遷到紐約去參加美國版的創建工作。
不料造化弄人,我在美國的工作並不如意,我內心充滿生涯選擇的困惑,第二年我就自覺不適合新聞工作而辭職了。回到台灣後,流浪徬徨了一陣子,最後我才接受亦師亦友的王榮文先生的邀約,來到遠流出版公司上班。此刻的遠流已經搬到高砂紡織改建的大樓裡,而當年周家兄弟讓我先睹為快的書店設計圖已經成了乾淨明亮的大書店,就在我的辦公室腳下,至於那個我倉皇用鉛筆圈下的位置,如今成了一間窗明几淨的咖啡店,從此我將每天坐在這裡讀書、寫作、聊天、面客,同樣的位子一坐就是八年,牆上幾乎要印出和達摩一樣的影子來。
書店並不是一開始就成功順利的,咖啡店和快餐店倒比較快賺了錢,當時負責經營的哥哥周正剛,有時也對書店營業規模成長的緩慢感到憂愁,咖啡店裡遇見了我,總要坐下來聊聊天,我也跟著胡亂出些主意。但周家兄弟可是劍及履及的企業家,不是自怨自艾的文人,他們是不斷尋求管理工具、尋找改進之道的現代化經理人;很快的,書店裡書籍的營業額陸續成長(咖啡店反而因為坐滿而成長減緩了),進而離開自己的地產,到其他地方開設新店,我看著他們開設重慶南路書街的「城中店」,開設台大周邊的「台大店」,再開設當時極具挑戰性的「忠孝店」(因為地租最高),「金石堂書店」不再只是企業家兄弟的文化夢想,它已經成為台灣讀書景觀裡重要的連鎖企業了。
台灣在此之前,不是沒有好的「大書店」,我年輕時代嚮往的台南「南一書局」、台中的「中央書局」、台北的「三民書局」可都是充實而豐富,曾經造福一個世代的認真好書店;也還有很多如今說名字沒人知道、在當時以較高折扣賣書、讓窮學生懷念的小書店,那是80年代以前的事。從80年代中起,更現代化、更企業化、更有零售業管理知識、更有能力服務現代社會的書店架構,就要由「金石堂書店」來領風騷了。
在目睹「金石堂書店」崛起的同時(還有機會在咖啡店裡聽到書店創辦人親自發音的「實況轉播」),我自己也正經歷著生涯裡的「出版學習之旅」。在出版社裡得到老闆王榮文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我正練習把自己所知道的半缸水經濟學(一種了解社會行為的知識)應用到正在快速變化的台灣社會裡。在幾個幸運成功的案子的庇蔭下,小出版社首先開始了雄心勃勃的人才延攬行動,因為我相信出版的力量與編輯人的創造能力密不可分(現在回頭看,這句話可能只對了一半,但當時對了一半也足夠打天下了)。我先把我的編輯師父周浩正先生請了來,又邀請了從前同事?玉雲來和我一起做行銷(使編輯人的成果有較好的後盾),後來又爭取到剛從報社離開的陳雨航和蘇拾平,再後來又因緣際會結識年輕銳利的郝廣才,其他才從學校出來、如今在各地獨當一面的人才也有不少。
但那是一個變革的年代,我們正面對變革的「果」,我們自己又是變革的「因」。因為社會在變,我們看到原有工作方法失靈的狀態(那是「果」),必須有新計畫和新想法;我們大膽提出某些不一樣的想法、做法,衝擊了我們身處的行業和社會,我們又變成「破壞者」(「因」)了。
我懷念那個學習的年代,我懷念在餐桌上與這些同事朋友討論爭吵的年代,我們拒絕做自怨自艾的無能文人,我們擁有知識也追求知識,有知識的人應該是有力量的人。我們分析環境,我們提出方案,我們要結果。如果我們在周圍找不到可提供我們幫助的知識,我們就通過實踐與經驗「建構」知識。
但世界滾滾前進,我們找到方法,很快地就又失去了它(因為環境又變了),這就不得不讓我們追尋的理解必須回到更根本,找到事物的底層,以便能夠解釋更多的現象與變化,直到它成為一種類似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所說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為止。
當時和我在桌上辯論最多的同伴蘇拾平(我的經濟系同班同學),顯然是第一個企圖寫出這種「一般理論」的人,他的新書《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技術:我的120道出版經營練習題》,就想從現象推回到本質,看出某些出版業經營(以及廣泛適用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規律,讓思考者不只有能力看出一個狀態、提出一個方案,而是有能力面對各種狀態,提出各種方案,包括我們今天還不曾面對的問題在內。
回到本質的思考力量是驚人的,最近「金石堂書店」爆發了與出版社結帳方式的爭議風波,媒體與一般的討論都流於情緒(小出版社趁機想表達多年的委屈)與八卦(把大型企業描寫成「邪惡帝國」是聳動而便宜的事),但蘇拾平在書中的一篇訪問稿就讓我看到完全不一樣的清晰分析。他從台灣圖書長期的「過度供給」(over supply)解釋出版業行之有年的「月結制」為什麼最後會失靈,「金石堂書店」的保留款與票期延長,很大部分來自於這樣的結構性因素(當然也有部分管理因素),而非出於對出版社的惡意。如果出版社明白這是模式與結構的選擇,就不會選擇一種抱怨、對抗或報復的姿態,可能願意與金石堂共同尋找一種更好也更久長的解決之道。金石堂當然也一樣,如果對出版社與媒體的怨懟與批評,產生一種受傷的情緒,決定要把更大的通路力量拿來報復個別出版社,這也是沒有看到雜音底下的真相。
蘇拾平的新書也有點讓我慚愧,我對25年來台灣出版業的現場目擊和分析反省,顯然是缺少整理與貢獻的熱情。此刻我有了客觀的立場(我已經從出版行業裡退休了),卻反而有心無力,但在蘇拾平新書之後,也許我該重新想一想,是否先寫那篇被我擱置多年的《論庫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