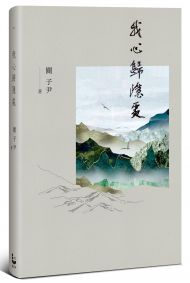【自序 — 一份感性的呼喚……】
吟詠唱酬之事,向來為我所欣羨,但從來沒設想過,此等風雅之事,自己終能躬身參與,更連造夢也沒想過終於有出版詩集的考慮。而這一切,都要從為先師勞思光教授草擬「像贊」一事說起。
事緣先師2012年捐館以還,在港一眾生員便醞釀著為老師樹立銅像之事。直到2017年銅像終於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未圓湖畔樹立的五年間,同人中以張燦輝兄的奔走斡旋居功至偉。自計劃構思之初,燦輝兄便力邀我和另一同人聯署,並撰寫像贊。當其時也,我自況早是閒雲野鶴,一直懇辭,並建議其他人選,然燦輝兄一再堅持如舊。有謂人貴自知,查辭章之事,我自份散文尚可勉力,韻文則從未涉獵,此實我懇辭的原因。唯念業師恩重如山,像贊事我雖不敢為之,實亦不敢終不為之!經過幾番掙扎,特別是在燦輝兄的堅持下,為及早綢繆,我於立像前一年起,便暗地責成自己鑽研格律,賦詩寫懷,以備萬一。集一年所得,計有五絕、五律、七絕、特別是七律多首,最後才涉獵歷代四言詩作。這個自學過程,猶試步於詩階。偶有逸趣,每喜不自勝。時屆非要著手於像贊不可之日,散文部分,固有一二處須與燦輝兄幾度斟酌,但十六句之四言贊辭,卻意外地水到渠成,一經抵定,竟無一字之改。
平生一大憾事,是未能把握機會,於思光師在世時跟他學詩。回想先師中大榮休至赴臺前很長的一段日子裡,曾多次移玉舍下索取紙筆,並信手寫下剛擬就的詩稿交我留存,這猶如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顆顆種子。多年後我因像贊事而終能粗通詩律,全出於先師的精神感召,這無疑是先師身後仍留給我的一份厚禮。我心底的感動,實無以言詮;先師九原知之,想亦必能開懷。
銅像之事完滿辦好後,本以為這個學習過程可告一段落,然而卻發現自己學詩以還,對世間事物的感知,那怕一草一木,一花一鳥,都常有新的體會;又對文字的音義,詞句的結構,亦屢有新的聯想。這是我未之曾有的經驗。這些新的體會,就如一份感性的呼喚,又反過來促使我進一步在已踏足的「詩階」上作了更多的嘗試……於是數年下來,每因「觸景生情」,便斷斷續續地又隨手寫下為數不少的詩作。
王船山有云:「詩者幽明之際也」。幽明二字,本指暗晦與明朗,後借指人間必經歷的「死」、「生」。上引船山先生一句,其實是說,詩的一大功能,就是能於逝者與生人之間建立起一些意向聯繋 (intentional linkage),以跨過幽明阻隔。事實上,我之所以學詩,出發點本來就是要紀念先師,故這本詩集中不少詩作都直接或間接和先師有關,其中有好幾首是以「步韻」的方式寫成的,這種方式的詩作,就有如在老師身後仍得以親炙於其胸懷。
此外,一旦粗通音律,這一份與逝者溝通的意向,便很自然地轉移到自己的至親、摯友,乃至自己感佩的時賢、甚至古人身上。因此,這本詩集除了「感懷篇」、「紀遊篇」、「寄贈篇」、「唱酬篇」、「親情篇」等篇目外,還包括了份量不輕的「悼念篇」。至於別成一篇的「憶兒雜詠」系列,其中的十多首七絕的醞釀,就像為我多敞開了一道穿越幽明阻隔的大門,對我多年以來紆鬱難釋的心志,是又一次的釋放。
幽明的考慮,印之於詩道,除可解作死生外,也可擬作虛實,而所謂「幽明之際」,其實可指實與虛之間的對立辯證,如象之與心,形之與意,今之與昔,情之與理,主之與從,換喻之與明喻等元素的各種對比、反差、交融,與磨合方式。我一向自忖對語言有一定浸淫與掌握,但直到初步體會了詩這另類的語言運用,才驚覺自己一向的不足。
詩的創作,似乎真的須有「別才」,而這正是我所欠缺的。我常欣羨一些詩友七步成詩的才華,相對之下,我每寫一詩,幾乎都是在「苦吟」。最近一年由於全心於完成一本論海德格思想的專著,結果寫詩的興味便大大冷卻下來。海德格書出版後,經檢拾書篋,發現最少還有三、四本學術書稿應陸續完成。問題是,幾年之間,整個世界似乎已鬧得天翻地覆。自己還有多少可資善用的歲月,已難預料。回想自己的「正務」畢竟是哲學,人生到了這一階段,是否應該為餘下的精神與時間作較合適的打算?
這本詩集的出版,其實正暗示了我在這「詩階」上的嘗試將告一段落。回顧過去四五年這段神奇旅程,我首先要衷心感謝燦輝兄,若無他的信任與堅持,這一切根本不會發生。回想當初閉門造車的一年將屆,而先師像贊將要動筆之日,由於茲事體大,我終於硬著頭皮向中大中文系以詩道見稱的陳煒舜君請益,並相唱酬;待部分詩作陸續於社交媒體發表後,承港臺不少以漢語、中文、國學為專業的學者首肯,對我來說,是極重要的鼓勵,其中,何志華、馮勝利、華瑋、鄭吉雄、林碧玲、彭雅玲、鄭毓瑜多位教授常不吝指教,諸位情誼於此深致謝意。
誠然,有謂慎終如始,古人向來有「詩戒」這回事。特別是科舉制度下,一些亟欲出仕的讀書人為免玩物喪志,都會有戒詩之舉。今日的我既早是閒雲野鶴,怎樣看也沒有戒詩的必要,不過,在詩興與責任的兩衡下,今後的我,詩肯定會愈寫愈少!今天難得把過去幾年所得來一個了結,或堪留一絲痕跡,對於「歲不我與」,而仍擬探步於詩階之來者,或許可算是一分拋磚引玉的誘餌吧,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