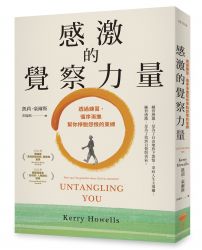第二章、認清怨懟的本質(節錄)
怨懟就像自己喝下毒藥卻希望能毒死敵人。──前南非總統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
感激有一種奇妙的力量,能照亮缺少它的地方,特別是與其相反的「怨懟」所在之處。我們可以開始在某些情境中留意這種現象,例如,我們想要表示感激,卻因為覺得痛苦或無法開口而難以做到的時候。我經常把這種情況稱為「渾沌」(murky),因為我們知道某件事不太對勁,卻又說不上來是什麼,也無法完全向自己坦承這一點,更別說要向別人坦承了。
事實上,我們甚至很難承認自己心懷怨懟,因為怨懟在本質上是隱藏的。正如美國政治和法律哲學研究者胡安.伯納爾(Juan Bernal)所言:「在人際關係中不應談論怨懟的標準;怨懟應該要保密,即使對自己亦然。」我們不敢承認自己的怨懟,可能是想要保持美好與正面的形象,或者不想擾亂現狀。
躲藏起來的怨懟
嫉妒、憤怒、沮喪、失望等其他負面情緒雖然也會使人不愉快,但卻比怨懟的感受更為「直白」,也更能讓我們意識到。要和別人談論這些情緒通常比較容易,因為我們會有那些反應似乎合情合理,也比較能被社會接受,例如,被當成臨時員工受到惡劣對待而感到憤怒是完全正當的、由於政府對氣候變化毫無作為而覺得生氣或沮喪會被視為情有可原、對於家暴造成的傷害表達厭惡和憤慨是一種真誠的反應且符合社會觀點。
然而,怨懟通常都帶有一種羞恥感:它會拆穿我們;它會使我們顯得有些軟弱,無法成為自己以為的那種人,也無法維持自己想在別人眼中留下的形象。為什麼我們還沒放下?為什麼我們要執著於看似不重要的小事這麼久?我們竟然會受到這麼深的傷害,有時候想想還真荒謬。那種羞恥與罪惡的感覺會使情況變得更複雜,讓我們更難認清怨懟的本質。
對我們應該感激的人產生怨懟,或許也會令我們覺得羞愧,使我們可能會陷入我稱之為「感激黏網」(sticky web of gratitude)的處境:在其中受到拉扯,一方面覺得自己受過某人的恩惠而虧欠對方,另一方面卻又因為受到傷害而怨恨對方。此時怨懟的感覺通常會更為強烈,但由於我們認為自己應該要感激,所以傾向於將怨懟隱藏起來。這種黏網在戀愛關係中非常普遍;我們平常可能會不斷被提醒,想起另一半「以前」曾為我們做過什麼,因此我們只能滿懷感激。然而,這可能會使我們無法誠實面對自己,不去處理「現在」對方讓我們失望或造成痛苦的問題。
感激黏網的另一個特點,是我們普遍認為無論自己對另一個人有多麼感激,只要我們覺得是對方引起的怨懟,那麼處理問題的人就應該是他們而不是我們自己。我們可能會對他們勉強表示感激或只是做做樣子(順帶一提,這不能算是感激),然後空等著想要對方知道我們的痛苦並採取行動。這種等待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月,甚至是好幾年;在此期間,我們可能會將怨懟合理化並隱藏起來,或者決定在關係中將就──全都是以「感激」的名義。
我們經常擔心如回想起過去的苦痛,就會挖出舊傷口。同時,如果考量到跟對方談論這件事的後果,我們可能也會害怕他們的反應,特別是當對方握有權力的時候。要面對傷害我們的人確實非常可怕,我們或許不相信自己能理性冷靜地解決情況,所以也許最好還是只對自己說「維持現狀就好了」;假使我們長期如此為之,就會一直將這種事情合理化,直到我們不承認自己心懷怨懟。我們的怨懟也可能經年累月存在,最後變成了生活方式或個性的一部分,說不定我們還會認為這不是自己能選擇的。
當然,某些怨懟並不會隱藏起來,例如,因為創傷事件遭受不公而引起的怨恨。要表達這種怨懟簡單多了,通常也會被視為理所當然,完全合乎情理。在這些情況中,怨懟可能會被當成最適當的反應,甚至往往還會得到公眾認同,不會帶有任何羞恥感。由種族偏見和宗教不寬容所引發的民怨就是十分具體的例子。
不過這種規模較大的怨恨可能會淹沒日常的怨恨,或使其變得無足輕重。我們會為了抱持著規模較小的怨恨而感到羞恥,有一部分原因是這種怨恨和世界上那些大規模的不公不義比較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再者,多數關於怨恨的著作都是在討論規模更大、更痛苦難忘的怨恨,而規模較小的怨恨幾乎沒人關心。
為了不讓怨懟躲藏起來,我們必須承認它的存在。我們必須讓怨懟擁有聲音、形體、地位,這樣才能好好討論,不會產生羞恥或罪惡感,也不會出現自我批評或批評他人。只有這樣才能看出怨懟是如何剝奪我們的感激並破壞我們的關係。在本章,我們會探討怨懟的一些主要特徵,讓我們能夠認出自己的怨懟。至於該如何尋找自己的怨懟?首先我們可以從「不可能覺得感激的地方找起」。
怨懟會抵銷感激
傑瑞米(Jeremy)和他的母親關(Gwen)之間的關係,就是怨懟的經典案例。關在一家養老院已經住了十年,但傑瑞米很害怕要去探訪母親(也因為自己有這種感覺而產生罪惡感)。他們的對話通常都會演變成關喋喋不休地抱怨她丈夫,也就是傑瑞米的父親,說他狠心地結束婚姻,跟比她年輕許多的「那個女人」跑了。她會不斷重複以前的故事,提起他們不得不賣掉那棟漂亮的房子、傑瑞米被迫轉學、她失去的朋友,以及要是她丈夫「做得對」,他們現在的生活就會過得更好。
關這種一直受到背叛與傷害的強烈感覺,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感覺在過去三十年中掌控了她的生活;不是只有五年、十年、二十年,而是三十年!關始終無法放下遭到背叛所造成的痛苦。由於陷入了痛苦,所以她的感覺無法「重新發送」──怨懟滲進了她的骨子裡,毒害了她的心智,也毒害了身邊的人。
聽到丈夫說要離開這段婚姻時,關感到嫉妒、憤怒、失望、沮喪、悲傷,而且震驚至極。她不知道他會傷害她這麼深,而這些痛苦的想法徘徊著,在她的腦中不停打轉,夜復一夜,年復一年,逐漸將她的情感轉化成一種深刻的怨懟。關會透過這種怨懟的視角看待其他所有事情,只要一個不如意就很容易感到失望。最後這股怨懟和忿恨定義了她的生活,也成為她的特徵。就像哲學家尼采說的:「世上沒什麼能比怨懟的感受更快能吞噬一個人。」被強烈的怨懟吞噬的關,自從發展出固定的人格面貌,變成了「一個對凡事都忿忿不平的人」。
關的忿恨通常會在聖誕節前後逐漸加深,因為她的丈夫就是選擇在聖誕夜那天,告知要離開的消息。傑瑞米可以料到她又要喋喋不休抱怨什麼:「我可不要又得熬過一個聖誕節……,又來了,又是一個難過悲慘的聖誕節,這都多虧了你父親啊」諸如此類。關幾乎隨時都沉浸在自己的憤怒中,以致於無法看見或感受到其他人的痛苦。傑瑞米的妻子與孩子都難以忍受。每一年他們都會懇求他,希望能過個「沒有關的聖誕節」。他們全都很厭惡關怨懟發作的樣子,這會徹底搞砸過節的氣氛,每一年都是如此。
覺得關難以相處的不只有她的家人,還包括養老院的大多數照顧者。大家都知道,只要任何一個人稍微晚一點處理她的需求,或者沒按照她的標準做到某件事,她就會說出尖酸刻薄的話。待在養老院的那些年裡,關幾乎從未對任何人為她做的任何事表達過感謝,這也使得工作人員比較不想跟她相處。
傑瑞米曾嘗試提醒母親,想讓她知道父親沒有那麼糟;他們兩人曾經有些日子很快樂,而且他也確實有一些優點;而最令他難過的是,關沒能想到傑瑞米就是他們以前發生過的好事之一。由於關的怨恨實在太強烈了,根本不可能對丈夫離開婚姻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覺得感激。
為了她好,也為了他自己和家人好,傑瑞米懇求母親原諒父親,放下一切的痛苦與責怪。不過關只要一聽到他提起這件事就會覺得受傷或生氣。她指責傑瑞米漠不關心,也無視她的痛苦。結果,怨恨就這樣繼續滋長。
怨懟會反芻
比利時裔美國哲學家艾蜜莉.羅蒂(Amélie Rorty)是這麼描述怨懟的:「……它會以過去為食,不斷咀嚼充滿了羞恥、侮辱與傷害的痛苦回憶,然後又吐回口中,直到苦味變成了香味。」
你是否曾經被某人深深傷害,覺得自己永遠無法放下那種痛苦?這種感覺可能會糾纏你好幾年,就跟關一樣。如果沒有事情讓你分心,它就會在晚上煩擾你;你會在腦中一遍又一遍回想發生的事.你會反覆思考,試圖處理傷痛與震驚,希望能釐清頭緒──可是你做不到。白天的時候,你會向願意傾聽你說話的人再次講述一切,試圖理解自己這麼失望的原因。你想從別人身上得到認可,安慰自己不是只有你會對這種情況感到厭惡、憤怒或訝異。
「怨懟」(resentment)一詞來自古法語的resentir,意思是「重新經歷一種強烈的感受」。怨懟有兩個顯著的特徵會促使我們反芻思考:它會在我們腦中不斷重現當初的情況,而且會長時間存留,揮之不去。
關的丈夫離開時,她沒有阻止。她向願意聽她說話的人表達了震驚、傷痛與憤怒。但由於她未能直接向丈夫表達自己的感受──亦即她的痛苦來源,對於丈夫的行為深感不公,遲遲無法放下,而這樣的感受也就卡在心中變成了怨懟;同時,她覺得自己無能為力,沒辦法改變情況。關的情緒(emotions)無法成為e-motions──energy in motion(流動的能量),因為使她陷在這份痛苦中了。
之所以會形成怨懟,不只是單一情緒,而是混雜的情緒。美國社會學教授華倫.坦豪頓(Warren TenHouten)將此稱為怨懟的「第三級」(tertiary-level)特性,結合了憤怒、厭惡與驚訝。這裡提到的驚訝並非愉快的那一種,而是關感受到的震驚:這種深刻的衝擊會影響人的行為舉止,或讓一切看起來不像表面那樣,而讓我們深陷於怨懟之中的就是這種震驚。
由於怨懟是一種難以擺脫的情緒,而且我們也無法走出痛苦,所以它會增長、惡化,進而開始吸引其他的怨懟。或許你有過這種經驗:夜晚醒著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沉浸在當下的怨懟之中,結果發現腦中似乎也出現了其他怨懟。如果你不做點什麼來處理這些忿忿不平的想法,就可能就會導致失眠,引發第一章所述的其他各種身體和心理疾病。
我們可以從關的案例中看出,她的反芻思考變成了習慣,使得怨懟變成了唯一的性格,也成為生活以及與他人相處的唯一原則,甚至也是這樣對待那些跟她的痛苦完全無關的人。當怨恨成為生存之道,我們不但會反芻自己的情緒和想法,也會發展出一種完整的病態怨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