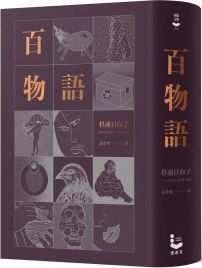今昔百物語 李長聲
聽人講鬼故事,有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樂趣。
我生於民國三十八年。一路伴隨中國的篳路藍縷或柳暗花明,諸如除四害、大煉鋼鐵、三年自然災害、文革,上山下鄉。我下到吉林省的山裡。民居是對面炕,一間屋子裡睡了兩炕「知識青年」,未讀完高中或初中的。夏天,勞累了一天也難以入睡,尤其月黑天,吹滅煤油燈真個是伸手不見五指,有人便提議講嚇死人的故事。菸頭的光忽明忽暗地照亮吸菸人的臉,滿臉的鬼氣。開車不暈車,談鬼不怕鬼,「如語者」吸一口菸,聽眾的心就被提起來一下。好些鬧鬼的傳說是紅海洋似的城市裡流行的,若采編「文革鬼故事」說不定也滿有趣,但當年聽了,出一身冷汗,酣然入睡。
日本也是愛在夏天裡談鬼,當作「風物詩」。時值溽暑,電視播放怪談節目,影院上演恐怖電影,游樂園開設妖怪屋。二○一一年發生東日本地震,引發大海嘯,造成核電站事故,全社會呼籲節電,更有人鼓吹「用怪談消暑」。
「鬼」這個漢字最早出現在七三三年成書的《出雲國風土記》中,該鬼一只眼,吃人。平安朝(八世紀末至十二世紀末)鬧「怨靈」,皇家貴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不得安生,那就是我們所說的厲鬼。日本鬼的造型是頭上長角,手持鐵棒,繫一條虎皮兜襠布。陰陽道的鬼出入鬼門,位於丑寅方向,丑牛寅虎,所以鬼的模樣是牛頭虎軀,後來從簡,只剩下牛的兩只或一只角和虎的一小塊皮。神、鬼、精、妖,統稱為怪,神被人好生供奉,人死變鬼,其他東西則修煉成精,不明不白的歸為妖。德川家康以下四代幕府將軍的侍講林羅山從中國《搜神記》等志怪、傳奇書籍摘編《怪談全書》,於一六九八年刊行,「志」、「傳」變為「談」。天下太平,人們就想辦法自己嚇唬自己,江戶年間尤盛行怪談,就是鬼故事。如今我們把怪談這說法拿了來,鬼故事也大大地(東)洋氣。
日本人有聚堆兒的習性,聚在一起吟連歌或連句,聚在一起修茶道,下班不回家聚在一起喝酒,當經濟大發展時就叫做團隊精神並大加贊揚。聚在一起開故事會,講鬼故事,叫「百物語」。關於百物語的起源有種種說法,其一說是用來試武士等年輕人的膽量,是膽大包天或膽小如鼠。實際上能否讓人聽得毛骨悚然,也得看主講的口才。為什麼叫百物語,怎麼個開法呢?
一六六六年刊行的《伽婢子》(「伽婢子」的詞義是驅鬼護身的布娃娃)說到百物語:古來講鬼故事,講到滿一百個,鬼就出現了。明治文豪森鷗外寫過一個短篇小說《百物語》,言道:「聽說百物語就是很多人聚集,豎一百根蠟燭,一人講一個鬼故事就滅掉一根蠟燭。」可一屋子人,再豎起蠟燭上百根,這說法令人起疑。果不其然,杉浦日向子做了一番考證,寫在了《怪談》這篇隨筆裡:「在裝滿油的碟子裡放上一百根燈芯,呈放射狀,罩上燈罩,把一百根燈芯全部點燃。」講一個故事拔去一根燈芯,當第一百根燈芯熄滅時鬼就從黑暗中出來了。
有畫為證。河鍋曉齋畫的《百鬼畫談》(一八八九年刊行)起首是百物語的場景,只見一燭高檠,一人像公鴨一樣張大了嘴,比比劃劃,周圍老少男女做驚恐狀,又一人爬去拔油燈的燈芯,看來到蠟炬成灰,燈芯也拔得所剩無幾。不過,這卷畫的結尾是紅日高照,鬼們做鳥獸散。
畫百鬼容易,畫一人難。日本自古有畫鬼的傳統,漫畫也算是畫鬼起家。最古老漫畫《鳥獸人物戲畫》(國寶)用擬人化手法畫兔、蛙、猴嬉戲,已經是動物成精的意思。十二世紀的《餓鬼草紙》(國寶)用平安時代末葉的六道輪迴思想畫餓鬼慘狀。京都真珠庵所藏《百鬼夜行繪卷》是室町時代(十六世紀)製作的,各種傢伙什兒成精作怪,縷縷行行。喜多川歌麻呂的師傅鳥山石燕一七七六年刊行《畫圖百鬼夜行》,墨色,說明寥寥,這類妖怪圖鑒不大有故事性,而大阪浮世繪師竹原春泉一八四一年刊行《繪本百物語》,套色印刷,有桃花山人撰寫的詳細解說,以致通稱為「桃山人夜話」。圖文並茂,但不知先有文後配圖,還是先有圖後配文,杉浦日向子繼承了這個流脈,而圖與文都出自她一人之手。
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畫過「百物語」,惜乎僅五幅傳世。漫畫家杉浦日向子的《百物語》在雜誌《小說新潮》上自一九八六年,連載八年。她也是江戶社會和江戶文化的研究家,讀一冊江戶年間的通俗讀物需要一個月,為把時間用在這上面,只好放棄畫漫畫,所以《百物語》是日向子最後的漫畫作品。刊登在文學雜誌上,不消說,這個漫畫作品具有文學性,或許譯成「連環畫」更符合我們的傳統感覺。
把百物語怪談記下來,彙編成書,濫觴於一六七七年刊行的《諸國百物語》。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御伽百物語》、《太平百物語》、《新選百物語》、《怪談百物語》等紛紛上市,風潮與江戶時代相始終,在日本文學史上定型為近世怪談。講鬼故事,起初講一些從中國舶來的東山狼、狐狸精。京都本性寺住持淺井了意將明人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余話》改編成《伽婢子》,是為中國志怪系統的怪談的嗃矢,對後世影響甚巨,而百物語怪談可算是國貨。除了《諸國百物語》,以及近代彙編的《古今實說 幽靈一百題》和《古今怪異百物語》,其他輯錄沒有收足一百個故事的。畢竟都怕鬼,百物語講到九十九個就收場,亮著一根燈芯,不許鬼出來,人們去夢裡自編第一百個故事。杉浦日向子的百物語怪談多數從江戶時代的怪談隨筆中選材改編,也是九十九為止。看畫讀文字,日向子《百物語》似倒行逆施,固然有點害怕,卻也有點笑人,彷彿聽完一段便點亮一根蠟,最後心裡亮堂堂。
創辦《文藝春秋》雜誌的文壇大老菊池寬於一九二七年召集柳田國男、芥川龍之介等人開座談會,柳田主談,悠然道:「近來東京的怪談是僅僅一百年以來的發明。和以前怪談的類型不同。怪談這東西不是逐步發展,好像有時代的地層,畫段落地變化。就是說,好像怪談的天才不出來,怪談也不會漸漸地驚人。」杉浦日向子是製造當代怪談熱的天才之一。莫非受柳田這番話啟發,東雅夫寫了一本《為什麼怪談每百年流行一回》,說妖魔鬼怪橫行,其實這種現像不僅是平成的現代,戰前、更往前的江戶時代也有過,每隔一百年便出現非常相似的時代,可真是奇妙。
上一波怪談熱是明治三十年代到大正時代的十幾年間,大約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二年。作家寫,畫家畫,藝人演,而且當作了一門學問悉心研究,成果有柳田國男的《遠野物語》、井上圓了的《妖怪學講義》等著作。據說柳田國男寫《遠野物語》是受了怪談熱的刺激,與其說是民間傳說集或者民俗學的書,不如說是怪談采風錄,但後來他被立為民俗學鼻祖,人們有意無意地避開怪談之「俗」。三島由紀夫從怪奇幻想文學的角度贊賞過《遠野物語》,或許問題在於民俗「傳說」與文學「怪談」的歸屬。更早些的有小泉八雲的《怪談》,幾乎成為怪談代名詞。泉鏡花的《怪談會》、內田百閑的《冥途》以及岡本綺堂的《青蛙堂鬼談》等,文化人談鬼說怪,一時間蔚為大觀。
關於怪談與文學,三島由紀夫在評論內田百閑的文學時這樣說過:「英國詩人阿瑟‧西蒙斯說:『文學裡最容易的技術是讓讀者流淚,和引起猥褻感』。把這句話和佐藤春夫的『文學的精粹在於怪談』之說對照,就明白百閑的文學質量什麼樣。即,百閑文學不讓人流淚,不引起猥褻感,而是暗示人生最深處的真實,另一方面鬼氣的表現很高超。這意味著當代頭一號反骨文學家全部摒棄了文學的捷徑,求取最難事,而且成功了。」
再上一波怪談熱是在德川幕府第十一代將軍的治世,十九世紀初葉的二十多年。怪談讀本有山東京傳的《櫻姬全傳曙草紙》、曲亭馬琴的《南總里見八犬傳》、鶴屋南北的《東海道四谷怪談》,而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語》被譽為「整個日本文學史上最優秀的怪異小說」。
◊ ◊ ◊
講鬼故事需要黑暗或背景的配合,谷崎潤一郎從陰翳看出美,但通常人們只覺得鬼影幢幢。恐怖的快感造成暫時的忘我,使人從日常中解放,幾乎是其他娛樂難以取代的。夏夜宜講鬼,那麼,斗轉星移,到了漫長的冬夜呢?吉林農村到了大地一片白茫茫的寒冬就要「貓冬」,炕頭熱烘烘,我們的遣悶就是聽老農講故事。女生佯作沒聽,講的人卻不時拿眼瞄她們,並不回答男生似懂非懂的問話,好像樂在講給女人聽。不是鬼故事,而是「性」,完全不用「情」來遮遮掩掩,對於我們這些看見驢發情大叫驢腸子掉下來了的「知青」來說,那真是學校裡不曾學到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