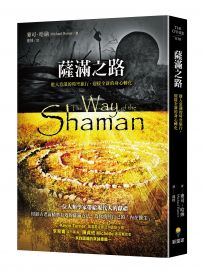【第三版前言】回到薩滿的宇宙之愛中
這本書的初版付梓至今已經十年,這些年對薩滿(Shamanism)的復興來說,是一段相當輝煌的日子。在這之前,由於部落人民及其古老文化受到傳教士、殖民、政府及商業活動的衝擊,薩滿正快速的在地球上消失。然而,在過去十年中,薩滿以驚人的力量回到人類生活中,就連紐約和維也納這些西方「文明」的都市堡壘,也不例外。這股復甦潮的湧現其實相當隱微,乃至大多數民眾可能根本還不知道有所謂薩滿的存在,更別說是察覺到它的重返。儘管如此,仍然有另一群人,在美國海內外快速增加了成千上萬,不僅接受了薩滿,還將薩滿融入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親身實證的薩滿方法
由於薩滿的復甦使許多在外旁觀的人感到困惑,因此,我想在此提出幾個促使薩滿復甦的要素。人們對薩滿的興趣與日俱增的原因之一,是許多受過教育、有能力思考的人,已經揚棄了信仰年代(the Age of Faith)。他們不再依賴教會的教義和權威當局來為自己提供有效證據,證明靈性領域,甚至是靈的存在。互相矛盾的二手或三手軼事,來自過去和遠方受到文化牽引的宗教經典,這些都不再足以做為個人存在的範型。他們要求更高水準的證據。
「新時代」(New Age)某些部分也可歸為科學時代(the Age of Science)的支脈,它將兩個世紀以來,在嚴謹科學方法的運用下所產生的範例,帶入個人的生活中。這些科學時代的孩子(包括我自己),對現實的本質與極限,寧可擁有屬於自己的第一手親身實證過的結論。薩滿為這些個人的實證提供了執行的管道,因為它是一種方法,而非宗教信仰。
科學時代創造出迷幻藥(LSD)。許多接觸薩滿的人,都曾經透過非正式的致幻性藥物的「經驗」來進行「實驗」。事後發現找不到可以為這些經驗定位的架構或準則,他們想在卡斯塔尼達(Castaneda)的書和其他書籍中,為自己的經驗找到指引的地圖,最後才意識到神祕的製圖法原來就在薩滿之中。
科學時代也創造出大量的瀕死經驗(near-death-experience,簡稱NDE),這是因為最新的醫藥科技,使數百萬美國人得以從臨床上已經定義為死亡的狀態中被救活。雖然瀕死經驗並非事先計畫的,但結果不僅檢驗並往往改變了瀕死經驗存活者過去對現實和靈性存有的假想。於是這些人也開始搜尋地圖,並且在尋找的過程中,轉向古老薩滿的方式。
為身心問題找到全新的解決之道
薩滿的方式,需要的是專注力與目的性的鬆緩紀律(relaxed discipline)。一如多數的原住民部落文化,現代薩滿通常會使用單調的打擊聲進入「意識的轉換狀態」(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這種典型不使用藥物的方式非常安全。參與者若是無法保持專注與紀律,只會返回正常的意識狀態,不像致幻性藥物,必然會經過一段意識狀態轉換的時期。
除此之外,典型薩滿的方式成效快得驚人,幾小時之內就能獲得人們或許要花上幾年時間靜心、祈禱或吟頌才能取得的經驗。單就這個理由,薩滿就非常適合現代人忙碌的生活方式,正如它也很適合愛斯基摩人(因努伊特人)一樣,因為他們白天的時間全都用來執行為了生存必須完成的工作,夜晚就可用來進行薩滿活動。
促使薩滿復興的另一個原因是全人健康(holistic health)取向這幾年的發展,這種取向積極透過心智的力量來協助療癒、維護健康。許多在全人健康領域的新時代修煉(practice),展現出人們正透過新的實證,重新發現過去在部落和民俗療法中廣為人知的方法。薩滿是一種系統,它能讓這個古老知識具體的呈現,因此有越來越多人,在為身心─情緒等健康問題尋找新的解決之道時,開始注意到薩滿。薩滿長期以來使用的某些特定技巧,例如:改變意識狀態、減壓、想像、正向思考,以及求助於非尋常資源(nonordinary sources)等,都在現代的全人健康照護中被廣泛運用。
與地球親族共存的靈性生態學
薩滿在今天會引起廣大興趣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薩滿是一種靈性生態(spiritual ecology)。在全球環境危機四起的此刻,薩滿提供了以人為本的「偉大」宗教所欠缺的:那對地球上其他存在,以及地球本身的尊敬和靈性上的溝通。對薩滿來說,這並非單純的崇拜大自然,而是雙向的靈性溝通,藉此重建人類祖先過去與偉大的靈性力量和美麗的地球花園曾經擁有,如今卻已失落的連結。正如已故的傑出薩滿及比較宗教研究學者米西.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指,薩滿是最後一群能與動物對話的人類。確實如此,我還要更大膽的說,他們是最後一群能和大自然全體,包括植物、溪流、空氣與石頭對話的人類。我們靠狩獵採集生活的老祖先,深諳環境掌控生死的力量遠甚於人類,因此認為與大自然的溝通是生存的必要條件。
如今,我們也開始察覺,環境具有比我們還大的力量,足以掌控我們的生死。我們在極度粗暴無情的摧毀地球上其他物種,破壞空氣、水和土地的品質之後,才遲緩的重新察覺到,人類這個物種的終極存活,必須仰賴對整個星球與環境的尊重。然而,只有尊重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以親密且充滿愛的方式,與「所有親族」(all our relations)溝通,這是北美洲的拉柯塔族(Lakota)的用語,我們不能只和人類一族交談,還要與動物族、植物族及所有的環境元素,包括土壤、石頭和水進行溝通。事實上,在薩滿的觀點中,我們周遭存在的並非「環境」,而是親族。
踏上古老薩滿的途徑
今天,從蘇黎世到奧克蘭,從芝加哥到聖保羅,人們再度踏上古老薩滿的途徑,通常是透過鼓圈或定期聚會的練習與療癒團體的形式。這些都是自主性的團體,一如薩滿自遠古以來的方式,在小社群裡學習,幫助自己也幫助他人。如今,這些非正式的社群,已成為國際大社群的一部分,社群裡並沒有階級教條,就如同在古老部落的時代一樣,個別的薩滿旅人(shamanic journeyer)必須親自去發現靈性權威是直接存在於「非尋常世界」(nonordinary reality)之中
鼓圈通常一週或兩週在夜間聚會一次,成員從三人到十二人不等,引導者和鼓手由成員輪流擔任。透過合作方式,參與者不僅協助現場擊鼓,也為彼此和親友們執行薩滿工作。
還有一些人獨自運作,不屬於任何鼓圈,他們可以用光碟機、耳機、專為薩滿旅程設計的鼓聲光碟等。若是使用得當,錄音的鼓聲也能產生驚人的效果(詳見附錄A)。光碟搭配其他科技和各種方法,也可以運用在所謂「薩滿諮商」(shamanic counseling)的問題解決系統上。
這些新的薩滿實踐者在運用本書,以及我在薩滿訓練工作坊中所強調的核心薩滿或基礎薩滿的技術時,並不是在「假扮印第安人」,而是在走向部落薩滿自古以來就持續造訪的那個能為我們揭露一切的靈性源頭。他們不是要假裝成為一位薩滿;他們在過程中,如果為自己和他人達到薩滿工作的成效,他們就是真正的薩滿。他們的經驗是真實的,和沒有文字的部落文化中的薩滿描述的內容,在本質上是可互相交換的。他們所做的薩滿工作內容是一樣的,人的身心靈也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文化背景。
在實踐薩滿的旅途上,他們發現許多人所描述的「實相世界」(reality),只觸及宇宙宏偉、力量與奧祕的表層而已。這些新的薩滿實踐者在經歷與重述自己的經驗時,往往會狂喜到流淚。他們以同理之心與經歷瀕死經驗的人交談,在他人感到絕望之處看到希望。
他們發現隱藏在宇宙中無與倫比的安全感和愛之後,往往會產生轉變。在旅程中不斷經驗和遭遇到的宇宙之愛,越來越頻繁的出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就算是單獨一人,也不會覺得孤獨,因為體會到:我們從來就不曾是孤身一人。如同西伯利亞的薩滿所說:「一切存有,皆活著。」無論走到哪裡,他們都在生命、親族的環顧之中。他們已回到薩滿家族永恆的社群中,不再受空間與時間疆界的限制。
麥可.哈納
紐渥瓦克,康乃狄克州(Norwalk, Connecticut)
一九九○年春天
【第一章】從無神論的人類學家到學習薩滿(節錄)
我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間,第一次以人類學者的身分,長期在厄瓜多爾境內安地斯山脈東側森林中的印第安希瓦洛族(Jívaro)─或稱為恩祖利修爾族(Untsuri Shuar)──進行田野工作。當時希瓦洛人以如今已失傳的「縮頭術」和仍持續存在的密集薩滿修煉法聞名。我成功的收集到大量資料,但對薩滿的世界,仍然抱持著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兩年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邀請我前往祕魯境內的亞馬遜地區,進行一場為期一年的探查,研究烏卡亞利河(Ucayali River)地區科尼波族(Conibo)的文化。我接受了,很高興有機會能對亞馬遜河上游迷人的森林文化進行更多研究。科尼波的田野調查工作是在一九六○至一九六一年間進行。
我與科尼波族和希瓦洛族這兩次特殊的際遇,是我探索這兩個文化裡的薩滿方法的基礎。我想與你分享這些經驗,也許能將那不可思議的隱密世界中的某些訊息,傳達給薩滿探索者。
喝下死亡藤蔓
當時,我已經在座落於烏卡亞利河支流一處偏遠湖畔的科尼波村落中,住了將近一年,對科尼波文化的人類學研究進行得相當順利,但在設法發掘與宗教相關的資訊上卻一籌莫展。科尼波族人都很友善,卻不願意提及超自然現象。最後,他們說我如果真的想要學,就得喝下由有「靈魂之藤」之稱的死亡藤蔓(ayahuasca)製成的神聖薩滿藥汁。我既感到好奇又帶著不安的答應了,因為他們警告我這會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經驗。
村裡一位親切的長老,也是我的朋友--多馬士,隔天一早就到森林裡去砍一些死亡藤蔓。他出發之前囑咐我要斷食,只能吃清淡的早餐,而午餐得完全禁食。到了中午,他帶著足以填滿五十多公升大鍋子的死亡藤蔓和卡瓦葉(cawa)回來。熬煮整個下午,煮到只剩下約一公升的草藥汁,最後倒入舊瓶子裡冷卻。等到太陽下山,他說我們就要來喝掉它了。
印第安人把村裡狗戴上嘴套摀住,如此牠們就不能亂叫。他們告訴我,狗吠的噪音會讓喝下死亡藤蔓的人抓狂。孩子們也都被告誡要安靜,太陽下山之後,這個小社群就變得一片寂靜。
赤道短暫的暮色很快就由黑暗接掌。多馬士將瓶子裡三分之一的汁液倒入葫蘆碗中遞給我。每個印第安人都盯著我瞧。我覺得自己像是在希臘雅典同胞的包圍下,接過毒芹汁的蘇格拉底。這讓我想到祕魯人對死亡藤蔓的另一個稱呼:「小死亡」。我迅速喝下那碗味道奇怪且略帶苦味的草藥汁,等著多馬士喝下他的藥,但他卻說他決定不喝了。
族人讓我在公共屋舍巨大茅草屋頂下的竹子平台上躺下。村裡除了蟋蟀的唧唧鳴叫和遠方森林深處吼猴的嚎嘯聲之外,一片寂靜。
我抬頭凝視著一片黑暗,模糊的光線開始顯現。光線越來越強烈,越來越複雜,最後迸發成豔麗的彩色。聲音自遠方傳來,如瀑布般的沖擊聲越來越大,漲滿了我的耳朵。
幾分鐘前,我還有點失望,很肯定這草藥對我不會產生作用。此刻,水流沖刷的聲音淹沒我的腦袋,我感到下巴一陣發麻,麻木感延伸到兩側太陽穴。
頭頂上微弱的光線變得越來越明亮,逐漸交織成一片彷彿由彩繪玻璃拼成的幾何馬賽克天庭,明亮的靛紫色組成不斷擴張的屋頂。我在這片洞天中聽到水流的聲音越來越大,看見模糊的影像在移動。當眼睛似乎適應了黑暗時,移動的影像也隨之化成類似巨大遊樂園的場景,一個超自然的妖魔歡樂園。在中央,指揮所有活動,且盯著我直看的,是個咧嘴獰笑的巨大鱷魚頭,洶湧的水瀑自牠的大顎深處奔流而出。水位緩緩上升,上方的樹冠層也隨之升高,直到整個場景蛻變成單純的二元景象,藍天在上,碧海在下。所有的生物都消失無蹤了。
靈魂接引之船
我臨近水面,從這個角度看見兩艘奇怪的船前後漂盪著,穿越空中朝著我漂浮而來,越靠越近。兩艘船慢慢結合成一艘;船首是個巨大的恐龍頭,和維京海盜船很像。船中央張著方形船帆。船身在我的上方輕柔的前後擺盪,我逐漸聽見一陣有節奏的嗖嗖聲,察覺到那是一艘大帆船,上面有幾百隻槳正配合著聲音的節奏前後划動。
我也察覺到這輩子聽過最美麗的歌聲正從大帆船上傳來,無數的聲音形成一種來自天堂般的高調。我仔細看著甲板,看見為數龐大的人形,他們有冠藍鴉的頭和人類的身體,就像是古埃及石墓中彩繪的鳥頭神。在這同時,某種能量體(energy-essence)開始從我的胸膛浮起,朝船上飄去。儘管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是個無神論者,此刻卻對自己正逐漸死去,而這些鳥頭人是接引我靈魂上船的情境,感到深信不移。靈魂持續從我的胸膛流出時,我察覺到四肢逐漸麻木。
從手腳開始,我覺得身體正慢慢變成硬邦邦的水泥,動不了,也說不出話。麻木感逐漸逼近我的胸膛,朝心臟而來,我試著開口求救,向印第安人要解藥。然而,不管我怎麼努力,就是無法有效的說出一個字。同時間,我的肚子似乎變成石塊,我也耗費了極大的力氣讓心臟保持跳動。我開始稱心臟為朋友,我最親愛的朋友,用僅存的力氣對它說話,鼓勵它繼續跳動。
我也有意識的察覺到自己的大腦,感覺到它在肉體上已分割成為四個分離而獨立的層次。在最上方的表層,是觀察者與施令者,那是身體狀態的意識所在,負責試圖讓我的心臟繼續跳動。它有所感知,但純屬旁觀者,意識著從大腦下層發散出來的影像。我感覺到緊鄰著最上層的下方是麻木層,它似乎被我喝下的藥汁給關閉了,覺得它就是不在了。再下一層是我看見的影像(包括靈魂之船)的來源。
這下子我肯定自己就快要死了。就在我試著接受命運安排時,大腦更下一層開始傳輸更多的影像和訊息。我被「告知」這些新素材之所以會呈現在我面前,是因為我正在死去,因此可以「安全的」接收這些揭示。訊息告訴我,這些祕密是保留給正在死去和已往生的人。我對於這些思緒的傳達者只有模糊的印象:許多巨大的爬蟲類生物,慵懶的靠在我後腦杓深處和脊椎的交會處,而我只能在陰沉黑暗的深處模糊的看見牠們。
來自黑色生物的啟示
接著,牠們在我面前投射出栩栩如生的場景。首先,牠們讓我看到億萬年前還沒有任何生命存在的地球。我看見一片海洋、荒涼的陸地和明亮的藍天。接著,成千上百的黑點從天而降,掉落在我面前的荒涼土地上。我看出這些「黑點」其實是閃亮巨大的黑色生物,有形似翼手龍的粗短翅膀和鯨魚般的龐大身軀。我看不見牠們的頭。牠們劈里啪啦的落下,這段旅程使牠們精疲力竭,而在地球上休息了億萬年。牠們透過某種思想語言告訴我,牠們正在逃離太空中的某種東西,到地球來是要躲避敵人。
這些生物向我展現牠們如何在地球上創造生命,好在無數的形體中躲藏,藉此隱匿牠們的存在。動植物的創造和物種形成的壯觀景象,以難以言喻的規模鮮活的展現在我面前。我得知這些恐龍般的生物存在於所有生命之中,包括人類。牠們告訴我,牠們是人類和整個地球真正的主人,我們人類只不過是這些生物的容器和僕人,因此牠們可以從我的內在對我說話。
這些從我腦袋深處湧現的揭示,和漂浮船的影像交錯出現,它就快收完我的靈魂了。載著冠藍鴉頭船員們的這艘船逐漸遠離,拉著我的生命力,朝一個兩岸荒涼殘破的大峽灣前進。我知道我只剩下片刻可活。奇怪的是,我對這些鳥頭人絲毫不覺得恐懼;只要他們能把我的靈魂留住,我很樂意讓他們取走我的靈魂。但不知怎麼的,我擔心我的靈魂恐怕無法停留在峽灣的水面上,透過某種未知的方式,我感受到並很擔心自己的靈魂會被深淵中的恐龍狀生物掌握或收回。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