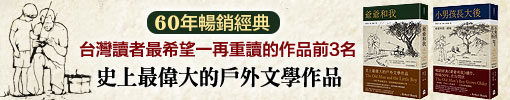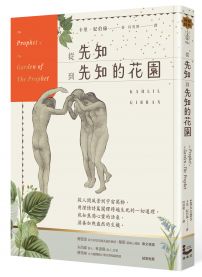先知話語中的對立與合一
諮商心理師/鐘穎
還有人不認識紀伯倫嗎?還有人未曾翻讀過《先知》嗎?他的話語早已滲透了這個世界,哪怕您可能是初次聽見他。
這本小書的結構簡單,第一部《先知》談的是先知阿穆斯塔法即將返鄉,返鄉前,這個他曾居住了十二年的小鎮居民央求他分享他這些年來所領悟的真理。而第二部《先知的花園》則是阿穆斯塔法返鄉後的故事,他回家後沒多久再次離去,這次他不知所蹤。他的去來正應了《福音書》裡的那句話:「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因為他們看得太遠,愛得太深,以致於忽略了自己走得太快的步伐。
紀伯倫是否以阿穆斯塔法自況?他不被理解的哀傷說明了我們心中永遠有兩種需求在激盪:歸屬感與自我實現。作為凡人的先知同樣深陷這種兩難,一方面我們需要親友家人的撫慰與肯定,一方面我們又需要追隨內心的指引,最大程度地成為自己。無論我們滿足哪一種,都會因為失落了另一種而哀傷。
這再度說明了人的衝突本質,而紀伯倫在書裡也多次暗示我們內在固有的對立:陽光與陰影、母親與孩子、聖人與罪人、正直者與墮落者,甚至直接以〈快樂與悲傷〉、〈罪與罰〉、〈理性與感性〉作為書中的篇名。
換言之,阿穆斯塔法的深邃並不是表現在神秘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而是表現在對衝突的意識,他看見的不是「道」,而是心理學家榮格所稱的兩極(opposites)。他清楚地意識到萬物總是彼此依存,「所有一切,都相依相生」。
人之所以能獲得超脫,是因為我們願意看見和接納自身的對立面,它會擴大我們對世界的覺知,總而鬆動我們對世界舊有的假設。換句話說,關注陰影(shadow),會為人帶來「腦內風暴」。而我們想追求的超脫,必須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達成。
因此,我們見到的其實是一個迥異於禪宗的傳統,禪宗公案中常出現「喝」與「棒」來當作止息提問者妄念的手段,但紀伯倫提供的路徑卻很不同。他的詩句裡大量採用了自然風景,諸如:風與海,花與鳥,土地與天空。他不截斷思緒,而是提供象徵。又有誰不被這些景物給感動呢?紀伯倫的詩之所以是跨文化的,正因為他所使用的象徵是跨文化的。
讀者同樣會注意到,他若在此處提及上帝,便會在他處提及「內在更偉大的自己」。很顯然,他並不認為上帝是自外於人的存在,相反地,祂映照著人人共通的大心,或者榮格心理學所說的自性(Self)。只有能觸及內在神聖的人,才會在外界看見神聖。只有深知自己是神聖一份子的人,才會將他人視為神聖。大心連結著彼此,從而使渺小的我們變得永恆。
紀伯倫的詩句因此處處透露著榮格的洞見,也處處反映著自性的靈光和他個體化(individuation)路上的風景。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明白何以在《先知》與《先知的花園》兩篇詩集裡,率先發問的都是女性,前者是女先知阿米特拉,後者是他小時候的女玩伴卡麗瑪。
用榮格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她們是阿穆斯塔法的引路神(psychopomp),帶領他從異界返還人世,她們也是男性心中的靈魂(anima/阿尼瑪),阿穆斯塔法因此才能從雙唇中吐出智慧的語言。同樣地,當紀伯倫在此處提及神時,也會在他處提及「人」。「他人便是你更寬闊的道路。」因此他要我們把鄰居當成彼此的神。但他人雖是道路,生命卻只能自己獨享。
就是這樣彼此矛盾的話語,讓許多讀者百思不得其解紀伯倫的意思。如果你也有類似的感受,那麼這正是他想達成的效果,他不要你拘泥於文字,不要你的心中滿是信條,卻沒有真正的信仰。
他為此感到哀傷,榮格也為此感到惋惜。我們是如此看重對錯黑白,看重非此即彼,從而讓生命失去流動性,並輕易而唐突地評價他人,引發許多痛苦的紛爭。因此書裡才特別指出,到達彼岸的途徑從來不是知識,也不是領悟。而是在這兩者之間,「有一條秘徑,你必須找到,才能與全人類合為一體,從而與自己合而為一。」
這種對人心的「宗教性」,而非對實體宗教的強調,正是本書的特色。有意思的是,它也是佛教的特色。「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就我來看,《金剛經》與紀伯倫的意旨,並無二致。
每年我都會和學生分享這本小書,我不厭其煩地告訴他們,日後的人生若是遇見了困惑,身邊有人可以請教最好;如果沒有,那就回來翻讀《先知》與《先知的花園》吧!裡頭的東西或許你暫時還不明白,但時間將教會你一切,這本書也會幫助你成為一個成熟且有智慧的大人。都說紀伯倫的文字是黎巴嫩獻給西方世界的禮物,但我想多數人同樣贊同,這本書更是獻給每個人的甘泉。特別是那些對傳統宗教與哲學感到煩膩的人們,它將會是你探求生命之謎的最佳嚮導。
二十年過去了,它依舊在我的書架,陪伴著我在現實的大地歌唱,在想像的天空中遨翔。請讓本書一起陪伴著你,那將流傳千古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