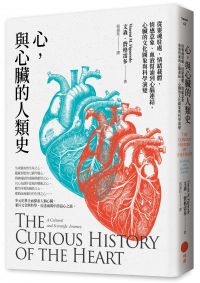英格蘭國王查爾斯一世(King Charles I)湊上前去,把三根手指和拇指放入那名年輕貴族左胸內的大洞,輕輕碰觸了那人跳動著的心臟。
「會痛嗎?」他問道。
「完全不會。」年輕人答道。
一六四一年,查爾斯一世經由御醫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獲知了這項奇蹟──沒錯,威廉‧哈維正是透過科學方法,呈現出心臟在整個人體的血液循環中扮演著何種角色的第一人。查爾斯一世聽聞這消息後興致勃勃,便問哈維自己可否會一會這名十九歲的年輕人,也就是愛爾蘭蒙哥馬利子爵(Viscount of Montgomery in Ireland)之子。
這名男孩在十歲騎馬時因馬兒絆跤而墜馬、摔上尖石,以致貫穿、撞碎了身體左側的多條肋骨,之後傷口化膿、癒合,在他的左胸留下了一個洞。九年後,這名貴族不僅安然無恙,還遠赴歐洲大陸向想一睹活人心臟跳動的人們展演,所到之處座無虛席,成了一位遠近馳名的人物。後來他返回倫敦,哈維便偕同英王一同檢視這名年輕人,並寫道:「我在不冒犯一名年輕又精力充沛的貴族之下,觸弄了其跳動中的心臟與心室,因而得出結論,即心臟毫無感覺。」
有史以來,人類一直都把心臟視為感覺的中心,所以心臟對實際的碰觸竟無所感,這實在非常諷刺。人類自有記錄思想以來,多數文明都深信心臟乃是人體中最重要的器官,而非大腦。沒錯,古人清楚他們胸口的跳動在在昭示著生命──害怕或渴望時跳得更猛、更快,然後一旦死亡,便戛然而止。數千年來,埃及人、希臘人、中國人與美索亞美利加(Mesoamerica)的特奧蒂瓦坎人(Teotihuacan)都把心臟提升到今日大腦所占居的地位,亦即靈魂、情緒、思想與智能之所在。翻遍史書,多數社會也都認為人是透過心(臟)連結上帝,而上帝更是依據人終其一生刻劃在心牆上的善與惡,來衡量其有否機會蒙主護佑、臻得永生。
一六四一年,哈維表示心臟扮演著血液循環的幫浦,這為之後數百年帶來了延續性的影響。醫生與科學家改變了他們原本對心臟的看法,任由大腦取而代之,慢慢成了主宰、蓄藏情緒及感知的唯一部位。如今,大多數人都深信人體──包括心臟的功能在內──皆由腦部掌控,外界也一直教導我們心臟僅是一只幫浦,藉著循環系統將血液推送至體內各處。
正因我們逐漸接受心臟只是幫浦的概念,便判定把某甲的心臟移植到某乙體內在道德上並無疑慮,只不過偶爾還是會發生類似克萊兒‧希爾維亞(Claire Sylvia)的案例。克萊兒‧希爾維亞原是一名專業舞者,曾進行心肺移植,而捐贈心臟的,正是一名因機車車禍亡故的十八歲男子──提姆‧拉米蘭德(Tim Lamirande)。在心臟移植後,朋友都說克萊兒走起路來開始像個男人,還大啖啤酒、雞塊,這些都是她在心臟移植前最厭惡的。提姆的家人則說,這些都是提姆才會做的事,對於克萊兒的行為舉止,他們一點兒也不意外,因為她的體內目前放的可是提姆的心臟啊。英國女演員珍‧西摩爾(Jane Seymour)在二○一三年所主演的電影《陌生人之心》(Heart of a Stranger)正是以這故事為主題,而外界也確實記錄了各式各樣的言論,表述人只要接受過心臟移植,便承繼了捐贈者的人格特質。這些故事不禁教人思忖,心臟究竟只是機械性的幫浦,還是承載著人性中的情緒。
身為心臟學家,我固定都會碰上一些彰顯「生理之心」和「情緒之心」密切相關的案例。我看過原無心臟病史的患者在驟失所愛之後心臟病發;也有其他患者在個人支持的隊伍於全美超級盃(Super Bowl)或世界盃(World Cup)點球大戰輸掉後心肌梗塞或猝死;我還經常目睹相守一生的伴侶在幾個月內相繼逝世。即便有這麼多案例當前,加上心臟與情緒長年來互有關聯,近代醫學卻對這樣密不可分的關係不以為意。透過本書,我不但詳述歷史、解釋何以如此,更揭示近代科學是如何啟發我們應去重新審視那些歷史上無從查考的事實。
近期的醫學科學發現,心臟可能有感,實際上還是「心腦(雙向)連結」(heart-brain connection)的一部份。研究顯示,心臟指揮腦部的程度,就跟腦部指揮心臟的程度相當,沒有分別。這方面的最新研究或許正是科學面臨轉變的開始,而這樣的轉變,正好符合了歷史與近代文化對心臟抱持的觀點。心臟可能不再僅被視為幫浦,反而再度受到認可、被視為情緒活力(emotional vitality)的一部份,確保我們身心靈的健康。
當大腦發出訊號,第一個回應訊號的器官就是心臟──想一想「戰鬥或逃跑」(fight or flight)的求生本能吧。當你在林間漫步,途中殺出了一頭獅子,大腦便會激活交感神經、啟動即時反應,讓身體不是準備立定戰鬥,就是拔腿狂奔;大腦告訴心臟馬上跳得快些、強些,向全身肌肉輸送充氧血,好準備行動。當心臟發出訊號,第一個接收訊號的也是大腦。若非如此,當我們猛地起身,就有可能暈倒在地。起身時,心臟及其周邊的大血管會警示大腦,血量及血壓正在下降,大腦於是加以回應,啟動血管收縮,以防血液集中流入雙腿。
我們在腦內意識到的情緒也會對心臟帶來廣泛的影響。一看到新戀人而引發臉紅、發熱、心跳加速等生理上的感覺,在在都是心臟回應的表徵。這種相互依存的「心腦連結」對人類的健康至關重大,而也正是如此,致使人類數千年來,皆把情緒、理智與靈魂置於這個熾熱、搏動,象徵著我們正活著的器官。古中國人及古印度人雙雙強調,快樂的心(臟)代表著身強體壯、長命百歲;古埃及人則把大腦視為一團灰冷的布丁、純粹只是生成黏液的器官,他們在對屍體進行防腐時,會用長鉤伸入鼻腔,掏出腦部組織。
時至今日,腦部取而代之,成了人類感知的所在,但心(臟)卻仍在人類的文化圖象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你只要從手機簡訊上看到情人傳來的表情貼圖,或在汽車保險桿上看到愛心符號,就能意識到心(臟)如今在生活中扮演的要角──至少,就象徵意義上是如此。心(臟)一直是浪漫、愛情的象徵,直到最近,心形圖案更成了健康、活力的符號,為眾人所熟知。我們仍會情緒飽滿地說「我全心愛著你」、「你觸動了我的心」、「她令我心碎」,也會斷言「他真是鐵石心腸」,甚至還會央求別人「有點同理心吧」;「她發自內心地說」帶有情真意切的味道;「回心轉意」暗示著和解或悔恨,而提到智能,我們則會以「用心背誦」來表達。一說到「我」,這究竟是指身體的哪個部位?即便心臟扮演的要角一直廣泛地分布在人類代代相傳的文化圖象、詩歌與藝術中,近代醫學卻仍駁斥「心臟蓄藏著靈魂、智能與感受」的概念,人們也多半忘了心臟以往所佔據的地位。
縱使醫學如此進步,全球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死於心臟病,且相較於各種癌症,未來將會有更多人死於心血管疾病。在美國,每四十秒就有一人死於心肌梗塞,女性死於心臟病的人數更是乳癌的十倍,而引發人類當前健康危機的前三大因素正是心臟病、憂鬱症與壓力,對此,我們為何不綜合審視,並施行交互治療呢?
相較於醫學中的其它領域,二十世紀的心臟病學走在了創新的尖端,到了二十一世紀尤有甚之。在二十世紀,我們見證了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以導管進行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coronary balloon angioplasty)與血管支架置放術(stent)、心律調節器(pacemaker)與心律去顫器(defibrillator)、心臟輔助器(heart assist device),以及心臟移植等發展。如今,有一半的美國人同時具有一個以上的心血管危險因子,如吸菸、高血壓、膽固醇等等。由於旨在減少上述危險因子的預防性保健措施已經有效幫助降低心臟病的死亡率,所以自一九六○年代起,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已獲大幅下降,只不過,心臟病仍是全美人口的第一大殺手。
我深信,為了改善人類全體的心臟健康,有一部分的答案在於更加瞭解心臟的文化史及科學史,及其過去如何逐漸與大腦區隔,從而退居劣勢。如今心臟是一只「可取代」的器官。倘若心臟已經衰竭的病患正在等待器捐,捐贈的心臟又未能立即到位,醫護人員便可於病患胸口植入機械性的幫浦,取代心臟功能。目前科學家也正在觀察如何從個人的細胞培養出一整顆立體、全新的心臟,來取代原本衰竭的心臟。由於人體捐贈的可用心臟短缺,科學家更持續研究是否可將豬隻等其它動物的心臟植入人體。此外,很快的,按基因篩檢結果所衍生出的個人化的醫療也將依據個人特有的基因風險,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接受心臟病的評估與治療。
我此生泰半都在研究心臟、照護心臟,這迫使我不得不拉長時間軸,綜觀心臟在整個人類史上所曾涵蓋的意義。我在本書中探究了心臟和大腦間的角力如何形塑出目前人類在文化、科學上對「心腦連結」的理解,追蹤了自兩萬年前人類古文明萌芽至今,人們對心臟的瞭解如何演變(詳圖0.1~圖0.3),並深入檢視人們對心臟功能的看法一路如何發展,乃至日後如何影響我們領略心臟究竟承載了哪些生命力。我們一向都認為心臟是人體的中心──其實人體的中心落在臍下近骶骨(sacrum)處──但心臟又是以何為中心呢?
我回顧了人類的先祖是如何看待這個奇妙的器官:古往今來,我們曾崇敬心臟、以其為尊,也曾曲解心臟,直到逐漸揭示其真實的樣貌。放眼史書,心臟一直都在詩人、哲人和醫者之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史前人類,歷經古代社會、黑暗時代、文藝復興,乃至近代,心臟在不同的文化都有著不同的意義。我且依時序一一檢視這個五臟之「主」是如何漸漸遭人摒棄,淪落成一只屈從於大腦、僅僅泵送血液的機械性幫浦──即便它依舊代表愛與健康,扮演著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核心。作為一名醫生,我對這個獨特的器官醉心不已,因而納入了另一部分獨立說明心臟的功能及其相關的疾病。另外,我更探討近代在心臟治療上的進展以及未來可能的光景。我們所正學到的,在在彰顯了人類的先祖對心臟的理解終究沒有錯得那麼離譜。
我「全心全意地投入」本書,甚盼你就和我一樣,覺得這本稀奇古怪的心臟史引人入勝、精彩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