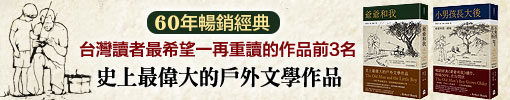龍樹(Nāgārjuna,約西元150年) 的《中論》(Mūlamadhyamakakārikā;MMK)是印度佛教中觀學派(Madhyamaka school)的根本典籍,內含二十七章,全由偈頌組成(譯按:本書依據原書之英譯頌文,以白話文譯出)。龍樹試圖在此書中確立中觀要旨:一切事物皆是「空」(梵śūnya)的,也就是缺乏自性(梵svabhāva)。「諸法皆空」這個主張,最早出現在總稱為「般若波羅蜜多經」(Prajnāparamitā)的初期大乘經典的佛教傳承中,而般若經系大約始於西元前一世紀。此前的佛教思想是基於一個比較特定的主張──「人空無自性」,也就是沒有獨立存在且恆存的自我,「人」是概念的建構;體悟「人空」被視為解脫輪迴的關鍵。最早出現的大乘經典大幅超越這個主張,斷言不只是「人」(還有諸蘊聚合的實體,例如車輛),一切皆空無自性。不過,雖然這些大乘經典主張「諸法皆空」,卻沒有為此辯護。龍樹《中論》的任務,就是為這項主張提供哲學上的辯護。
《中論》與四部論注
《中論》和其他相同性質的文本一樣,往往以極為精簡的形式呈現論證,也因此不依賴注釋便很難理解,這是此類文本的特質和著述目的所致。所謂「論頌」(梵kārikā),是一種偈頌體的著作,言簡意賅地闡述某項學說(通常是哲學義理),換句話說,「論頌」是由偈頌組成的作品。運用這種形式的著作,原本是因為以偈頌體呈現,比較容易將資料牢記在心。每個偈頌的結構是四個音步(分別以a, b, c, d指稱),每個音步有八音節,這種偈頌造成的規律節奏就成為記誦的一大輔助。但另一方面,由於偈頌體的限制,以致很難清楚闡述且充分辯解複雜的哲學論點。然而,這種文類的作品並非以此為著述目的,原本似乎是期望弟子能牢記這些偈頌,並且在師父面前背誦,以示對內容的嫻熟,然後逐頌聽聞師父對內容的詳盡解說。日久歲深,各個師父所作的解說最終被人以散文體記錄成書。原先的偈頌加上注釋,這兩者合併正是為了詳盡闡述與辯護作為議論焦點的哲學論題。牢記偈頌讓弟子有必備的綱要,以便鉅細靡遺地記住注釋中詳述的思辨系統。
據我們目前所知,《中論》在印度的注釋書共有四部:(一)《無畏論》(Akutobhayā,作者不詳);(二)佛護(Buddhapālita)所作的《中論注》(Madhyamakavṛtti。以下簡稱《佛護注》);(三)清辨(Bhāviveka)的《般若燈論》(Prajñāpradīpa。以下簡稱《燈論》);(四)月稱(Candrakīrti)的《淨明句論》(Prasannapadā。以下簡稱《明句論》)。這些注釋書對於每一頌的詮釋並非完全一致,其中有些注釋書會針對特定論點提出較詳細的解說。但這四部注釋書對於偈頌的論證,以及每一章破斥哪些特定的觀點,還有其他諸如此類的事項,大體上是吻合的。若是沒有這些資料,任何人都可以天馬行空地解讀這些偈頌,提出各種不同的詮釋。當然,我們無法確定傳統印度的注釋書中哪一部忠實地反映出龍樹的本意,但如果我們自詡比這些注釋者更了解龍樹,那就未免太自以為是了。
本書譯本以注釋書為依據
我們的《中論》譯本即以這些注釋書為依據,而且不僅限於梵文模稜兩可時英文譯詞的抉擇問題,許多偈頌的英譯內含一些補充資料,置於方弧中,那是原來梵文偈頌沒有出現的字詞,但是如果不添加這些字詞,根本無法解讀偈頌。方弧資料的補充,是因為注釋書有指明偈頌省略的部分。顧及前述韻文格式造成的限制,偈頌本身有這種省略是可以理解的,應該附帶說明的是,我們已經儘量減少以方弧補充譯文的情形。換句話說,在「偈頌本身」的內容詮釋上,我們一直採取相當開放的態度。若從上下文可明顯看出梵文偈頌有哪個字詞為求精簡而被省略,我們就直接添加相對應的英文譯詞,而不加方弧。不過,如果有讀者想核對我們的英譯忠於梵文原文的精確度,或許可以查閱這個譯本稍早發表於《印度與西藏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Tibetan Studies)的版本,該文在方弧的使用上,更符合嚴謹的學術風格。
我們並未翻譯任何注釋書,而是根據上述四部《中論》注釋的經典之作,針對英譯的偈頌,逐一提出我們自己的注釋。我們盡可能地減少主觀詮釋,在解說時,絕大部分是根據至少一位注釋者所言,少有踰越之詞。我們希望一旦適當地闡述偈頌背後更大的脈絡,論證本身就能得以自行發言。對於龍樹的整體立場,以及他原本打算讓論證發揮何種作用,每個人都有各自偏好的觀點,但我們一直儘量避免讓這個譯本成為鼓吹這些個人觀點的工具。
《中論》的每一章皆針對一個特定教義或概念加以觀察,這些教義或概念通常是某個佛教論敵的主張。從目前所用的文本看來,並沒有明確的線索足以判定龍樹是否訂定每一章的章題,而且即使他的確為各章下標題,當初的章題是什麼,我們也不得而知。大體而言,我們沿用月稱注釋書中的章題,但有些章節採用其他注釋書的章題,因為我們認為如此一來更能彰顯其中的內容。
《中論》論敵所持的見解
現在,針對龍樹造論的目的和策略作一些整體介紹,應該不致太過突兀。龍樹《中論》的對談者是佛教內部人士(另一部公認為龍樹著作的《迴諍論》[Vigrahavyāvartanī],其主要談話對象也包括非佛教的正理派[Nyāya school])。特別重要的一點是,龍樹的造論對象所持的見解,是基於阿毘達磨(梵Abhidharma)體系背後的基本假設。阿毘達磨是佛教哲學傳統的一部分,其目的在於填補「無我」、「無常」、「苦」等佛法要義背後的形上學細節。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的阿毘達磨部派,就是因為對這些細節產生重大的爭議。然而,這些部派卻有一套共同認可的基本假設,或許可以粗略勾勒如下:
一、某一項陳述的真偽,可以由「世俗」(conventionally)和「勝義」(ultimately)兩方面來檢視。
(一)說某項陳述在世俗上是真實的,亦即世俗諦(conventional truth),等於是說以世間之認可為基礎的行為,必然導致暢行無阻的慣例。我們對自身和世界的常識性信念大多是世俗諦,因為這些信念反映出一般公認有用的日常慣例。
(二)說某項陳述在勝義上是真實的,亦即勝義諦(ultimate truth),等於是說它與真實(reality)的本質相應,而且不主張也不預設有任何純粹「概念上的虛構」(conceptual fiction)存在。所謂「概念上的虛構」,意指那些僅僅是與這些概念使用者的我們有關,以及我們碰巧使用的概念,因而被視為存在的事物。例如,「車」是一個概念上的虛構物。當一組零件以正確的方式組合時,我們僅僅因為它是和自己興趣相關的事實(我們對促使交通便利的組合物有興趣),以及自身認知的局限(由於有限的認知,我們很難羅列所有零件和一切零件的組合),而相信除了零件之外,還有車的存在。勝義諦是絕對客觀的,它反映世界的真實面貌,不受恰巧對我們有用的因素所影響,沒有任何與「車」相關的陳述在勝義上是真實的(或不實的)。
二、只有諸法(dharmas)在勝義上是真實的。
(一)說某件事物在勝義上是真實的,等於是說關於這類事物可以在勝義層次上陳述它是真實(或不實)的。勝義真實的實體(entity)有別於純粹概念上的虛構物,因為前者可以被視為獨立存在,不受與我們相關的事實所影響。
(二)勝義真實的諸法是結構簡單或不可分割的,它們不是心智為求概念精簡而聚合(aggregate)為整體的習性所造成的產物,而是這種心智活動的所有產物經過層層分析,最終分解而餘留下來的基本成分。它們可能包含諸如下列類別的事物:不可分割的物質微粒、時空上各自獨立且具有形色的事物、痛覺、飢餓、口渴等基本欲望的特別情況,或剎那的意識。(各個阿毘達磨部派所陳述的「諸法」,內容多少有些差異。)
(三)關於人、城鎮、森林、車等構成的常識世界(commonsense world),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事實,都可以完全以諸法和諸法彼此關係的角度來解釋。換句話說,世俗諦可以完全以勝義諦的角度來加以解釋。
三、諸法依賴眾因緣而生起。
儘管並非所有阿毘達磨部派都認為一切法皆依賴「緣起」(梵pratītyasamutpāda),卻一致公認諸法大多數是如此。另外,既然凡依賴緣而生起者,亦依賴緣而滅盡,大多數(或一切)的「法」都是無常的。
四、諸法具有自性。
(一)所謂「自性」,是一種特性或屬性,是持有此屬性者本身固有的。換句話說,一個實體以某屬性為特徵的這項事實,不受其他任何事物的相關事實所影響。
(二)只有諸法具有自性。一輛車的大小、形狀不是它的自性,因為這輛車具備的大小、形狀取決於它的零件大小、形狀和組合。車的大小、形狀是「他性」(梵parabhāva;extrinsic nature),因為它們不是車本身「自有的」,而是從其他事物挪用而來的。
(三)諸法只具備自性。某件事物的某個特徵只能藉由和另一件事物的關係而得來(例如,「比勃朗峰更高」),這就不是此物固有的特徵。但之所以依然會推斷此物具備這個特徵,這是要讓內心的造作(mental construction)在我們建立真實事物的概念過程中發揮作用,因為我們需要推斷某件事物可以有複雜的本質,也就是它具有自性(排除其他一切事物之後,它自己的本來面目),外加與其他事物的關係而造成的種種特性。一件事物的本質得複雜到這種程度,才會被心能聚合的習性建構成為概念。
(四)任何一法都只有一個自性。既然諸法是分析到最後所剩餘的成分,而且分析拆解了內心所造作成的聚合物,所以任何一法只能有一個自性。
五、滅苦之道是最終能領悟關於我們自身和世界的勝義諦。
(一)苦的起因是以為有恆常的「我」這種不實的信念,也就是誤以為有恆存的經驗主體和行動執行者,生命中的種種事件因此主體而可能產生意義。
(二)這個不實的信念來自於不能看清人只是概念上的虛構物,其實並無自性,勝義真實只是一切諸法的因果相續。滅苦之道,是最終以真正客觀的方式看見真實,也就是不在世間投射任何概念上的虛構物。
龍樹不否認部派所述的諸法,但他卻不接受這些敘述引申的寓意──諸法事實上是存在的。龍樹所持的立場是,如果有勝義真實的事物存在,那就是諸法──具有自性的事物;但事實上不可能有這種事物。不僅人和其他可分解的事物因為缺乏自性,都只是概念上的虛構物,諸法也是如此。說一切事物皆空,即是此意。
由於這個主張的本質,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單一論證可成立此主張。這樣的「主論證」(master argument)勢必得根據事物勝義自性的相關主張,既然成立這種主張所需的是勝義真實,就涉及對某種自性的支持。龍樹的策略卻反而檢視認為有勝義真實的實體者所提出的種種主張,並且試圖顯示其中沒有任何主張可能為真。《中論》注釋者甚至在每一章開始引言時,提出論敵對前一章結論所作的反駁。這種作法是希望論敵一旦看到本身的基本主張被駁斥的數量夠多,就會承認繼續發掘勝義諦的企圖大有可能徒勞無功。
《中論》常見的推論模式
這種期待,有一部分是基於龍樹在反駁時所運用的一些常見的推論模式。人一旦看出某個推論策略如何用以駁斥若干相異的假說,就比較容易明瞭同樣的策略,也可能運用在自己對某個形上學議題的偏好見解。以下是《中論》特別常見的推論模式。值得注意的重點是,對論敵而言,每一項被駁斥的假說都是勝義諦。
一、無窮後退(infinite regress):
這種推論的用意是彰顯假說H不可能為真。因為導出H的推論如果運用在H本身,會進而導出另一項假說H’,運用在H’本身,則會導出H”,如此推演無窮無盡。但是提出H是為了解釋某個現象P,而完善的解釋應該止於某一點,不能無限推論。因此,H不可能是P的正確解釋。關於此類推論的例子,詳見【2.6】(譯按:即指第二章.第六頌,餘以此類推)、【5.3】、【7.1】、【7.3】、【7.6】、【7.19】、【10.13】、【12.7】、【21.13】。
二、不一不異(neither identical nor distinct):
這種推論旨在駁斥「x和y以某種方式R產生關連」之類的假說。如果這種假說成立,則x、y必定全然相異,或實則為同一物(只是用兩種不同的描述)。然而,若x、y相異,則兩者獨立存在,沒有交集;若x、y各自獨立存在,則R不是x的特徵,因此「x和y之間具有關係R」不可能是勝義諦。反之,若x、y完全相同,則x和自身具有關係R,但這是荒謬之論。以「R是起因」的關係為例,「某一事件可能肇因於自身」的想法是荒謬的。關於此類推論的實例,詳見【2.18】、【6.3】、【10.1–2】(譯按:即指第十章.第一頌至第二頌,餘以此類推)、【18.1】、【21.10】、【22.2–4】、【27.15–16】。
三、三時(the three times):
這種推論的用意是駁斥「x具有某種屬性P」之類的假說。欲使這項假說為真,x必須在過去、現在、未來三時中的任一時具有P。但根據《中論》論證,基於種種理由,「x在任何一時具有P」不可能為真。第三種可能性,亦即「x現在具有P」,通常略而不論,因為沒有迥異於過去、未來的「現在」;換句話說,「現在」只是一個點,沒有持續期,我們視之為一段延續的現在時刻,是從過去和未來建構出來的概念。不過,有時第三種可能性被排除,是因為勝義真實的諸法必定是不可分割的單一元素。關於此類推論實例,詳見【1.5–6】、【2.1】、【2.12】、【2.25】、【3.3】、【7.14】、【10.13】、【16.7–8】、【20.5–8】、【21.18–21】、【23.17–18】。
四、反自反性(irreflexivity):
這種推論的運用,通常是在論敵藉由主張「實體x與其自身具有關係R」,以試圖防止無窮後退論證的情況。根據反自反性的原理,一個實體不能對自身起作用,通常援引以為佐證的例子,包括不能自斫的刀,以及不能指向指頭本身的手指。龍樹在【3.2】、【7.1】、【7.8】、【7.28】運用且證實這項原理。
五、非互易性(nonreciprocity):
這種推論旨在駁斥「x、y處於相互依賴關係」之類的假說。所謂相互依賴,即是x以某種方式依賴y,而y也以同樣方式依賴x。此類推論實例詳見【7.6】、【10.10】、【11.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