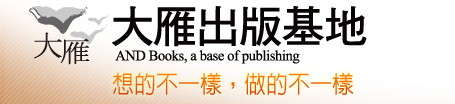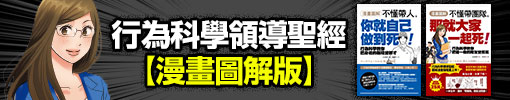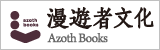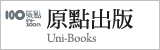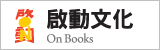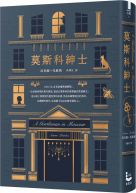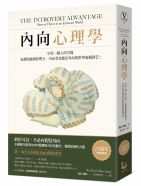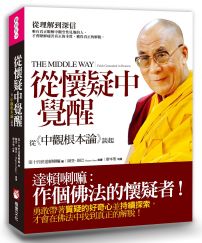第1章 趨向甚深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時、此地,人類在物質發展和各種領域的知識方面已經達到高度發展的階段,而且我們仍在這些領域持續地進步中。但是,需要我們關注的事物卻永無止盡,而在這樣的氛圍下,對於佛教徒而言,以理解(understanding)和論理(reason)為基礎,而對佛法獲得真正的信心,這是很重要的。
基於真正理解的信心
我們要如何獲得一個基於「理解」的信心呢?就像我在〈吉祥那爛陀寺十七位大班智達祈願文〉的後記中所寫的:我們應該以帶有好奇、懷疑的客觀心態,去從事謹慎的分析並尋找理由。然後,基於所見的這些理由而引生由智慧所伴隨的信心。
現在,無論什麼時候,當我們進行任何分析時,例如關於心的本質或實相,假如我們從進行的一開始,就已經說服自己「這一定是如此這般」的話,由於這個偏見,我們將無法看見真正的真理,反而只會看到自己內心幼稚的投射。因此,在進行分析時,試圖讓心態保持客觀且不受成見所左右,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一顆帶有懷疑的好奇心,我們的心在各種可能性之間游移,真誠地去追問它是否如此,或者還有其他可能。我們必須盡可能客觀地進行分析。
然而,即使我們保持一個不受偏見所動搖的客觀態度,但是對於分析卻沒有感受或興趣,這也不對。我們應該培養探索所有可能性的好奇心,而當著手去做時,想要深入探究的欲望自然便會產生。假如缺乏這種想要嘗試各種可能性的心,我們便會放棄探索,並且只會輕蔑地說「我不知道」這樣的話,而這不會帶來實質的利益,因為我們並沒有用開放的心態去接受新的洞見。
因此,好奇、質疑的態度非常重要。因為只要存有這樣的質疑,便會持續地追究下去。科學進步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它持續不斷地質疑探究,並且基於「它為什麼會像這樣」的真正客觀態度,帶著嘗試各種可能性的好奇心而進行實驗。透過這種方式,真理會變得愈來愈清晰,人們才能正確地理解它。
「謹慎的分析」指出了粗略或不全面的分析是不夠的。例如在佛教邏輯與認識論典籍所提出的分析方法中,憑著「僅僅基於事實的片面觀察」、「於同類事物中額外觀察到這個事實」,或基於「在任何異類事物中僅僅沒觀察到這個事實」等論證,這是不夠的。基於片面的理由,並不足以推出你的結論。佛教邏輯和認識論典籍強調,要論證一個主張為真理,必須建立在植基於直接觀察的健全論理。透過謹慎的分析,我們的結論才會更穩固且更周延。
當我們更清楚並瞭解典籍當中所提出的論理時,必須把這些回歸到自己個人的經驗上。而最究竟的證明,則是直接有效的經驗(現量的經驗)。
佛教典籍提到「理智」分為四種類型或特性: 卓越理智(great intelligence)、迅捷理智(swift intelligence)、清明理智(clear intelligence)與洞察理智(penetrating intelligence)。因為我們必須謹慎地分析對象事件,因此需要「卓越理智」。除非基於精密地分析,否則我們不能輕易地遽下「某事就是如此」的這種結論,因此我們需要「清明理智」。因為我們必須能夠獨立思考,因此需要「迅捷理智」。而且因為我們必須要探究序列問題的完整含義,因此需要「洞察理智」。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分析,並且從自己的理解中尋求可以推導出來的結論與意義(重要性),我們將會看到那些結果。在此,我們首先必須有系統地組織典籍當中提出的論式,並和自己個人的經驗連結,如此一來,這個論理便可以受到直接觀察與經驗證據所支持。當我們把這些論式連結到自己個人的經驗時,便會覺得「是的,它們真的很有幫助」,或「這真的非常好」。這時,我們對於佛法的信念便已經獲得確定了,這樣的信心可稱為「基於真正理解的信心」。
分析的順序
至於從事分析的實際順序,我在〈吉祥那爛陀寺十七位大班智達祈願文〉第2偈寫道:
通達事物本質二諦義,
四諦確定輪轉與還滅,
由量所引堅信三皈依,
奠定解脫道本祈加持!
透過理解二諦(事物的存在方式),
我將確定我們如何經由四諦而於輪迴中流轉與還滅,
我將更堅定由理解(量,有效認知)所引生的對於三寶的
敬信,
惟願加持解脫道的根本能深植我心!
在此,當談到修習佛法時,我們所要談的是,在尋求解脫的脈絡底下,遵守斷除十種不善行的倫理道德標準,並且培養悲心與慈心。光是禁絕十種不善行,或是培養悲心與慈心,並無法構成佛法獨特的修習之處,因為倫理道德與悲心的修持,畢竟是許多精神傳統都共有的特質。當我們在這個脈絡底下談到佛法時,「法」(Dharma,或精神方面的事物)一詞所指的是「涅槃」(nirvana)或「解脫」的寂靜,而且是指「決定勝」(definite goodness),它兼含「解脫輪迴」與「成佛的圓滿覺悟」兩者。我們使用「決定勝」一詞,是因為涅槃的寂靜是全然殊勝、清淨且恆久的。當避免無益身心、傷害他人的行為並培養慈悲等這樣的修習,是希冀從輪迴三有中證得解脫的一部分時,它們才真的成為佛教徒精神活動那層意義的「法」。
「解脫」(liberation)在此的定義是:透過運用相應的對治力去滅除心中的染污。主要的染污(我們尚未覺悟的這種存在狀態的根源)就是對於「我」(selfhood)或自我存在(selfexistence)的執著,以及伴隨執著自我存在而來的所有相關的心理與情緒因素。直接對治我執的心及其相關心理因素的方法,便是洞悉「無我」(selessness)。因此,基於對「無我」的領悟,我們才能獲致真正的解脫。
上述便是如何證得「決定勝」的方法,而連繫證得這種解脫的精神方法,則是佛教獨一無二的方式。因此,我寫道:「奠定解脫道本祈加持(惟願加持解脫道的根本能深植我心)。」
解脫道的根本:四聖諦
現在,為了把解脫道的根本深植我們心中,就必須瞭解四聖諦。四聖諦就像佛陀所有顯密兩種教法的基礎,當他第一次對最初期的弟子教導佛法時,所教導的便是四聖諦。
假如我們去深思佛陀教導四聖諦的方式,就會看見他首先描述它們的特徵或本質,其次是功能,第三則是一旦直接證悟它們(現觀)時,我們將會經驗到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在佛教教法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基」(ground,基礎)、「道」(path,道路)和「果」(result,結果)這三個主要成分的討論。瞭解實相的本質是「基」,而「道」的追求(實踐)則是基於對「基」的瞭解,而最後所經驗到的「果」,則是開發「道」的結果。
﹝基的階段:﹞佛陀關於四聖諦的教法,是對實相真正本質的一種描述。當佛陀教導四聖諦時,他是以描述它們的本質作為開始,他說:「這是苦聖諦,這是苦集聖諦,這是苦滅聖諦,這是道聖諦。」透過這樣的方式宣說諸諦,佛陀說明有關事物存在的方式,他是在描述「基」的本質。
現在,在佛陀的第一苦聖諦當中,他所說的「這是苦聖諦」包含了所有折磨我們的苦。其中,有許多不同的細微層次,不僅有明顯的疼痛和艱辛之苦,而且還有我們經驗當中,更深沉且涵蓋更廣的特性〔,這些也是苦聖諦〕。「這是苦聖諦」這句話,可讓人辨認到所有這些經驗都是無法令人滿足的,或處在苦的本質當中。
在第二諦中,「這是苦集聖諦」這句話說明了導致苦或構成苦的來源之因。即使「集」(苦的根源)本身也是苦的一種形式,因此可被包含在第一諦中,此處是以「因」和「果」的方式來分辨並描述「苦」和「集」。再次地,佛陀確認主要的苦因就是對於自我存在的執著,也就是扭曲我們對於實相的看法,並讓我們只連繫到令人困惑的表象,而非事物真正存在方式的根本無明。
在第三聖諦中,「這是滅聖諦」這句話說明了從苦解脫的本質,也就是苦的完全息滅,這說明苦因可以被刻意地終結。當這些苦因的種子變得愈來愈少而最終被根除時,那些原本會產生並被經驗的結果自然便不會出現。因此,這句話在此所要說明的是,我們的苦及其根源(集)終有一天可能完全止息。
要充分瞭解這種息滅的可能性,你不能只憑藉著自己對表象的理解,而必須更進一步透視它們真正存在的模式。你不能依賴一般層次的表象,因為它們是靠不住的。你的苦的核心根源—根本無明(即對於現象真正存在的模式或事物實際存在的方式,感到迷惑),它主宰我們目前每一剎那的經驗。
但是根本無明和心的光明本質並非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最終,無明和心可以被分離開來,無明並不是心的固有本質。因此,在第四諦中,「這是道聖諦」這句話是要說明透過某些方法,可以在我們的心續中實現寂滅。在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瞭解實相本質的智慧。為了斷除根本無明,我們開發「無我」的知識並觀修這個真諦。現觀「無我」之道,可以直接攻擊這個錯誤地認知「我」而受到蒙蔽的心,並且斷除它。以這個方式,宣說「道」的本質。
簡而言之,透過列舉四諦的特性,佛陀教導了「基」—事物真正存在方式的本質,這點可以透過底下的比喻來說明。例如當某人患了還能治癒的疾病時,便有疾病本身的苦、產生疾病的內外因素、治癒的可能性,以及對治病因並使其痊癒的治療方法或藥物。同樣地,有一條通往止息一切苦的道路。這就是「基」的本質—對於事物實際存在方式的瞭解。
沒有人會強迫我們追求安樂並試圖克服痛苦,而且我們不需要用邏輯去證明這兩種追求的價值,因為尋求安樂和規避痛苦的傾向,自然而然存在於我們所有人,甚至動物的身上。就像尋求安樂和避免痛苦的自然傾向是我們的實相的基本事實,同樣地,有因果關連的苦、集、滅、道四聖諦,也是實相的基本事實。
〔道的階段:〕現在的問題是「把這些事實作為基礎之後,我們要如何運用自己對於四聖諦──『基』──的瞭解?」要回應這個問題,佛陀回答:「辨認苦,斷除集,現證滅與修習道。」(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在他第二次列舉的四聖諦中,佛陀要教導它們的功能,即在我們心中實現它們所必須依循的過程。在基、道、果的三重解釋中,這是「道」的解釋。
現在,當我們徹底地辨認苦時,自然便會產生希望從苦當中脫離的想法。因此,透過「辨認苦」這句話,佛陀教導善加瞭解苦的所有粗、細層次的重要性。透過明顯之苦(evidentsuering,苦苦)、變異之苦(changeable suering,壞苦)和制約之苦(suering of conditioning,周遍行苦)這三個依次愈來愈細微的苦的差異性,來觀修苦。「明顯之苦」也稱為「苦苦」,它是顯而易見的疼痛與艱辛,這是世俗所定義的「苦」。「變異之苦」在世俗中被理解為安樂(有漏安樂),但是它的不穩定性和無常性,總是在最終時帶來痛苦。最細微層次的「制約之苦」,是受到無明所制約的一切苦、樂、捨經驗的核心特性。無論何時,無明都是〔影響〕我們覺知實相時的一個因素,而且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一直都是如此。然後,無論我們從事何種行為,以及擁有什麼經驗,都將被錯誤想法所產生的不安所扭曲。
一般而言,明顯之苦甚至連動物都能辨認出來,我們不需要特別去深思以便開發想要脫離它的想法。然而,明顯之苦是基於變異之苦而來,而後者又植基於制約之苦。因此,即使我們可以試圖並單獨去除明顯之苦,但是只要制約之苦還在,明顯之苦或許可以降低,但是無法被斷除。因此,要完全斷除明顯之苦,我們必須斷除制約之苦。「辨認苦」這句話的意義就是去辨認制約之苦。
同樣地,「斷除集」這句話的意義,就是去斷除一切苦的根本原因—根本無明。「現證滅」這句話的意義,則是去遮止苦及其根源。這就是我們所必須尋求且必然會渴望的最終目標,也就是前面提過的「決定勝」。
最後,「修習道」則意味著,所謂的「滅」必須在內心中實現,因此,我們必須培養那些將導致證得滅的因(道),必須把自己的理解付諸實修。提到未覺悟與覺悟的存在狀態(輪迴與涅槃)時,我們真正要談論的是兩種不同的心態。只要內心處在一個尚未覺悟、受到無明欺騙或蒙蔽的狀態,那麼我們便身處在輪迴或尚未覺悟的存在狀態。而一旦我們獲得洞悉實相真正本質的智見,並且看穿無明的虛妄時,覺悟的過程便由此開啟。因此,輪迴與涅槃或無明與覺悟,事實上是我們對於實相的究竟本質是否無知或具備洞見的作用(function)。前往覺悟旅程的核心便是要開展這個洞見。
簡而言之,佛陀在初次宣說四聖諦之後,接著教導如何運用它們,也就是解釋我們走上這個道路所必須依循的順序。佛陀教誡我們所要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辨認苦」。﹝果的階段:﹞佛陀詳細說明:「辨認苦,而沒有苦尚待辨認;斷除苦之集,而沒有苦之集尚待斷除;現證滅,而沒有滅尚待現證;修習道,而沒有道尚待修習。」透過這些敘述,佛陀提醒我們瞭解四聖諦如何能達到它的頂點—道的「果」(結果)。在此階段,我們不再需要辨認任何更進一步的苦,或者去斷除任何更進一步的苦之集,這個事實就是最終現證四聖諦。
這便是佛陀如何以基、道、果的觀點來展示四諦的情況。
當佛陀教導四聖諦時,他提到兩重因果關係,一方面是「苦」和「集」,而另一方面則是「滅」和它的因──「道」。第一重因果關係跟雜染(煩惱)的現象或我們在輪迴中受生有關,而第二重因果關係則與覺悟的現象或徹底斷除苦的狀態有關。雜染種類的因果關係是以無明作為根本,而覺悟的因果關係則透過根本無明的息滅或雜染因果的淨化來進行。在此,我們可以再次看到輪迴三有及其超越—輪迴與涅槃,是以瞭解或昧於實相究竟本質的觀點來定義的。而且我們再次看到輪迴和涅槃之間的差異,正是我們如何覺知實相的一個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