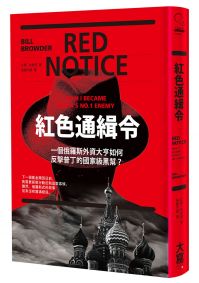紅色通緝令
RED NOTICE
〔定義〕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要求他國協助逮捕通緝犯時發佈的通報,其目的在於引渡罪犯回國。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是目前效用最接近國際逮捕令的手段。
1 不受歡迎人士
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是個重視數據的人,不如就從幾組重要的數字說起吧。這些數字分別是:260、1和4,500,000,000。
這三組數字各有代表的意義:每兩星期,我就必須從居住的城市莫斯科遠赴倫敦,回到我心目中的家。
過去十年來,我總共往返「兩百六十」趟,而讓我甘願遠渡重洋的唯「一」理由,就是探視我當時八歲的兒子大衛,他和我的前妻住在漢普斯特(Hampstead)。離婚時,我暗自許下承諾,無論如何,我都要兩個星期去看兒子一次。至今我仍未違背諾言。
我會定期返回莫斯科,則是為了「45億」的理由。這是我名下赫密塔吉資金管理公司(Hermitage Capital)所管理的總資產市值。我是公司的創辦人兼執行長,過去十年間,我幫許多人賺了大錢。二○○○年時,赫密塔吉擁有全球績效最佳的新興市場基金,這些基金的投資標的主要是俄羅斯這類開發中市場。自從一九九六年創立以來,我們為投資人賺進1,500%的獲利。事業的成功遠超過我最樂觀的預期。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曾擁有幾次金融史上最輝煌的投資機會,同時也是堅苦卓絕(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冒險,但其產生的龐大利潤也同樣迷人。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挑戰。
由於頻繁往返倫敦和莫斯科,對於旅途中的每個環節我都瞭若指掌:舉凡在倫敦「希斯洛機場」通過安全檢查需要多少時間、登上俄羅斯航空飛機需要多少時間、起飛需要多少時間,乃至於往東飛進籠罩著夜幕的國度需要多少時間,我都知之甚詳。若是在十一月中左右飛行,甚至可以感覺到飛機很快就進入另一個更寒冷的冬季。飛到另一座機場需要兩百七十分鐘,這段期間已夠瀏覽《金融時報》、英國版《時代》雜誌、《富比士》和《華爾街日報》,外加處理重要的電子郵件和文件。
飛機往上攀升之際,我打開公事包拿出準備閱讀的報章書刊。成疊資料、書報和封面光滑的雜誌之間夾著一個皮製小資料夾,裡面放了百元鈔票,總共七千五百元。我這輩子從未賄賂過任何人,但我總是隨身攜帶這筆錢,以備不時之需。這樣的話,萬一發生緊急狀況,我才能有更多機會搭上最後一班飛機離開莫斯科,就像昔日金邊或西貢陷入混亂和毀滅前倉皇逃出的難民,驚險脫困。
不同的是,我沒有逃離莫斯科,我仍然會回去。我得回去工作。因為這個緣故,我希望能利用飛行時間瞭解週末發生了哪些大事。
即將抵達目的地前,《富比士》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文章內容並非什麼投資機會或經濟新聞,而是某個人的專文介紹,而且主角和我一樣,都畢業於史丹佛大學MBA。他的名字叫邵裘德(Jude Shao),是晚我幾年進入商學院的美籍華人。我不認識他,但他跟我一樣,也是在異國功成名就的商人,直到他去了中國。
暫且不談他遭遇的複雜狀況,重點在於,他和幾名貪腐的中國官員發生衝突。一九九八年四月,他拒絕向上海稅務員繳交六萬元的賄款而遭到逮捕。最後他因莫須有的逃稅罪名,遭判處十六年徒刑。史丹佛校友組成遊說團體,試圖營救他出獄,但無功而返。我讀到文章的時候,邵裘德正在環境惡劣的中國監獄內受盡煎熬。
讀完文章後,我的心情陡然一沉。就做生意而言,中國比俄羅斯安全十倍。隨著飛機從一萬英呎的高空朝向莫斯科的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Sheremetyevo International Airport)降落,我一度有幾分鐘認為自己會這麼想實在很傻。多年來,我在投資上採取的主要策略是所謂的股東行動主義(shareholder activism)。在俄羅斯的投資環境中,這意味必須挑戰寡頭政治的貪腐作風,也就是對抗共產主義潰敗後據傳竊占國家百分之三十九財產而一夕致富的二十幾個寡頭執政者。這些寡頭掌控俄羅斯股市中絕大多數的上市櫃企業,並時常掏空這些公司。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能成功應付寡頭。雖然我的投資策略讓我的基金表現亮眼,但也為我樹立了不少敵人。
讀完邵裘德的故事後,我暗自思忖,或許我該就此罷手,我的人生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除了大衛之外,我在倫敦還有新婚妻子。艾琳娜是俄國人,美麗大方,聰慧過人,當時懷著我們的第一個小孩。或許我該放慢腳步,我在心中暗自想著。
這時飛機降落地面,我放下雜誌,將黑莓手機開機,關上公事包,開始查看電子郵件。我的注意力從邵裘德和家人以及寡頭政治,轉移到飛行時錯過的各種資訊。下飛機後,我必須先過海關,坐上自己的車,然後回到我住的公寓。
謝列梅捷沃機場是個奇特的地方。我最熟悉的第二航廈當初是為了一九八○年夏季奧運所建。當時啟用時一定光鮮亮麗,可惜到了二○○五年已飽經風霜,顯現出歲月痕跡。航廈內瀰漫著汗臭和廉價菸草味。天花板架著一排又一排的金屬圓柱裝飾,看上去就像生鏽的罐頭。護照查驗站前沒有正式的排隊動線,所以你必須在人群中站定位置,隨時提防有人插隊。就連提領行李也是曠日廢時,即使護照蓋上了入境章,你也必須再等上一個小時才能領到行李。在經過四個多小時的飛行後,以這種方式入境俄羅斯一點也不有趣,尤其對每隔一個星期就得體驗一次的人更是如此。
自一九九六年開始,我每次都以這種方式進入俄羅斯,直到二○○○年左右,有位朋友告訴我機場禮遇通關服務。雖然每趟必須多付一點錢,但卻能省下一個小時,有時甚至兩個小時。這一點也稱不上奢華氣派,不過每分錢都花得相當值得。
下飛機後,我直接進入貴賓室。那裡的牆壁和天花板全都漆成豌豆湯般的青綠色,地板鋪上亞麻油地氈。貴賓室座椅採用紅棕色人工皮革,已算是相當舒適。等待時,服務人員會送上淡咖啡或泡得太濃的茶。我拿了一杯附上檸檬片的茶,同時把護照交給移民官。不過幾秒鐘,我就可以開始專心處理黑莓機上成堆的電子郵件。
我的司機「阿列克謝」(Alexei)預先取得進入貴賓室的許可,但我幾乎沒有注意到他在什麼時候進來,並開始和移民官聊天。阿列克謝和我一樣也是四十一歲,但他身高一百九十五公分,體重一百零八公斤,金黃頭髮,五官深邃。他曾是莫斯科交通警察總警監,不諳英文。他一向準時,總能應付得了路上的交警,順利從車陣中脫身。
我一邊回覆電子郵件,一邊喝著手上微溫的茶,沒仔細聽他們閒聊的內容。過了一會,廣播系統傳來通知,我搭的航班可以提領行李了。
這時我才猛然回神,心裡暗想,我在這裡一個小時了嗎?
我看了看手錶。我的確已經等了一個小時。我的班機在晚間七點三十分左右降落,現在已經八點三十二分。同時進入貴賓室的其他兩名同班機旅客早已離開。我瞥了阿列克謝一眼,他用眼神告訴我,讓我確認一下。
他向機場人員詢問時,我撥了通電話給艾琳娜。當時倫敦只是下午五點三十二分,這個時候她通常都會在家。講電話的同時,我持續注意阿列克謝那頭的情形,他和移民官的談話一下子就演變成了爭執。阿列克謝拍了桌子,和櫃檯人員怒目相視。我告訴艾琳娜,「出了點問題」。我站起來走向櫃檯,準備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惱怒的情緒多於擔憂。
當我靠近櫃檯時,我才發現事態嚴重。我打開手機的擴音功能,讓艾琳娜替我翻譯。語言一向是我的罩門,即使過了十年,我還是只能在搭計程車時講上幾句簡單的俄語。
雙方的對話彷彿永無止盡。我像是網球比賽現場的觀眾,只能站在一旁觀看,並隨著對話來回轉頭注視說話的人。艾琳娜一度說道:「我覺得是簽證出了問題,但對方一直不說清楚。」此時,兩名身穿制服的移民官走進貴賓室,一個指向我的手機,另一個指著我的隨身行李。
我跟艾琳娜說:「這裡來了兩個移民官,他們要我掛電話跟他們走。我待會再打給妳。」
我掛上電話。一個移民官提起我放在地上的行李,另一個則從櫃檯拿回我的入境文件。尾隨他們離開時,我看向阿列克謝。他的嘴巴微開,顯得垂頭喪氣、意志消沉。他感到不知所措。他知道,一旦在俄羅斯遇上壞事,情況通常會糟到不能再糟。
我隨移民官走出房間,魚貫通過第二航廈的後門走廊,走向更寬敞的一般移民大廳。我用蹩腳的俄語發問,但在護送我到一般拘留室的路上,他們一句話也沒說。拘留室的燈光刺眼,樣式統一的塑膠排椅固定在地面上,牆上到處都是斑駁脫落的米黃色油漆。幾個遭到拘留的人神情不悅,懶洋洋地坐在一旁。沒人交談。每個人只是靜靜地抽菸。
移民官離開了。房間較遠的一端有個以玻璃隔開內外的櫃檯,裡面全是身穿制服的機場人員。我挑了附近一個較靠近櫃檯的椅子坐下,試著釐清當時的情況。
不曉得為什麼,他們讓我保留所有隨身物品,包括訊號還足以撥通電話的手機。我把這視為好的徵兆。我試著適應當時的處境,但腦中卻不禁浮現邵裘德的遭遇。
我看了看時間。晚上八點四十五分。
我回撥電話給艾琳娜。她的語氣聽起來並不擔心。她告訴我,她正在準備一份簡短的傳真,寫好後會傳真給駐莫斯科的英國大使館。
接著,我打電話給公司員工艾瑞爾(Ariel)。他是以色列人,曾在以色列秘密情報局(Mossad)擔任探員,現在是公司在莫斯科的安全顧問。他是國內公認的優秀安全顧問,我相信他能順利解決眼前的問題。
艾瑞爾聽到我的遭遇時非常驚訝,他說他要先撥幾通電話,稍後再給我答覆。
約莫十點半的時候,我撥電話到英國大使館,與我接洽的是領事處的克里斯.鮑爾斯(Chris Bowers)。他已經收到艾琳娜的傳真,對我的狀況略知一二,至少我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他重複確認了我的所有資料,出生日期、護照號碼、簽證簽發日期,毫無遺漏。最後他說,由於當時是星期日晚上,他能做的可能不多,但他會盡量嘗試。
掛上電話前,他問道:「布勞德先生,他們有提供您食物或飲水嗎?」
「沒有。」我答道。他咕噥了幾句。在衷心向他道謝後,我便掛上電話。
我試著在塑膠座椅上找到最舒服的姿勢,但依舊坐立難安。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站起來,在煙霧中來回踱步,試著不去看其他拘留旅客的空洞眼神。我開始查看電子郵件。我打給艾瑞爾,但他沒接電話。我走到玻璃隔間外,用不流利的俄語和裡面的辦事人員講話,但沒人理我。在他們眼中,我只是個不重要的路人;更糟的是,我已形同囚犯。
需要一提的是,俄羅斯是個完全不尊重人權的地方。人民可能因為國家需求而無故犧牲,成為人肉盾牌、交易籌碼或甚至棄如敝屣。若有必要,任何人都可能從世界上消失。史達林的名言形容得最為貼切:「沒有人活著,就不用擔心發生問題」。
這時我又不禁想起《富比士》中有關邵裘德的報導文章。我過去是否應該更加謹慎?我對應付寡頭和貪腐的俄羅斯官員早已習以為常,要是有人暗中指示,我也可能就此人間蒸發。在我的認知中,這是理所當然的下場。
我猛然搖頭,將邵裘德的身影趕出紊亂的心頭。我又走向櫃檯,試著從辦事人員口中問到相關消息,不管什麼都好,只是最後仍然無功而返。我回到座位,再次撥打艾瑞爾的電話。這次他接起了電話。
「艾瑞爾,有什麼進展嗎?」
「我聯絡了好幾個人,但無人回應。」
「無人回應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沒有人真正接起電話。比爾,我很抱歉,我需要更多時間。星期日晚上很難聯絡上任何人。」
「好,有任何消息立刻通知我。」
「沒問題。」
掛上電話後,我再次聯絡大使館。他們也沒有任何進展。他們開始敷衍搪塞,或是我的處境根本還算不上緊急狀況,抑或其實兩者都是原因。
掛電話前,領事人員又問了一遍:「他們有提供您任何食物或飲水嗎?」
「沒有。」我給了相同的答案。這問題表面上看來毫無意義,但顯然克里斯.鮑爾斯不這麼認為。他一定遇過類似情況,而這也不免讓我開始覺得,不提供食物或飲水其實是俄羅斯的典型作風。
過了午夜之後,拘留的人數越來越多。遭到拘留的旅客清一色全是男性,看起來都是來自蘇聯解體後獨立的國家,諸如喬治亞、亞塞拜然、哈薩克以及亞美尼亞。他們如果帶著行李,多半是簡便的旅行提袋,或是體積過大、以膠帶纏繞的奇怪尼龍購物袋。每個人菸不離手,有些人窸窣交談,但沒人顯露半點情緒或擔憂的神情。雖然我在他們之中顯然格格不入─身穿藍色西裝外套,手拿黑莓機,腳邊放著黑色拉桿公事包,顯然侷促不安─但他們就像那些辦事人員一樣,不太在意我的存在。
我再次和艾琳娜聯絡。「妳那邊有消息嗎?」
她嘆了口氣,「沒有,你呢?」
「也沒有。」
她一定從我的語氣中聽出我的憂慮,於是安慰說,「一切會沒事的,比爾。如果這真的只是簽證問題,你明天一定就能回來,到時就能弄清楚所有事情。我向你保證。」
她的冷靜沉著感染了我。「我知道。」我看了看手錶,英國已經晚上十點半。「去睡吧,寶貝。妳跟肚子裡的寶寶都需要休息了。」
「好,如果有任何消息,我會立刻打電話給你。」
「我也是。」
「晚安。」
「晚安。」我緊接著補上,「我愛妳。」但她已經掛掉電話。
心頭突然閃過一絲不確定感。萬一這不是單純的簽證問題怎麼辦?我還能見到艾琳娜嗎?我還有機會看到未出生的孩子嗎?我還能去看兒子大衛嗎?
我一邊壓抑這些負面想法,一邊用外套充當枕頭,想辦法在硬梆梆的椅子上平躺下來休息,但這些座椅的設計擺明就是為了防止讓人睡著,更別說周圍還有一群面露兇光的人。和這些人共處一室,我怎麼能安然入睡?
我睡不著。
我坐起身來,開始在黑莓機上打字,列出過去幾年在俄羅斯、英國和美國認識,且可能協助我脫離險境的人,例如政治人物、商人和記者。
大使館的克里斯.鮑爾斯在結束值班前最後一次和我聯絡。他向我保證,他會將我的狀況完整交接給下一個值班人員。他仍然想知道,機場人員有沒有提供食物或飲水給我。答案還是沒有。他向我道歉,但其實他也無能為力。倘若發生任何虐待情形,顯然他就會二話不說記錄下來。掛上電話後,我在心裡嘀咕,媽的。
當時大概是凌晨兩三點。我關掉黑莓機以節省電力,然後再度嘗試小睡一會。我從行李中拿出一件襯衫蓋住雙眼,乾吞兩顆布洛芬(Nurofen)消炎止痛藥,企圖緩解開始出現的頭痛症狀。我試著忘記這一切,嘗試說服自己明天就能離開這裡。這只是一般的簽證問題,不管如何,我都會安然離開俄羅斯。
過了一會,我漸漸失去意識。
我在清晨六點三十分左右醒來,拘留室中已經擠進新的一批旅客。他們的樣貌都差不多,但就是沒人像我一樣。周圍瀰漫的菸霧更濃,更多窸窸窣窣的低語聲。空氣中聞得到濃烈程度不同的汗臭味。我的嘴巴散發出口臭,而且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有多口渴。克里斯.鮑爾斯反覆詢問現場是否提供食物和水是有道理的。我們可以自由使用公共廁所,但這些混帳更應該提供所有人食物和飲水。
醒來後,我同樣抱持正面的態度,認為這只是官僚體制中的一場誤會。我打電話給艾瑞爾。他仍然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確實提到,下一班飛往倫敦的班機將在上午十一點十五分起飛。我只有兩種下場,不是遭到逮捕就是驅逐出境,因此我試著相信自己終究會搭上那班飛機。
我盡可能找事情做。我回了幾封電子郵件,和正常上班一樣。我打電話向大使館確認最新情形。新的值班領事人員保證,一旦開始辦公,他們會立即處理我的事情。我收拾好行李,不厭其煩地向辦事人員尋求協助。我試著向他們要回護照,但他們仍舊漠然以對,彷彿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坐在玻璃窗口後,對所有拘留者視而不見。
我開始來回踱步:九點整、九點十五分、九點二十四分、九點三十七分。我越來越緊張。我想打電話給艾琳娜,但倫敦的時間還太早。我又打電話給艾瑞爾,但他還是沒有問到任何消息。我不再主動對外聯絡。
到了十點半,我忍不住拍打玻璃,但裡面的辦事人員依然維持著最專業的姿態,對我視若無睹。
我接到艾琳娜的電話,只是這次她再也無法安撫我的情緒。她向我保證會釐清所有狀況,但我已開始覺得無所謂。邵裘德的身影再度從我的腦海中浮現,益發清晰。
十點四十五分,我開始驚慌失措。
十點五十一分。我怎麼會這麼愚蠢?我只不過是芝加哥南區的凡夫俗子,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在擺平一個又一個寡頭後,還能安然脫身?
十點五十八分。愚蠢,簡直愚蠢至極!自大又愚蠢,比爾!自大,蠢到不行!
十一點零二分。我要被關進俄羅斯監獄了。我要被關進俄羅斯監獄了。我要被關進俄羅斯監獄了。
十一點零五分。兩個穿著長統馬靴的航警突然闖進拘留室,直接朝我走來。他們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迅速收拾我的東西後,就把我拉出房間。他們帶我走到外頭,通過走廊,爬上一段階梯。這一刻總算到了。我即將被丟上囚車,送到遙遠的監獄,一定是這樣。
不過他們反而踢開一扇門,然後我們就置身在出境大廳,以飛快的速度前進。我們一路經過登機門和目瞪口呆的旅客,我的心臟跳得又急又狂。我們來到十一點十五分倫敦航班的登機口,他們領著我走過空橋、進入機艙,催促我快步通過商務艙,最後把我安置在經濟艙的中排座位。航警照樣不發一語。他們將我的行李放進頭頂的置物櫃中,沒有歸還我的護照就轉身離開。
飛機上的乘客無不盡力假裝不在意,但他們怎能不注意?我忽視旁人投射而來的目光,心想我終於不必進入俄羅斯監獄了。
我寄了封簡訊給艾琳娜,告訴她我已經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能見到她。我在簡訊中跟她說,我很愛她。
飛機起飛了。在輪胎猛然收進機身的那一刻,我頓時鬆了好大一口氣,未曾感到如此輕鬆。即使是賺賠幾百萬美金也無法比擬那種感受。
飛機爬升到巡航高度後,機上開始送餐。我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沒有進食。那天的午餐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俄羅斯酸奶牛肉,但卻是我這輩子吃得最津津有味的一餐。我又額外點了三份,喝光四瓶水,然後就不省人事了。
直到飛機降落在英國機場的跑道,我才轉醒過來。飛機滑行時,我在腦中盤算接下來即將面臨的所有程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沒有護照的情況下通過英國海關。不過這應該還算容易。自從我在九零年代末入籍英國後,英國就是賦予我公民身份的國家。比較棘手的問題還是俄羅斯。我要如何擺脫這淌渾水?誰要為這整起事件負責?我該向俄羅斯的哪些人求助?西方國家有誰可以幫我?
飛機靜止下來,機上廣播聲響起,乘客紛紛解開安全帶。輪到我離開座位時,我沿著走道走向艙門。當時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我朝出口一步步走去,並未注意到機長正站在機艙前方看著乘客下機。當我走近他時,他伸出手打斷了我的思緒。我注視他的手,他正拿著我的英國護照。我接過護照,一句話也沒說。
入境只花了五分鐘。我搭上計程車,直奔我在倫敦的住處。到家後,我給艾琳娜一個深深的擁抱。我從未對任何人的擁抱如此感激。
我告訴她自己有多愛她。她睜著明亮的雙眼,報以燦爛的笑容。我們牽手走向家中共用的辦公室,一路聊著發生的每一件事。我們坐到各自的書桌前打開電腦,拿起電話開始工作。
我必須找到回俄羅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