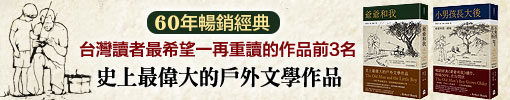前言:最弱的強者
這種事理應不該再發生的。二○一○年十一月,一個俄羅斯家庭正在慶祝新屋落成,這是位於葛林大街上、一棟令人自豪的磚瓦房。這家人以務農維生,做得有聲有色;庫雪夫斯卡亞(Kushchevskaya)是個安靜的城鎮,位於南方肥沃的黑土平原上。當天有很多事情值得慶祝,一家人能在國家團結日相聚,而家裡剛出生的寶寶還不滿一歲。當全家人圍坐在餐桌前,準備舉杯慶祝時,他們的看家狗被麻醉飛鏢射中了。就在此刻,有人闖進屋內。十一個武裝男子衝了進來,開始無情地屠殺每一個人。一開始是男人,然後是女人和小孩,先勒昏再刺死他們。轉眼間,餐桌旁就躺了十二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小孩。兇手把汽油澆淋在屍體上,點火燒了。兇手逃跑時,把屍體扔在九個月大的小女嬰身上,任她在火焰中尖叫、在濃煙中無法呼吸。隨後,兇手們在當地的速食店喝啤酒,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
面對這樣的慘劇,該州的首長只是聳了聳肩說:「很不幸地,在某種程度上,每個地區每個城市都有這樣的幫派存在。」
他說的對。這些人是非常普通的俄羅斯罪犯。他們不只是變態,還是與官員掛鉤的強盜,早已在這個國家中橫行霸道。他們的老大不是亡命之徒,是謝爾杰.查帕克(Sergey Tsapok),他本身就是法律;他是地方議員,與稅務機關、地方警察和檢察官關係密切,有關當局至少放過他上百次的罪行。他喜歡炫耀自己受邀過參加克里姆林宮的總統就職典禮。他宣稱自己曾經就在那裡,親眼目睹小孩被勒死。
這些謀殺者讓俄羅斯驚恐不安,因為他們嗅到了比謀殺小孩更壞的事──一個腐敗的國家。那位死去的農夫一直拒絕對查帕克繳交土地「貢金」。當查帕克勒索敲詐在地方上比他弱勢的人時,他勇敢站出來說話。但是這個國家已經被黑手黨滲透了,無力保護他。
讓我們回到莫斯科,政府正努力查出到底發生了什麼,試著安撫歇斯底里的輿論,但到最後發現,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說出真相、沒有一個地方官員是清白的。情況疑雲重重,國家又如此敗弱,克里姆林宮別無選擇,只好派檢察總長出馬,「親自」到場調查。
弗拉吉爾.普丁(Vladimir Putin)被迫承認在庫雪夫斯卡亞的「所有權力當局都失職了」。但這並不是單一事件。這些人只是普丁失職最新的受害者。普丁曾經承諾要用他所謂的「法律獨裁」和「垂直權力」來終結「狂野的一九九○年代」。但是他口中的穩定變成了腐敗。他的言論就等於承認了一九九○年代的貪污和無法無天還沒結束。像是憲法法庭大法官弗拉瑞.佐金(Valery Zorkin)這樣偉大的好人就嚇壞了。他曾如此寫到,「誠實地說,有人必須承認組織犯罪的疾病已經深入侵害了我們的國家。」「如果黑手黨不收斂,俄羅斯在十年後不知道還是否存在。」
本書想提出一個問題:為何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還會發生這樣的謀殺。我們如果想找到答案,不只要把審訊的大燈打在普丁的臉上,還必須調查這個國家和普丁的體制。為什麼普丁身為勝利的政治人物,卻無法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本書是要問,普丁統治的俄羅斯到底出了什麼錯,一個如此弱勢的國家如何設法從人民的身上偷走這麼多的東西,而他們又為什麼能允許這些事情發生。以前的書已經介紹過普丁體制的興起,而本書的目的是要開始講述它的衰敗。書中會探討一個搞砸的國家體制,不但沒有創造所謂的「法律獨裁」和「垂直權力」,反而顯示了慢慢解體的種子如何已經在普丁曾經無法挑戰的支持度中發芽萌生。
普丁的失敗已經把俄羅斯變成一個充滿龐大矛盾的國家。這讓社會現代化了,卻讓一個國家衰退了。這個國家更富裕了,卻也更分裂、更封建了。俄羅斯已經全球化,實質收入飆升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但是許多機關卻淪為詐欺和勒索的工具。本書將會調查人民如何看待這個國家的政治。莫斯科的億萬富翁人數已經超越紐約,在二○○○年至二○○九年的經濟成長的速度遠超過巴西,擁有歐洲地區最廣大的網路人口,也是全世界社交媒體最熱衷追逐的地方。但是二○一○年的數據警告,它就像巴布亞紐幾內亞一樣腐敗,著作權如肯亞一樣糟糕,而競爭力只能跟斯里蘭卡匹敵。
這是個憤怒又破碎的社會,但是這可不在普丁的規劃中。他提倡像是「我們的」青年運動的社會融合,還有像是「主權民主」的意識形態,然而這些都已經徹底失敗了。儘管如此,這個國家還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在新的教堂和超市裡找到自己。與此同時,一個扭曲的公民社會儼然成型,其中崇拜維持治安的權威,將腐敗的官員妖魔化。這個國家正在拉扯,正在受一場文化戰爭主宰,一邊是俄羅斯宗主教(宗主教又稱「大牧首」,高於主教)把普丁的時代稱為「神蹟」,而來自狂野的莫斯科地下社會的英雄──這是歐洲最嬉皮的地方,已化身爲「暴動小貓」的女生團體,成員們戴上色彩繽紛的頭套帽,在大教堂中念「龐克祈禱詞」。
然而,事情也不盡然如此。本書會探討為何普丁一度像真正的俄羅斯英雄尤利.加加林(Yuri Gagarin)一樣備受人民擁戴,在政治首都累積了巨大的財富,卻如此揮霍地一擲千金。我會提到,普丁找到一個複雜微妙的方法,可以同時實行「中央計畫型民主」又監控媒體,但他也會誘惑數百萬俄羅斯人民,告訴他們迫切地想要什麼的。但人民需要什麼,還需要他說出口嗎?書中也會解釋普丁的朝廷從一開始就有多麼地腐敗失能,但為何當他無法建立一個人民深切渴望、功能健全的現代化國家時,人民卻仍是支持他。
我曾經目睹普丁主義的巔峰。二○○八年年底在喬治亞,我看著俄羅斯軍隊在南奧塞提亞哀悼死者並慶祝勝利,此時「國家領導人」的支持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三。人民相信普丁已經恢復俄羅斯的霸權地位。但是到了二○一一年年底,我在莫斯科看到龐大的集會示威,抗議者要求他瓦解同樣的體制。他們認為普丁已經偷走了選舉,甚至整個國家。如此看來,普丁已經無法控制事情的發展了。
就在俄羅斯史上的這兩個時間點之間,這個政權的結局已經昭然若揭,也開啟了如今正在破壞它的機會。本書就是要講述這段時間的故事。書中會問到,為何普丁會揮霍他在二○○八年勝利之後如此令人炫目的支持度巔峰。書中也會提到,當示威者在二○一一至二○一二年冬天走上街頭,譴責他的政權是不合法的,稱之為「騙子和小偷的政黨」,普丁是如何堅守他如沙皇般的權力。
新的年代已經誕生了。老舊的普丁模式已經不管用了,而普丁主義正不斷地、慢慢地邁向終點。我為了理解俄羅斯的現況,從聖彼得堡旅行到海參崴(Vladivostok),試圖尋找普丁政權的結局,還有這個新年代的輪廓。我想認識反對勢力和他們令人不安的英雄。他們對於俄羅斯的未來做了哪些承諾和麻煩事?我試著解釋這個運動如何開始破壞這個政權,但這股力量可能不如期待中的強大。整個國家的不滿是如此龐大,抵抗的聲浪卻如此渺小。我想要找出原因,有些地區幾乎快要無法容忍現況了,但只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就如「垂直權力」下的莫斯科殖民地,所以即使在最遙遠的地區和受苦的城市中,許多人還是覺得除了普丁之外別無選擇。政權的合法性已經瓦解了,但是在人民心中,卻無人能取代它。
最後,本書觀察了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夢魘,探討這個殘破不堪的體系是否能抵抗中國的興起。
為了寫這本書,我在過去五年內旅行超過三萬公里。我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橫跨俄羅斯兩次,在一些西方記者不曾去過的地方訪問了數百人。在雅庫茨克(Yakutsk)和馬加丹(Magadan)之間的結冰道路上攔便車,搭上狂野的金礦工人的卡車;跟著東正教舊信徒遠下西伯利亞的河流,尋找沒有電的村落;和薩滿巫師和圖瓦共和國的女巫聊天。我甚至在喬治亞戰爭末期搭著俄軍卡車越過停火線,進入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我試著盡量多花點時間在一些不太光鮮亮麗的地方和平民百姓相處,像是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油膩膩的酒吧,下塔吉爾(Nizhny Tagil)的路邊攤,還有伯力(Khabarovsk)的小商場。他們的觀點和恐懼影響了我的研究,而這遠勝過任何其他資料。從犯人、徵召軍人到核心幹部,我試著訪問來自各種生活領域的人們,了解他們對於國家的看法。當我談到俄羅斯或一些區域時,我把這些數千次的訪談內容融合為一,視為一體。
我曾經搭著史達林時代鏗鏗作響的地鐵,在莫斯科穿梭不下數百回,趕去跟反對派領袖、分析家、政治家和官員會面。我發現莫斯科有點像是結合了一九三○年代的柏林和芝加哥,又有點像一九六○年代的巴黎──我的世代會將這裡定義成一個對抗長者的地方,歐洲沒有其他地方像這裡一樣,充滿了熱情浪漫的抗爭情懷,就像一九六○年代的嬰兒潮。他們未來無疑會大權在握。我不記得冷戰或蘇聯,我來自新的世代,這是一個有反普丁示威者上街的世代。我希望我的新觀點能反映出他們的立場──這不是後蘇聯,而是沒有蘇聯。
我在這個國家,有機會和部長、州長和官員談話,甚至包括聯邦安全局的人,這些人拘留我,沒收了我的初稿,卻意外成為本書最早的讀者。聯邦安全局的官員拿起一篇草稿,質問我是否知道俄羅斯實際上有多麼接近瓦解,多麼地波動不安(「俄羅斯可能再度瓦解!我們如果不阻止的話,會再度陷入浴血的內戰……」)本書講的就是這種啟示錄般的恐懼,就是這種恐懼打造了俄羅斯,就是這種恐懼讓普丁大權在握,而他也利用它來維持權勢,但如今這種恐懼又變得對普丁不利。
只有當一件事情開始瓦解時,我們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運作。「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到底出了什麼錯?」如果我們想找到答案,就必須知道為何俄羅斯人會愛上普丁,他現在為何會變成國家之惡的縮影?而他的名字就像是國家的同義詞。
為何是普丁?是什麼樣的俄羅斯造就了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像他這樣的人可以被交付大權?那個來自聖彼得堡沼澤區的陰沉中校,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後記:亡魂
「權力過度集中是件危險的事。」──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Dmitry Medvedev)
普丁的地方如果有鬼魂出沒,那不會是布里茲涅夫的年邁幽靈,而會是尼古拉斯二世的痛苦靈魂。這位最天真的沙皇在死後是否仍躊躇在他的慘敗之中,是否還活在令人尖叫、脫離歷史軌道的俄羅斯火車失事中。他是否會在普丁入睡時對他竊竊私語,當這位最不可能的繼承者流著汗時,當革命一百週年的日子接近時,他們都面臨了一種類似的進退兩難──他是否必須不惜代價地從自己的災難中學到教訓?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安全地假設果真如此,而這位沙皇的精神仍然像他還在冬宮時那樣令人信服,他就會躡手躡腳地更靠近普丁,彎下腰,懇求普丁跟他做完全一樣的事:要撐住,絕對不要放棄任何東西,絕對不要退位來支持詭辯的自由派,這些人冒險把繼承權交給歇斯底里的人。絕對要有必要的統治,要獨自統治,要不惜代價地這麼做,還要宣稱這都是為了俄羅斯需要的穩定。
這位「國家領袖」愈來愈少待在莫斯科。他盡量撤退到自己在莫斯科外圍樹林中的城堡工作。他不再讓自己通往克里姆林宮的車隊凍結交通,除非是為了非常重要的外交事務。這個政府似乎很怕莫斯科,甚至有計畫地把政府搬離這個城市。理論上,他們正在進行,把整個官僚和克里姆林宮員工搬到一個新的「行政區」,就蓋在靠近伏努柯沃國際機場的一個單調建案旁。他們說是因為交通阻塞,才會想出這個計畫。莫斯科人則說,是因為抗議使然。
普丁的行徑像是他無法了解為何在二○○八年,他擁有如電影明星般的人氣,在首都成為自太空人加加林以來最偉大的俄羅斯英雄,但是如今在這個最高度發展的城市,這些在他統治下發達的人在講到他時,就像他們曾經講到的布里茲涅夫,把他視為盜取國家的小偷。普丁講話的方式,彷彿俄羅斯人還是很愛戴他,但是走路時卻偏執地拖著腳步,帶著一種不安的侵略。寵臣說,普丁覺得很受傷,覺得不被感激。他取消了外交行程,不再和「人民」打混,改而偏好跟野生動物廝混。就像他曾經說過:「我是一個迷信的人。」
俄羅斯不愛他了,普丁建立的模範也開始瓦解。這本書解釋了在葉爾欽之後,俄羅斯如何建立了一個高度精緻發展,同時又大幅落後的政權。中央計畫式的經濟結合了所有聰明的權力技術,讓這個國家有一個正式的民主機制,但卻從內將它掏空,讓它不具任何意義。陰謀和貪汙讓杜馬(俄羅斯眾議院)變成一場玩偶秀,讓選舉淪為與小丑競爭的公民投票競賽。俄羅斯已經變成了電視治國,給平民百姓看審查過的電視內容,卻允許知識分子取得自由的報紙和部落格。俄羅斯看著它的領袖利用影像對現代人的誘惑,把自己變成一個電視民粹主義的超級巨星,也見識了他介乎於偉大名人和優秀政治家之間的混亂。
俄羅斯透過這種方式,以最少的代價打造了一個霸權,這讓獨裁者們傾羨不已。他們關的記者比土耳其少,抗議比中國少,反對派的威脅不如白俄羅斯般嚴重。普丁看起來既獨裁又合法。這位歐洲最成功的後現代政治家已經顛覆了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福山認為會「終結歷史」的每一種機制。
但是在這個電視幻覺的背後,這個政權正在打造一個失能又落伍的權力結構。它發起了巨大的資產轉移,一開始是對別列佐夫斯基的掠奪,最後以對侯德爾科夫斯基的掠奪畫下句點,然後再創造普丁的寡頭來鞏固政權。克里姆林宮試圖建立一些落伍又無效率的機制,即使他們還很年輕時,就開始這麼做了──這是一種恢復蘇聯指揮系統的垂直權力,儘管有統一俄羅斯黨,但這其實只是一黨治國。他們承諾這些會帶來一個「法律的獨裁」。
這些偉大的計畫不經意地在普丁的模式中,植入了腐蝕的種子。他們是糟糕的管理員,拙劣地修補著政府建築。垂直權力最後變成了垂直貪汙,統一俄羅斯黨變成了一種贊助的網絡而非政黨,「法律的獨裁」變成了一群掠奪成性的官員的專制。他們讓俄羅斯變成一個分裂且封建的國家,所有貪汙的警察、督察和州長,都登記加入了普丁的政黨。
俄羅斯對此另有看法。當經濟蓬勃發展時,他們愛上了它的領袖,這是俄羅斯經濟史上最大一波的生活水準提升。新的中產階級活躍興起。人們相信可以克服政府的無能。歷經了數十年的貧窮、解體及失去地位之後,贏家們奔向消費主義,輸家們則鬆了口氣,因為這場自由墜落終於結束了。俄羅斯忽略了政治。
這場經濟榮景讓普丁的電視民粹主義,足以在菁英之間鞏固了一種普丁的共識,還在社會中奠定了普丁的多數。這是如此成功,到二○○八年時,當他改為擔任總理時,他成為了他那個世代最偉大的政治家,這不只是在俄羅斯,在國際同儕中亦然。布希、布萊爾和貝魯斯柯尼都以失敗結束;在中國、印度和巴西,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曾經累積了這麼多的權力。
就在此時,普丁主義開始從根腐壞。普丁先選擇梅德韋杰夫當總統來規避憲法的總統任期限制,接著允許他大張旗鼓地支持一個「現代化的方針」。這個政權打造了一個改革的故事、架構和選民,最後痛苦地令人失望。梅德韋杰夫偉大的說法,還有經濟危機的重創,暴露了俄羅斯的治理危機。垂直權力、統一俄羅斯黨和法律獨裁顯然都失敗了。表面底下的價值觀正在改變,俄羅斯不再想要中央集權化,不再想要聽到他們十年前渴望的「指揮聲音」。
普丁回來了,但是他回到另一個俄羅斯。他的重返最後在普丁共識和普丁多數的瓦解下畫下句點,而這瓦解是在梅德韋杰夫之下開始的。當時剛好是經濟榮景帶來的安靜、巨大的改變,破壞了電視政治和他的電視民粹主義。普丁重返總統職位,蹂躪破壞了這個更富裕、更全球化、上網的俄羅斯。俄羅斯人以為普丁建立的這個拙劣的機制,將會永遠蓋在他們的未來之上。就是在此時,普丁主義的贏家開始覺得自己像個輸家。
就身為一個政治家而言,普丁贏了,但是他老舊的模式失敗了,他的老套政治失敗了。這一切都暴露在二○一一年至二○一二年冬天的抗議運動中,譴責這個中央計畫式民主的選舉舞弊。那場運動並未讓這個政權畫下句點。那只是暴露了這個政權過去的權力所在──那是奠基於控制巨大資產、電視媒體和維安機關,而不是正當性和菁英的喝采。
俄羅斯對這場運動感到震撼且恐懼,汙辱統一俄羅斯黨是「騙子和小偷的政黨」。這是第一次有人在政治上傷害了普丁。這代表人們在取得共識的情況下,揭開了普丁主義的末日。克里姆林宮試圖胡亂拼湊出一種新的模式,但是這非常危險。普丁的共識已經被文化戰爭取代,普丁的多數則變成了階級戰爭。普丁失去了社會最進步族群的支持,被迫在最落後的人們身上尋求支持。這種新的模式顛覆了老舊的普丁預算。他終結了一種限制花費的經濟,那不會過度依賴高油價換來預算盈餘和低債務。當時俄羅斯油氣業嚴重的生產和投資問題不斷加劇。普丁展開了一場巨大花費的狂歡揮霍。他的會計帳目受脅於未改革的退休金制度,這可能會讓債務一飛沖天,預算和貿易盈餘也會因此消失,而油價如果從目前的高峰點跌落時,他就必須大幅縮減支出。他為了確保這個政權的生存,已經祭出了動盪無常來取代經濟穩定。
普丁知道他如果想要繼續掌權,就必須分裂這個國家,不能讓莫斯科的反對派與其他地方的不滿連成一氣。他在俄羅斯內地的民望只是虛構。那裡有一個極度痛苦的國家,他們對貪汙的官員憤怒不已,他們怨恨垂直權力,也對缺乏一種「法律的獨裁」感到驚恐。他們渴望一個現代國家,結果卻只看到事情反其道而行。這場反普丁運動至今仍無法克服區域、世代和階級之間的連結。這導致了國家分裂,也無法切斷在國營企業中暗藏的貪汙和依賴連結。這些企業將人民與普丁綁在一起,這解釋了為何當時有廣大的不滿情緒,但反彈卻是微不足道。這種現狀非常危險不安,如果普丁的預算失控,減少了對地區工人階級及窮人的救濟,這就可能促成動盪。他們只能容忍制度的現況。這是因為在數千個城鎮,像是西部的庫雪夫斯卡亞和東部的基洛夫斯基,普丁拙劣修補的國家建設已經將官員變成獵捕人民的「穿著制服的狼人」。這只是讓人民痛恨這個國家,讓每件事情都變得脆弱不堪。
在過去幾世紀以來,這個國家塑造了俄羅斯社會的樣貌,首先將它編制成農奴制度,然後再拿它來實驗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重建時期冒出的公民社會,最後被埋在蘇聯的廢墟裡,在一九九○年代的經濟蕭條中破碎瓦解。普丁很容易就鞏固了他的權力,就像原子分裂一樣,他沒有靠著強勢的非政府組織、報紙或成為精神領袖就做到了這一點。當俄羅斯在世紀轉替之際,根本沒有這些東西。但是普丁沒有想出任何計畫或意識形態來塑造社會──他只有「我們的」、統一俄羅斯黨或主權民主黨。現在社會走上自己的路,受到大趨勢的驅策,克里姆林宮只能試著引導方向。抗議運動開啟了新中產階級的政治化。人們想要參與。放眼全俄羅斯,在每一個城鎮或延伸的領土上,活動分子、部落客和公民倡議者開始具體形成一個公民社會。這種演變會如何決定所有的一切?這會變成迷戀民兵治理,毆打弱者,就像在烏拉地區的「無毒城市」嗎?或是會像莫斯科附近希姆基的自由派和環保派?我們很快就會知道這些數以百計的小規模作為,到底是會分享普丁的侵略和偏執,還是抗拒?
俄羅斯是歷史上最大的失敗之一。在上一個世紀之初,俄羅斯如果能像過去帝國時代的成功一樣,其實曾經有機會扮演如美國的角色。但是到了上世紀中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帝國無法變成現在的中國,也許她是該更早開始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實施更有效的管理。在世紀轉替之際,俄羅斯的處境類似戰後的法國。法國失去了殖民地,備受羞辱,被推向無政府政治,但是多虧了戴高樂和他的世代,這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強大、獨立,甚至是富裕的後帝國玩家。這也可以是俄羅斯的想望。
普丁的重返把這種想望扔進疑惑之中。他不是在拯救俄羅斯,而是阻礙她,讓她困在荒廢的機制裡。他就像一個嫉妒又虐待的愛人,他不斷地緊緊握住俄羅斯,告訴她如果沒有他,她就活不下去了。中央計畫式民主的老梁柱正在崩垮。這不是普丁認為他如此努力奮鬥該換來的穩定。而這也意味著,他如果想要繼續掌權,就必須進行改革或是打壓。這個國家唯有透過適當的機制,才能達到下一個階段的發展;它必須恢復普丁為了鞏固自身權力而破壞的一切,同時捨棄他所建立的一切。否則這個國家最好的狀況是政治停滯,它將會在國家的層級中繼續降格,甚至可能變成後奧圖曼時期的土耳其一樣無足輕重。
俄羅斯不是面臨政府瓦解的危機。它的確有問題,但他們不是蘇聯政府。這個政權可能不受歡迎,財政不穩,但並不一定會被宣判死刑。普丁仍然能夠控制所有重要的資產。寡頭們雖然有抱怨不滿,但仍然希望他當他們的仲裁者。俄羅斯還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國家,不想革命,也很害怕無政府狀態。但是整個氛圍、社論,還有人民的想法都很激動不安。
普丁主義具有某種啟示。他能上台,是因為他擁有控制俄羅斯全面解體惡夢的權力,他也因此能繼續執政。只有當某人能從他手中偷走這種權力時,他才可能被趕下台。西方國家不能決定俄羅斯的命運,但是必須思考如何應對普丁的命運。這充滿了極度不確定的因素。如果油價對他們有利的話,普丁和他的黨羽可能執政數十年。如果他們的確如此,布魯塞爾和華盛頓就必須自問,該如何與一個更壓迫又刻板的俄羅斯相處,其中還有正在興起的反對勢力。普丁曾經把他的反對者關入大牢。
西方國家必須有應變方案。此刻沒有馬上爆發的真實危機。但是如果群眾的躁動和人民的抗命在未來幾年的某些時刻失控了,這個「騙子與小偷的政黨」就必須犧牲他們的「沙皇」。現在幾乎有無以數計的總帳都取決於普丁的繼續掌權。但是金錢的最佳利益很容易翻轉。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領導人聚在比亞沃維耶扎(Belovezhskaya)森林,準備把戈巴契夫踢出大局,不過還是保留了他們的政治機器。這並非不可思議的想法,有一天俄羅斯石油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和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的領導們也會做同樣的事。這就是危險所在──普丁可能會覺得,他只有在克里姆林宮才是安全的。我們不知道普丁的這一面。我們不知道當普丁被逼到牆角時會怎麼做。發生在侯德爾科夫斯基身上的事,還有喬治亞的前例,讓我們很沒有信心。
西方國家開始設想這個可能性。他們應該自問是否會提供他流亡待遇,以避免流血暴力。我們不知道事情的結果。但我們知道只有百分之六的俄羅斯人說,他們能夠想像這個國家在未來五年的模樣。他們能確定的只有當下,人們無法在政治上擊敗普丁,只能在經濟上擊垮他。然而,納瓦尼的竄起顯示了莫斯科渴望一位新領袖。但我們也很清楚,最後是阿諛諂媚者推翻了柴契爾夫人和赫魯雪夫。
在克里姆林宮裡,人們有尼古拉斯二世的惡夢。他熬過了一九○五年革命的內部威脅,但看著他的制度在在戰爭的壓力下瓦解。普丁也處於類似的處境──任何外來的打擊,只要目前市場的腳步不再一致了,都可能把他推下脆弱的王位。雖然把政權變化視為不可避免的事並不是正確的想法。在西方國家,我們傾向認為獨裁體制,「會像氣候學的比喻一樣凋零」,只要生出一個中產階級或是一個網路,或是諸如此類的年代,克里姆林宮就會融解。但是在俄羅斯,人們並不這麼想。他們會想到板塊結構論。這個政權如此脆弱,底部遍是裂痕。這會被一場地震毀了,但沒有人知道地震什麼時候發生,會有多強烈,甚至不確定是否會有地震。
知識階層之間也有噩夢。聽聽他們的辯論,俄羅斯主要的雙開報《紀錄報》論壇編輯、評論家楚多盧伯夫感嘆:「空氣中充滿了一種感覺,俄羅斯好像受到某種詛咒……被詛咒陷入永無止盡的革命、停滯和瓦解的循環中,永遠都在重複。」
到處都有偏執,普丁的辦公室也有一種偏執,這個陰影圍繞著所有一切,讓它無法被視而不見,這就是葉爾欽的鬼魂。普丁的整個政治事業都在努力不要變成葉爾欽。為了不當葉爾欽,他必須先變成別列佐夫斯基,然後再變成侯德爾科夫斯基。為了不當葉爾欽,他必須建立垂直權力。為了不當葉爾欽,他運動,他打冰上曲棍球,甚至為了鏡頭,願意與鸛一起飛行。為了不當葉爾欽,他控制電視。但是他犯了一個錯。他在鞏固權力的過程中轉移大量的資產,這代表他無法下台。他已經變成了葉爾欽。普丁不能離開權力,因為他害怕被逮捕。歷史逃不開一再地重複。他最終會需要一位保護者,也許在二○一八年或二○二四年,因為任何的權力轉移都代表了資產轉移。他重返克里姆林宮,將梅德韋杰夫降職為總理,就暗示了他不相信在俄羅斯,會有任何人會為他這麼做。
俄羅斯還沒有出現不穩定,但是它的未來已經變得不確定。某種中世紀的東西籠罩著莫斯科,即使你試著用Wi-Fi或餐廳隱藏它,餐廳會供應進口的義大利食物,由進口的義大利廚師替你烹飪。我曾在這樣的一個地方跟評論家基里爾.羅格夫(Kirill Rogov)聊天,他是一位自由派和研究學者。我們一開始談到民調資料,但是當我們點了魷魚義大利脆皮麵包,配著酒喝感覺非常糟糕時,這些數字開始變成了對過去的恐懼。這裡的氣氛很陰沉,隔壁桌有些喝醉的石油商粗聲粗氣地點了更多的酒:
這種事情在這裡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了。這個國家先是狂喜地相信,然後突然之間,就會發現克里姆林宮裡的沙皇不是真正的沙皇,他是個冒牌貨,他是一個假沙皇……真的沙皇在別的地方。接著人們就會把他趕出城堡。這就是普丁害怕的事。此時每個人都針對他,把他視為江湖騙子,而他只是孤軍一人。這就是讓他驚恐的事。而你知道這些統計有些準則嗎?在民調中,若以十分為滿分,那麼對於某事的信任度在一瞬間從八分掉到兩分,永遠比從八分掉到七分、掉到六分、掉到五分、再掉到四分來得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