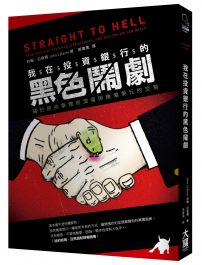母親來訪
成為分析師即將屆滿一年,我覺得自己非常棒。績效評估的結果公布後,我的成績在我們班上名列前茅。在我的職涯中,此時此刻,獲得五萬美元還是十萬美元的紅利,對我真的並不重要。有人對我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班上沒有其他人的成績或薪水,比我還要好。我的薪水確實是挺不錯,讓我感覺並不需要操心我的學生貸款。
當我告訴我的導師,我計畫將紅利獎金多元化的投資在股票資產上,希望隔一年可以買一間公寓時,他阻止了我。「你現在何必要努力存錢呢?你今日雖辛苦的存下一美元,可是幾年內,你卻可以輕易的存下十美元,何必這麼辛苦呢?把錢花掉吧,要相信你自己。」
這句話實在非常的有道理,因此在次個月,我說服了許多分析師班上的朋友們,一起去法國聖特羅佩(Saint Tropez)度假,我們的唯一目的,就是在五天內把我們的獎金全部花完。這項任務遠比我們預期中的還要簡單多了。
在未來幾個月裡,我又回到了月光族的生活。我有一間面著泰唔士河的公寓,但我的花費應該不至於如此難以控制。理論上,我不應該有時間在這麼快的時間裡把錢花光;因為我每周至少五天在公司工作至晚上。
由於晚下班(晚上八點後),我們也可以向公司申請誤餐費(二十英鎊)與搭車回家的交通費,因此即使我們較早完成工作,多數的分析師通常會先在外頭喝一杯,或者是偶爾上一下健身房,再回到辦公室點個餐,叫車回家。我最愛的食物是諾布姊姊在「金絲雀碼頭」經營的餐廳的食物,我在回家路上都會外帶回家吃。石蝦沙拉、鰤魚生魚片淋上墨西哥辣椒與柑橘酢醬、以及黑鱈味增湯是最讓我上癮的食物。我的花費通常接近四十英鎊,因此我只要在收據上寫上另外一位分析師的名字,把這一餐作為兩個人的花費即可。我並不對此感到愧疚,這是比較年長的分析師教我們的。況且我的作法並沒有很離譜;併購團隊的分析師們,他們的行徑比較誇張。
金字塔的底部
大約在二○○二年,我們每個人都配有一台黑莓機,可隨時隨地檢查、收發電子郵件,這無疑是將年輕的銀行從業人員綁在自己的工作上的工具。不過,對我們交易大樓的員工來說,事實並非如此;我通常得坐在配有交易鍵盤的彭博系統(Bloomberg)終端機螢幕前,以及在聽力所及的範圍裡,與大家一起在承銷單位裡工作才行。至於併購團隊的分析師們,完全不把這個放在眼裡,特別是在直屬主管外出時。許多人白天就溜到電影院,若收到緊急電話或是重要的電子郵件,這與身處於星巴克或正在抽根菸的情況沒有兩樣。隔一天,他們又會回到戲院,把剩下未看完的電影看完。
投資銀行的分析師就像是犯人一樣;小小的反抗動作,也可以為我們帶來極大的愉悅感,有助我們容忍作為一名銀行分析師所帶來的壓力。
我們多數的閒暇時間與花費, 都是耗費在Home House、Tramp 以及Annabel’s 等地方開派對。若我們對倫敦已經感到厭煩,就會移師到巴黎或斯德哥爾摩。由於我們彼此相處的時間長,融入於這個文化變成一件相當容易的事;而這段時間裡,我在倫敦的唯一朋友就是銀行分析師與同事們。
我們的文化是他人所無法理解的:包括生活型態、長時間的飛行與航班取消、豪飲、以及無聊至極的幽默感。我不認為其他人有過這樣的經驗:曾在地鐵車廂裡的昏睡中醒來,澡也沒洗、在眾人的歡呼讚美聲中穿著前晚的燕尾服直接進辦公室。這些荒誕的行為,其他人怎能夠理解呢?他們肯定也沒有這可觀的可支配的收入──儘管依照我的消費速度,我覺得這些可支配收入偶爾仍是有限的。
擔任分析師第二年快結束時,我在班上的成績表現依然是名列前茅。聖特羅佩的度假生活變得更是頹廢委靡,我們一整周都住在拜勒斯酒店(Hotel Byblos)的獨棟雙層套房,俯瞰著泳池。白天我們都在Nikki Beach 與Le Club55 等餐廳消磨,晚上接著是在貴賓室與Les Caves du Ray 等夜店度過。我們不可能玩得不盡興,但儘管如此,在南法度假一周只是再度提醒我們,這世上存在著數不完的財富,這世間誰才是真正重要的人;而投銀工作者,仍只是接近這金字塔的底部罷了。
當我在聖特羅佩度假曬黑的皮膚消退不久後,我又回到入不敷出的生活。在銀行上班扭曲了我對金錢、事情的優先順序、以及我應當或覺得應該享有的權利等價值觀。即使我有薪水收入,我仍覺得自己很貧窮。這種對現實的分離感,以及對社交圈愈來愈挑剔,再加上夢寐以求的奢糜文化強化之下,已讓我的生活型態與一般中產階級一樣,變得不太穩定,只不過錢的數字比較大而已。
無妨。當我擔任分析師邁向第三年以及最後一年結束時,我預料自己的成績與紅利獎金,將再度成為班上之冠,因此我帶著我的新女友,來到安提瓜(瓜地馬拉南部)的瓊比灣(Jumby Bay)短暫度假。若我們在夏天前分手,在我領到紅利獎金後,依然可以到聖特羅佩過年假。
我們倆白天都在船上航行、潛水,並輪流在沙灘酒吧、泳池酒吧與SPA 之間度過;晚上的話,則因為懶得穿衣服而叫了客房服務,度過了浪漫夜晚,或者是喝得醉醺醺的去附近賭場賭一把。只是這個賭場有個危險的規定,讓我們可以將賭場的籌碼都記在飯店的帳上。
在海邊大吃大喝與度過愉快的一周假期後,超過兩萬五千美元的飯店帳單,包括賭場一萬兩千美元的賭金,像怪獸般的痛擊我。我訂房時所使用的信用卡已被拒絕支付。我試了另外一張卡,結果也一樣。接著我很糗的打電話查詢我所有信用卡額度,即使我把帳單拆開,仍湊不到兩萬美元。
我絕對不能請我的女友協助。並不是我覺得丟臉──畢竟,她也花了四小時在賭場裡玩輪盤──而是我知道她的信用狀況,比她的智商還要低。再者,她現正在禮品店裡,正同步增加購買品項。
我破產了
事情很簡單,我先用公司卡支付,並且在帳單到期之前,打電話過去支付費用。我常見有人使用公司卡來支付小額項目或晚餐費用,卻可惡的不還錢;但我從未見過有人拿公司卡來支付所有假期的支出。我們生活在安隆(Enron)與世界通訊(WorldCom)爆發企業作假帳的事件後,因此不管我的績效評估與班上成績多好,工作保障仍是我向來重視的重點。正如日本人所說:「槌子總打突出的釘子」,因此我真的不想做出任何有辱名聲的事,但現在,我沒有其他選擇。
「先生,很抱歉,我們不收大來卡。」我想對方對於我還擁有大來卡,覺得很好笑。在花旗掌門人威爾(Sandy Weill)決定購買大來卡的幾年前,所有員工被迫得用美國運通卡交易。
此時我想到電影《華爾街》裡一句很貼切的台詞:「我破產了。」我只剩下一個選項,只能放下尊嚴打電話給我的父母,但我並未告訴他們這個奢侈的度假計畫,以及我可能已面臨寅吃卯糧的情況。
他們的態度親切的令人覺得神奇,並立刻提供信用卡資料,讓我再次覺得自己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仍住在寄宿學校裡並試圖從巴塔哥尼亞(Patagonia,成衣商)型錄上訂購東西。他們替我紓困,但我知道自己並不想聽到故事終了時的訓話。幸虧我分析師第三年的紅利獎金,在幾個星期後就會發放,因此等到他們準備開始訓人時,我手上又有錢了。
次星期,我試著向我母親再次確認,所有事情都很順利,我過得很好。她知道我賺多少錢,也知道我沒什麼時間花錢。她也曾耳聞身為年輕的銀行從業人員,要面臨許多壓力與緊張。她已見識到我的工作已提升我的身分,不過當她每周通電話問我忙什麼時,我總愛說:「只是工作及『閒晃遊蕩』而已。」上回她來倫敦看我時,她卻問我有沒有在吸食毒品。
「沒有,媽。我當然沒有吸毒。」
我能想到緩解她的擔憂的唯一方式,便是邀請她來倫敦,尤其是我的新公寓很不錯,她可以跟我住在一起。她毫不猶豫的接受我的邀請。兩個小時後,我收到她班機的確認信;她下周四就會到,恰好就在我入厝派對結束的隔天。感謝老天,因為我並不想讓她見到我的朋友,或者破壞氣氛。
我們正站在第十二號月台旁
對一個二十四歲的孩子來說,我的新公寓算是相當不錯的地方──兩個臥室、分層式的內部,與國王街(King´s Road)距離一個街口遠,且與斯隆廣場(Sloane Square)只有兩條街的距離。
在我舉行入厝派對的前一天,我的主管接到一通來自帝國菸草公司的電話,告知該公司即將發行歐元公司債,而我們銀行已符合其承銷條件,已列入該公司的初選名單中。我們被要求必須在隔天早上,面對面的進行最後一場競標簡報。這是一件聲望很高、且非贏不可的承銷案,預計銀行間的競爭將會非常激烈。
主管指派我將簡報內容彙整在一起:包括了幾頁關於歐洲債券市場的概要、我們銀行是全球最佳債券交易公司的紀錄回顧、以及我們給予帝國菸草公司的特別建議等;我在承銷部一一的完成了這項工作。當我完成時,我的主管已經下班回家;他是老派的銀行人,先前曾在施羅德集團工作,後來才到所羅門。下午五點,這已是他上酒吧、喝馬丁尼的時候。
通常來說,他相信我會把所有內容彙整好,不出任何差池的把簡報完成。可是,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簡報,因此我準備在當晚將檔案傳真到他家裡,若有任何修改,他可以再傳真回來給我。我不怕麻煩,因為自我保護總是件好事。
我通常會把簡報檔傳到樓上的印表機列印,幾小時後再傳真至我主管的家裡。不過,這次我老闆有不同的想法。
「我不想花時間等檔案印好。」這意味著他可能喝了太多杯雞尾酒了。「你把這些檔案收好,並且在明早帶著它們一起來。簡報是你寫的,你應該也要一起參與這場會議。我們明天八點準時在派丁頓火車站搭特快車出發。」
媽的。我根本沒料到自己必須參與這場會議。今晚我要舉行派對,且我老媽從休士頓搭著紅眼班機,明天早上就會到這兒了。
當印表機把簡報檔案列印完畢後,我已晚了兩個小時出現在自己的派對上。我一走進房裡,約莫有二十位朋友與同事,擠在我的客廳裡面。整間屋子充滿著大麻煙的味道。顯然,我女友已經讓派對先開始,即使我這個主人仍不在家。
很好,這正是我回家所需要的。我一整天都為了這件緊急的救火工作忙得不可開交,明天一整個上午還有一個會議,接著還得招待老媽一整個禮拜──主要因為她擔心我已快要失控。
我伸出手抓了一杯酒。接著後面的幾個小時,我們都在喝酒、抽菸,痛快狂歡。
隔天早上,我三個鬧鐘準時鈴聲大作。現在是早上七點半,我必須在三十分鐘內出現在派丁頓火車站。距離大約五公里遠,這至少要花十五分鐘車程,即使是在交通還不太擁擠的時候。
我的公寓真是一團亂。但好在我波蘭籍的管家,在老媽抵達前就會把這裡整理乾淨。
五分鐘後,我洗好澡、穿上了西裝,衝出了門外。我女友仍在床上昏睡。我停下來把我的鑰匙放在信箱裡讓老媽使用,之後再衝向國王街,手中緊握著我的簡報。有另外一個西裝筆挺的傢伙站在我前面的轉角,他攔下這四周唯一的一輛計程車,因此我大聲叫「對不起,我有很緊急的事情」,並且給了他一張二十英鎊的鈔票。他讓我搭了這輛車。
七點五十五分,我收到我主管的簡訊:「我們正站在第十二號月台旁。」
八點鐘,我收到另一封簡訊:「我正在月台上車。約翰,我很擔心你。」
最後,我的車子停在派丁頓車站前面,我回覆我老闆:「我已經在車站,火車上見。」接著跳下車並且全速往大廳方向衝去。當我到了十二號月台,我看到火車開始慢慢移動,我想我可以趕上。若趕不上,我被炒魷魚的機率相當高。
此時此刻,一位穿著藍色外套的火車站務員瞧見我連滾帶爬的往移動的火車跑過去,他站在我前面說:「火車已經開了」,他看起來準備用身體來阻止我。
「我不能錯過這班車」,我往他的方向衝過去,頭往另一個方向閃過,接著跨步越過他,在車門快要關閉的瞬間,八點零二分的時候,跳上了火車的最後一個車廂。
八點零三分時,我老闆發了另一封簡訊:「我坐在第一號車廂。你最好在這輛車上,這是唯一一輛特快火車。」因為我在非常後面的車廂,因此整整花了十分鐘才走到前面;但這段時間對我老闆而言,卻有如一輩子那麼長。不過, 一切都不重要了;接下來,我們花了四十五分鐘瀏覽簡報內容並概略描述我們的報告,至於剩餘時間,則是一片靜默。
搭了一小段計程車後,我們抵達客戶的辦公室,耐心的在會議室裡等他們的出現。我對自己可以完成這項任務備感驕傲,以致於讓我完全忘了自己的宿醉有多難受。我現在仍覺得有點微醺。
我的手機開始震動起來。不知名的來電者,我選擇不接。
一分鐘後,我的電話又震動起來,我還是沒有接。
我老闆有點為難。「如果你需要回個電話,我們可能還有一兩分鐘的時間。」
電話震動了第三次,可能是辦公室裡不知道我外出開會的某位同事打來。因此我接了起來。
******
「你這混蛋到底怎麼了?」是我老爸。我猜我媽的飛機提早一小時抵達。
我不能在我的同事面前承認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我是。」我回答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我只希望我同事們別聽到電話另一端裡的咆哮。
我老爸並沒有停下來。「你媽飛了十個小時來看你,你卻讓她走進一間髒亂不堪的房子裡,這就是你表達感謝的方式嗎?」媽的,我猜應該是管家還沒有來。她被開除了
「好的,我了解。」我必須遮住聽筒,以免他怒氣沖沖的聲音在會議室裡傳開。
他依然不掛上電話。「什麼?你說什麼?」
「好的,我知道了。我正在一個會議上。」同時間裡,帝國菸草公司的財務主管及其團隊,正走進了會議室裡。「合理,感謝你讓我知道這件事。」隨後我掛上電話,馬上把電話關機,並在西褲上把出汗的雙手擦乾,及時的與客戶們握手。
(本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