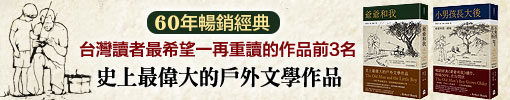政府是否應該強制推行年金保險?
「經濟自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我們給自己花多少錢,花在哪些方面;存多少錢,以何種形式存錢;給別人花多少錢,給誰花等等。當前,我們的收入的40%以上被政府花掉了。」米爾頓.傅利曼和海耶克一樣是新自由主義潮流的旗手。他反對政府強制民眾購買政府提供的年金保險,反對政府替民眾花錢,尤其反對政府介入再分配—無論是對個人在不同時期的分配還是人際間的分配。政府強制購買年金保險是政府介入個人在不同時期的收入分配。傅利曼認為,民眾既可以選擇不購買年金保險,也可以選擇到私人機構那裡購買年金保險。如果政府提供的年金保險比較有效率,那麼其售價會更低,民眾自然願意購買。否則,政府強制民眾購買年金保險,不僅形成壟斷,還導致政府雇用大量的專家和雇員,製造了龐大的官僚機構,這是家長主義的作風。特殊利益集團中最主要的構成就是實施計畫的大批官僚,他們正是靠這些計畫過活的。「大部分福利沒有用在窮人身上,其中有些被行政開支挪用,以優厚的薪酬維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即便政府強制民眾購買年金保險這樣的做法是出於善良的意願,但傅利曼指出:「我們這些相信自由的人必然會相信自己有犯錯誤的自由。假如有人喜歡活在當下,喜歡眼前享樂,故意選擇一個更為拮據的老年生活。那麼,我們有什麼權力來阻止他這樣做呢?我們是否有權強制他,讓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有人或許會說這些人會成為社會的負擔。但是傅利曼問:假如90%的人都不購買保險,到了老年成為社會的負擔,這一論點才有說服力。但是如果只有1%的人會成為負擔,為什麼為了避免這1%的人成為負擔,而限制99%的人的自由呢?因此,政府強制購買年金保險獲得很少的好處,卻花費了很大的代價,這樣的政府干預是得不償失的。
那麼,即便對養老問題不管不顧,政府是否也應該對貧富分化無動於衷呢?政府是否需要積極作為,以促進一個社會更為「平等」呢?每年,《富比士》雜誌都會公布一份全美最富有的400人名單。曾經連續十多年,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都位居榜首。2017年,《富比士》雜誌估計他的淨資產為860億美元。躋身財富排行榜的還有投資家華倫.巴菲特、沃爾瑪的所有者、臉書、谷歌和亞馬遜的創始人、石油大亨等。實際上,美國最富有的人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超過了底層90%的家庭所擁有的財富之和。籃球巨星麥可.喬丹也是美國富人中的一員。為了實現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我們是否應該對喬丹徵稅呢?桑德爾在其《公正》一書中展示了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者的論證:當然不應該。讓我們設想一下,喬丹退役以後,芝加哥市政廳或者美國國會為了安撫不滿的芝加哥公牛隊球迷,通過投票要求喬丹再打三分之一賽季的比賽。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大家會覺得這樣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因為它侵犯了喬丹的自由。可是,如果國會不能強迫喬丹重返籃球場,哪怕只是強迫喬丹去打三分之一賽季的籃球,那麼,它又有什麼權力強迫喬丹放棄他打三分之一賽季的收入呢?因此,徵稅就是奴役,就像強迫勞動。
傅利曼在與妻子合著的《自由選擇》一書的第五章中,談到了他對「公平」問題的看法,這代表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對「平等」這一問題的看法。傅利曼反對政府採用經濟政策提供社會福利,促進「平等」。
「道義的責任是個人而不是社會的事情,孩子照顧自己的父母是出於愛或責任感。現在,他們為他人的父母解囊是由於受到政府的強制和出於恐懼。」事實上,政府靠徵稅來提供養老與福利也沒有幫助到窮人,因為,「福利津貼的發放確實是偏於照顧工資較低的人。這種照顧被另外一種情況大大地抵消了。窮人家的子弟開始工作的時間較早,因而開始納稅的年齡都比較早;而富人家的子弟則晚得多。另一方面,就生命週期而言,低收入者的平均壽命比高收入者的平均壽命短。結果,窮人納稅的年頭比富人長,領取福利津貼的年頭比富人短」。
因此,傅利曼反對政府積極去建設一個結果公平的社會,他強調「機會平等」,指出機會平等的真正含義是:「前途向人才開放。」那些促進機會平等的政策措施是促進我們自由的,而那些強調結果平等的措施則是損害自由的。「只要有自由,今日之窮困潦倒者就有機會成為飛黃騰達者;在此過程中,幾乎上上下下每個人都能受益,過上更加健全、更加富裕的生活。」相反,政府促進結果公平的政策措施,卻會導致一些嚴重的後果。
為什麼美國的債務居高不下?
2013年6月,在希臘首都雅典,人們聚集在國家廣播電視公司總部大樓前,抗議政府以應對債務危機為由關閉該公司的決定。2014年3月,希臘當局宣布將部分地標建築納入私有化專案,以此來緩解巨大的債務壓力。希臘政府此舉招致希臘民眾的強烈不滿,市民在雅典市中心遊行示威,批評政府賣掉這些關鍵地標是希臘的國恥。
不僅希臘,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也遭遇了嚴重的債務危機。19世紀時,美國的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最低時不到10%,最高時也不到40%。根據全球經濟指標網站(www.tradingeconomics.com)公布的數據,美國聯邦淨債務(Gross Federal Debt)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時已達到美國GDP的100%;到了2017年,這一數字增至105.4%。
美國的債務問題並不是特例,其他已開發國家同樣遭遇了嚴重的國家債務膨脹。如表3-1 所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趨勢。除了英國的情況有所緩解,其他國家債務問題都在惡化,其中義大利與日本的狀況尤其嚴重。日本政府的債務,1966年時占GDP的比重僅為0.2%,到1994年上升至74.8%,2004年又猛增至153.4%。
如此嚴重的國家債務是如何產生的?公共選擇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回答,正如其著作的名字《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是政治家在民主制度下的理性選擇。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你是一位面臨巨額債務負擔的政治家,你應該做怎樣的選擇呢?傳統智慧是政治家需要「開源節流」。一種辦法是增加稅收來彌補財政赤字,償還債務,這是「開源」;另一種辦法就是減少開支,管好政府的錢袋,這是「節流」。政府花錢少了,政府的赤字就會相應減少,進而緩解政府債務上升的壓力。但是這兩種辦法對理性的政治家而言都是不可取的。
道理很簡單,我們先來看「開源」可能給政治家帶來的損害。如果政治家選擇增加稅收,那麼他會損害部分選民的利益。選民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不喜歡增稅。如果增加對窮人的稅收,而窮人又是選民的多數,下次選舉,這位向窮人徵稅的政治家就難以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政治家選擇對富人增稅,同樣面臨政治風險,因為競選活動需要資金,政治家往往需要向富人,也就是他的「金主」們籌集資金。如果增加對富人的稅收,那他從富人那裡籌款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1988年老布希在競選演說中信誓旦旦地宣稱:如果他入主白宮,就絕不加稅。他的名言是:聽好了,我絕不加稅!(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但在他當選美國總統以後,龐大的政府預算赤字迫使老布希不得不食言,同意增稅改革方案。老布希絕不加稅的諾言落空了。「我絕不加稅」成了被美國選民和老布希對手不斷重複的名言。在1992年的大選中,民主黨利用這一點來抨擊老布希,這是導致他謀求連任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再來看「節流」。為了遏制居高不下的政府債務,有一部分政治家選擇減少政府開支。問題是,當政府減少支出時,會有不少人受損。如果政治家削減對大學的補貼,大學生將要繳納更高的學費;如果政治家減少養老金,那麼老年人退休後的生活狀況會變得更為淒涼;如果政治家削減醫療支出,那麼病人將支付更高的診療費用。因此,作為選民,沒人願意看到自己的蛋糕被切割。2013年,巴西政府為控制政府債務,調整了公車票價,儘管只提高了不到0.6元人民幣,但卻引發了超過20 萬人上街遊行,抗議政府為了「節流」,損害民眾利益。這是巴西民主化以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
在民主制度下,增加稅收會有人受損,不利於政治家連選連任,這一方案被否定了;減少支出也會有人受損,不利於政治家的政治生存,這一方案也被否定了。相反,即便在政府高債務的情況下,增加支出也是受歡迎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和你的競爭對手一同競選,他許諾每個月給每位選民增發500元的補貼,你許諾給選民1000元。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你當選的概率更高。那麼,在高額債務的情況下,你從哪裡去找資源來兌現你的承諾呢?兌現承諾的一個可靠辦法就是繼續借債。用借來的新債來還舊債,用借來的債務來收買選民。民主制度有競選壓力,理性的政治家會注意滿足民眾的短期利益,樂意提供慷慨的津貼、良好的醫療等。所有民主政府的政治家都樂意借錢,因為借錢可以自己花,還錢則是下一任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他們自己不借錢,他們的競爭者當選以後也會選擇借錢。這樣一來,對理性的政治家而言,還不如自己借了錢,讓政府負債,反而讓競爭者不好接手。理性的政治家借來錢,通過各種途徑讓選民獲益,收買選票,增加當選的可能性。因此,即便在有財政盈餘的年份,政治家也未必想著去解決債務問題。在民主制度下,理性的政治家沒有政治動力去解決赤字問題、債務問題。這就是布坎南指出「赤字中的民主」的邏輯。民主國家競選的壓力會讓他們的財政赤字問題越來越嚴重,相應的問題就是公共債務積累得越來越多。
為何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受經濟危機困擾?
80年代初,拉美國家經歷了嚴重的債務危機;80年代末,美國經歷了儲貸危機(S&L Crisis),全美3000多家儲貸機構中,有上千家無法兌付儲戶存款;1987 年,以美國紐約股市暴跌為開端,美國的金融地震引發了全球股災。進入90年代,日本也經歷了股票市場的蕭條與經濟停滯;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出現問題,爆發貨幣危機;1994年,墨西哥比索匯率狂跌,股票價格大幅度下跌,墨西哥和土耳其爆發危機;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從泰國開始,波及印尼、韓國,1998 年,危機擴散到俄羅斯等國家。2000年,由於互聯網泡沫破裂,美國與歐洲股市大跌,遭遇危機;2001年,土耳其以及阿根廷又爆發危機,阿根廷危機期間,兩周之內五易總統。從2007年開始,次貸危機席捲美國,2008年,美國的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危機,這次危機波及了歐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也引發了全球企業破產浪潮。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指標急劇下降,全球經濟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衝擊。以上危機的原因和形式各不相同,但卻證明了馬克思的預言—危機將始終和資本主義相伴隨。
斯皮格爾認為馬克思從未提出一個獨立的、內容充實的經濟波動理論。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危機受到無窮多因素的影響,所以不可能在任何一個抽象的層面得到一個完整的解釋。馬克思關於危機的論述散見在《資本論》及《剩餘價值理論》中的多個章節。馬克思對危機的論述有重要價值,海爾布隆納指出,馬克思的預言被不斷驗證,尤其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學者都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內在的危機傾向。馬克思對危機的關注點有好幾個,包括生產部門的比例失調導致危機等,這裡無法一一展開。薩伊等人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一種產品,生產得越多,對要素需求就越大。買的過程就是賣的過程,供給與需求相聯繫、相適應。因此,資本主義不會出現普遍性的危機。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認為不會有經濟危機。「在人們為自己而生產的狀態下,確實沒有危機,但是也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古代人在他們的奴隸生產中知道有危機這一回事,雖然在古代人中,曾經有個別的生產者破產。」資本主義之所以會有危機,是因為人們不再為自己生產產品,「沒有一個資本家是為了消費自己的產品而進行生產的」。馬克思注意到,如果為他人生產產品,就可能存在買和賣的脫節:「危機的可能性在於賣和買的彼此分離。」因為出賣商品的人會遇到困難。「已經賣掉了商品而現在持有貨幣形式的商品的人並不是非要立刻重新買進、重新把貨幣轉化為個人勞動的特殊產品不可。」
如果持有貨幣的人並不著急買進產品,而是把貨幣儲存起來,延緩使用,這就為下一步支付帶來了壓力。「賣者—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價值—的困難僅僅來自於買者可以輕易地推遲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的時間。」一旦他推遲了消費的時間,就可能引發連鎖效應,「不僅是因為商品賣不出去,而且是因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內賣出去,在這裡危機所以發生,危機所以具有這樣的性質,不僅由於商品賣不出去,而且由於以這一定商品在這一定期限內賣出為基礎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實現」。一系列支付不能實現,債務鏈條被干擾,就會引發信用危機,進而出現經濟危機。因此,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包含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買和賣的分離以及支付連鎖關係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