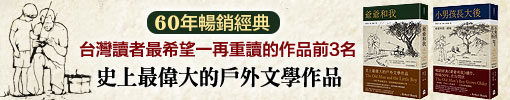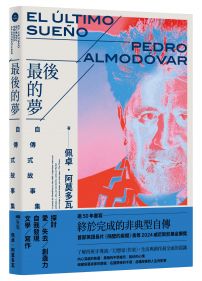作者序
曾經有人找我寫自傳,我一概婉拒;之後也有人建議我找人代筆,但我依然對於一本完全以我個人為主題的書,感到某種反感。我從沒寫過日記,每次嘗試往往不超過兩頁就放棄了,那麼,這本書豈不是我的第一個矛盾。這本書比較像片段式自傳,不夠完整,還帶點撲朔迷離。不過,我想已足以讓各位讀者對我作為導演、幻想家(作家),還有我的形式作風是如何讓這些人生角色錯綜交織,能有最全面的認識。但是這本熱騰騰出爐的書還看得到其他矛盾處,我從沒寫成日記,書中卻出現四篇與這個說法相反的內容:〈最後的夢〉,談到我母親的過世;〈再會了.火山〉,我到墨西哥迪坡斯特蘭(Tepoztlán)探訪查維拉(Chavela);〈追憶空虛的一天〉,以及〈一本蹩腳的小說〉。這四篇精準捕捉了我的人生片刻,整本書就像是故事集(我把每一篇都稱作故事,不分種類),呈現我所寫的、所拍過的,和所活過的之間緊密交纏的關係。
蘿拉.賈西亞(Lola García)把這些故事和其他許多故事,全都歸檔放在我的辦公室。蘿拉是我的助理,她除了幫我處理這件事,也處理其他多如牛毛的雜務。她從我多次搬家的混亂中,救出好幾個老舊藍色檔案夾,並整理出這些故事。她和浩門.波菲爾(Jaume Bonfill)決定讓故事重見天日。我從寫完之後不曾再看過一眼,蘿拉幫我歸檔,最後我還是忘了它們的存在。幾十年過去了,若不是她提議我再翻閱一下,我從未動念再讀這些故事。蘿拉精挑細選出幾篇,要看我讀了之後有什麼反應。我利用《荒漠斷背情》(Extraña forma de vida)前製和後製時的一些零碎時間,讀得津津有味。我沒再多加潤飾,因為我想要回憶當時的自己,重溫當初寫下的原汁原味,見證我從取得兩個高中文憑畢業之後,如何改變自己的人生和周遭的人事物。
我從孩提時就知道自己想當作家,經常寫些東西。我了解自己的文學志向,但我對於耕耘努力的結果沒有把握。本書其中兩篇談到我對文學和寫作的著迷:寫於1967年至1970年裡某幾天下午的〈米蓋爾的生與死〉和2023年才寫的〈一本蹩腳的小說〉。
我重新閱讀其中幾篇故事,回憶起是在哪裡以及如何寫下這些文字的。我彷彿看見自己在馬德里加萊霍鎮(Madrigalejos)老家院子的葡萄樹下,對著打字機寫下〈米蓋爾的生與死〉,一旁掛在繩子上的是一隻噁心的剝皮兔子,好像一支大蒼蠅拍。或者1970年代初我在西班牙電信公司的辦公室裡,忙完工作後開始偷偷摸摸地寫作。當然,還有在我住過的不同屋子裡,面對一扇窗戶寫作。
這些故事是我電影作品的衍生篇章,有時候直接反映了我寫作當時的生活片段,或者在多年之後搖身變成一部電影(《壞教慾》〔Lamala educación〕和《痛苦與榮耀》〔Dolor y gloria〕的某些片段),又或者將來可能拍成電影。
所有的故事都只有起頭(當時都沒寫完),許多篇的誕生是為了逃離生活的乏味。
1979年,我創作了一個集各種荒誕於一身的角色─佩蒂.狄芙莎(Patty Diphusa,〈性感偶像的告白〉);在新世紀開始時我寫下了〈最後的夢〉,記錄我成為孤兒的第一天。接下來的創作─包括〈苦澀的耶誕節〉在內,我還加入關於查維拉的橋段,她的歌聲曾以難忘的方式出現在我的幾部電影中─我的視線回到自己身上,看見自己變成筆下〈再會了,火山〉、〈追憶空虛的一天〉和〈一本蹩腳的小說〉的新角色。這個新的角色,雖然和佩蒂相反,卻又和她是一體的。進入新世紀後,我比以前陰沉、嚴肅和憂鬱,少了自信,沒安全感,多了點恐懼;而我能從這裡汲取靈感。從我執導的電影,特別是近六年來的作品,都能窺見這些痕跡。
一切盡在本書中;我也發現,早在1970年代初剛到馬德里時,我已經變成了後來的自己。〈不速之客〉在2004年拍成《壞教慾》,以及如果我當初有錢,說不定就會以〈失心美人胡安娜〉或〈鏡子儀式〉作為導演處女作,再繼續拍我後來完成的電影。而抵達馬德里之前,我還有一些在1967年至1970年之間寫的故事,〈贖罪〉和先前提過的〈米蓋爾的生與死〉。在這兩篇故事中我發現,一方面我當時剛從高中畢業,另一方面這三年和家人住在馬德里加萊霍鎮,我正沉溺於年少時期的憂愁,害怕自己永遠困在小鎮無法離開,需要儘快逃離那裡到馬德里。
我試著原封不動保留我寫下的故事,但我承認,我還是忍不住潤飾了〈米蓋爾的生與死〉,因為故事風格太過矯揉造作,但我尊重原先的風貌,只稍加修改。這是我在五十多年後重新回味,最感驚豔的一篇。我依然清楚記得,故事的主軸是倒述主角的一生。這是最重要的,而且請容我說這頗具原創性。幾十年之後,我曾想過《班傑明的奇幻旅程》其實是剽竊我的點子。這篇故事本身很普通,呼應我當時閱歷不多的人生旅程,但重要的是這個創意。如今重讀,我發現這故事主要是敘述回憶,和面對歲月腳步的無可奈何。我相信,這正是當初寫下這個故事時我腦海中所想到的,而我驚訝的是後來竟然遺忘了。時至今日,所有描述1970年代的故事依然常見宗教教育的題材。
我在1979年創造了佩蒂.狄芙莎這個角色,是我徹底的轉捩點,這一定得在1970年代末尾的混亂時期才寫得出來,不能提前也無法延後。我的腦海浮現當時的自己,坐在打字機前,以飛快的節奏做各種嘗試、生活和寫作。我成為孤兒的第一天,以〈最後的夢〉為一個世紀畫下句點,我認為這短短的幾頁是我創作至今的最佳內容,所以加入了這一篇。這不代表我是個好作家,除非我能寫下至少兩百頁同樣品質的內容。我能寫下〈最後的夢〉,一定得是母親百年之後。
除了《壞教慾》與〈不速之客〉的關係外,本書有許多題材,已
化為我的電影。其中一篇是出自我對考克多(Cocteau)的獨幕劇《人
聲》(La Voix Humaine)的著迷,而這出現在《慾望法則》(La ley del
deseo),也出現在初版的《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Mujeres al borde de un ataque de nervios),並再次現蹤在《破碎的擁抱》(Los abrazos rotos),最後在兩年前變成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演出的《人聲》(eHuman Voice)。我也在〈男女變變變〉談及在《我的母親》(Todo sobremi madre)出現的一個重要元素:折衷主義,混合的不只是性別,還有深深影響我的作品,除了考克多的獨角戲,還有改編自田納西.威廉斯作品的《慾望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我的製片公司就叫慾望無限電影公司〔El Deseo〕),和約翰.卡薩維蒂(John Cassavetes)的電影《首演之夜》(Opening Night)。凡是到我手中或經過我眼睛的東西,我都加以消化融合變成自己的,不過尚未達到〈男女變變變〉裡的雷歐的本領。
我在後現代主義爆炸時期當上導演,靈感來自四面八方;各種風格和時代共存,不存在任何對形式或性別的偏見,也不存在市場考量,唯一存在的是活在當下和做想做的事。對我這種想吞下世界的人來說,這是個理想的大補湯。
我的靈感,可以來自童年前期所在的拉曼卻(La Mancha)院子,或陰暗的搖滾波浪文化沙龍(Rock-Ola),如果有必要,我會在童年後期度過最悲慘歲月的地點停下腳步,也就是那間恍若監獄的慈幼天主教學校。那是充滿痛苦和光輝的幾年,可怕的學校拉丁文彌撒恍若原聲帶播放,而我擔任合唱團的獨唱(《痛苦與榮耀》)。
現在我可以說,形塑我的三個地點是:拉曼卻的院子,婦女在那裡織棒槌蕾絲、唱歌,以及聊整個村子的是非;1977年到1990年間馬德里放浪形骸的熱烈夜晚;還有1960年代初我在慈幼天主教學校所受的可怕宗教教育。所有精華都濃縮在這本書,再加上其他元素─慾望製片公司製作了我的電影,也製作了瘋狂、主顯節,還有不得不遵從的律法,彷彿我們是一首波麗露舞曲歌詞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