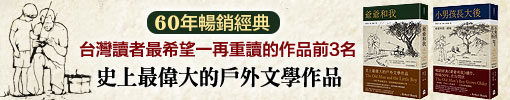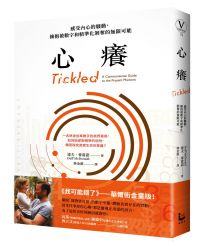序言(摘錄)
精準悖論
我要用一種可能跟你讀過的大多數書稍微不同的方式,來開始這本書。這確實不同於我所寫過的任何一本書,這是一本我一直想寫、但終究沒有寫成的書。這本書在談一個我自認極為符合我的專業與優勢的主題,而且我相信它將是我所創造過最好的東西——我職業生涯的巔峰之作。我的出版商樂見其成,還給了我一筆可觀的預付款,於是,我在二○二○年五月開始動筆。
結果,沒有一件事如我所規劃的那樣,那些最初的想法再也無法使我發癢。因此最終,我寫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在我說明此事發生的原因前,我想先讓你知道最初設定的那本書,因為它對於理解我最後為什麼改變十分重要。請別以為我在要求你讀一個未完成的東西,因為它確實完成了:此刻你正在讀它。而且,我至今仍然相信,你即將在書中讀到的每一句話都是完成品,差別在於,我比剛開始寫的時候更深刻地相信它們。因此,我最終寫出了一本和預期中不太一樣的書。那麼,我們開始吧。
這是本書該有的樣子,更確切地說,它也只能是這個樣子。在寫了這篇引言後,我明白我做錯了什麼。
《精準悖論:我們的執迷於測量,如何導致常識的衰退。》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以為能夠測量一切,而另一種人知道辦不到。前者從後者手上奪取了社會的決策工具,而且一直緊握著這項工具,並且獲得了權力——如果主事者認為測量的重要性高於它應有的程度,那麼,測量的重要性就會被高估。我們將太多集體決策的控制權交給那些自命為「專家」的人,他們在注定一無所獲的地方,也就是大量的數據資料中,找尋對人類極其重要的真相。
當你數算東西,你會得到什麼?一個數字,當然。這個數字裡包含了什麼?除了它本身,什麼也沒有。數字永遠是對的嗎?這個嘛……你請三個人去計算某個柴堆的木柴數量:
甲:「柴堆裡有二百根木柴。」
乙:「柴堆裡有一百九十八根木柴。」
丙:「我沒空數,所以我把前兩個推測平均起來,視為一九九根木柴。」
有沒有可能,其中一個數字是正確的?是的,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這三個數字都是正確的?當然不可能。
有沒有可能,沒有任何一個數字是正確的?絕對有可能,尤其考量到第三個人甚至嫌麻煩而設法透過了數學——將兩個數據加以平均——來得到一個解答,而非尋求直接的體驗(去數算木柴的數量)。
因此總結來說,某個數字可能包含了真相,也可能不包含真相,得視情況而定。不僅如此,我們都知道,從事計算的人在討論的方式及數字的重要性上發揮了極大的權力,即使他們並沒有掌握真相。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對的,可以理解的是,每個人都傾向於認為自己說的話是帶有真相分量的事實,即使這些事實是錯的。我們隨時都在這麼做,但有個問題:到了某個時刻,我們開始將「事實」與「真相」混為一談,久而久之,我們逐漸相信數字不再只是表明了事實,也表明了真相。此外,我們賦予數字高於文字的資格。
有些人處理真實的人和真實的事——我們稱為專業人士;也有些人處理我們所產生的數據,並試圖記錄下來——我們稱為專家。專業人士處理現實,而專家處理現實的模型。我知道還有其他類型的專家,但如果你翻開二○二一年的報紙,當他們提到專家時,其實是指分析師,而分析師負責數算東西。想想:在二○二一年,如果你願意花時間數算東西,就可以稱自己為「專家」。連三歲小孩都會算數,然而,要幫助三歲小孩了解他們到底在算什麼,則需要一個知道如何使用他們語言的人。
算數者想做的是:測量和評等一切的事物。
是這裡或歐洲,有更多的人命在旦夕?
所有這些死亡要花費多少成本?
史上最昂貴的病毒是哪一種?
民調對於那個數字有何看法?
我不只在談新冠疫情,我也在談一切的事物。我們之所以無法停止計數,原因是計數比理解更容易。但是,真相藏在事物的本質中,如果我們想知道某樣東西有多少個,那麼計數通常就足以應付了,前提是,我們能對在數些什麼東西達成一致的意見,然後對計數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共識。然而,問題不在於有多少個?而在於為什麼?你有多常更新你的數字並不重要,它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數字唯一包含的東西就是它們本身,此外別無他物。
儘管如此,我們繼續不斷地測量和數數,想藉此回答那些不能被量化的事物的問題。什麼是人的價值?專家要我們用數字彼此評估:我們的年度銷售績效、我們的智商,或我們的網紅等級……然而這些數字絲毫不能說明我們真正的身分,或者釐清使得我們成為「人」的是哪些事情,例如覺知程度或態度,或者換個方式來說——我們的心境。唯有透過覺察你的存在,才可能獲知真相或絕對的現實。但關於覺知,並沒有精準這回事,因為覺知不是一種思考,無法被任何心智過程所理解,它完全存在於智能領域之外。
量化的世界觀
我們牢牢地被困在對精準的執迷之中,而精準的源頭是數字和量化的世界觀。在多數情況下,精準是一座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對於某些事,我們可以講求精準,包括身高、年齡、每隻手的手指數量或房間裡的人數,但有些事我們無法做到精準的理解,例如直覺、心情、和諧度或人們做各種事情的理由。還有,一旦你測量了某件事物,如同理論物理學家海森堡告訴你的,你已經放棄了它的來龍去脈,當你確定了位置,你就失去了對速度的掌握;當資訊變得去情境化,你對它的理解就流失掉了。
這種情況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捷克經濟學家塞德拉切克(Tomas Sedlacek)認為:現今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色,或許是從強調「為什麼」變成了強調「如何」,他寫道,「這種變化可以說是從本質到方法的轉變。科學時代試圖將我們的周遭世界去神秘化,以機械、數學、決定論和理性的外衣來呈現,並摒除那些無法憑藉經驗來證實的自明之理,例如信仰和宗教。」從「為什麼」到「如何」的轉變,也是大多數人變老時會發生的事:兒童想知道為什麼,而成年人想知道如何。
說到試圖量化那些不可量化的事物,社會科學家特別應該被究責。一個世紀前,他們為了得到眾人的敬重,給自己穿上了科學方法的外衣,此後我們一直聽到團隊合作的百分比,以及樂觀估計平均數之類的胡說八道。我們為何不停下來處理這些荒謬的測量行為?因為我們太忙於透過計算來打通啟蒙之路。但是,數字並不是解開存在之謎的辦法。
就這個層面而言,數字同樣無法解開新冠病毒之謎。如果你光是數算新冠疫情所引發的事情,那麼你只是在描述表象,沒有深入理解重點。沒有人需要被告知這個病毒是什麼——它是殺手。再者,所有專家似乎都是在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這裡有多少人被感染、那裡有多少人死亡、病毒如何傳播等,但我們應該瞄準的答案是此事為什麼會發生,那是我們能做出有意義決定的唯一辦法;同時,不只是關於如何做出反應,更關於我們如何預防新冠疫情的再度發生。我們需要問為什麼,才能去理解,而非只是描述那些所遭遇的事。事實是,我們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而儘管我們擁有數量驚人的專家建議,卻可悲地無法了解它。
不過,本書不是在談新冠病毒,而指涉了更寬廣的事。這本書在談奇蹟。什麼是有史以來發生過最神奇的事?對每個人而言,最天大的奇蹟就是我們存在,沒有這個奇蹟,就什麼也沒有。因此,存在是個重點,但關於存在的這個狀態,你無法數算或量化它,它在不停地改變中,它是一種變遷。
關於活著,現在和將來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精準地說明,但我們卻數了又數。我們冒著失去什麼的風險?我們已然失去了什麼?答案幾乎就是我們的人性。人類發明了數字並迷戀這個創造物,人類想要測量一切,忙著計算事物的本質。讓我換個說法:我們沉醉在打造機器的成功中,開始試著打造靈魂科技,而這麼做就是冒著失去靈魂的風險。
我沒有興趣重申由來已久的品質與數量之爭,我感興趣的是現代生活核心中的悖論。例如大家可能都同意:快樂比有錢好。但我們對於測量的執迷導致了我們設法去計算品質,近來此類事物的典型諸如荒謬至極、可以被量化的「快樂科學」,以及製造滿足感的龐大產業。
我們試圖利用測量來回答的問題包括:
我是誰?
我為什麼在這裡?
什麼事使我快樂?
我們越是想利用測量來回答問題,越是忽略了真正的本質。當我們設法仰仗計算來達成結論,就會出現太多無法調和的變數。人性包含了太多的層面,這些層面與我們所珍視和無法控制的事物有關,多到不可能塞進一個公式裡。如果我們想得到一切問題的答案,我們需要從我們一貫依賴的測量中抽身,試著以不同方式來理解現實。
近年來,情況變得明朗,我們以為是真相的東西,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般不可動搖,那是因為真相位於我們的思考範疇之外。測量者或許能數算出我們有多少個人,但無法為唯一的真相(亦即存在狀態)標上一個數字。這個真相取決於我們自身,而答案不是一個數字。我們不能也不該用我們難以理解的心靈,去換取簡單計算人口數量的效率。前者是我們的一切,而後者只是一種方法,一種用來描述表象的貧乏方法。
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我們將太多的社會控制權放在極小範圍內的一群思考者——分析師——手上,這麼做已經剝奪了我們豐富的共同生活,因為這些分析師以為我們能靠測量獲得真相,但真相並非一個數字。
客觀和真相
再者,我們混淆了所謂的「客觀性」和「真相」。如同多數人的理解,客觀性只不過是個過程罷了,也就是我們測量、測量、再測量,忙著致力於無節制發展的一個過程,這麼做的同時,我們用智慧交換精確,用人性交換數學化。就如同我的朋友溫克(Chris Wink)——藍人樂團(Blue Man Group)的共同創辦人,以及拉斯維加斯溫克世界(Wink World)背後的策劃者——所描述
的,我們陷入了瘋狂的「統計淫」(“statsurbation”)。
想想「量化的自我」這個概念。在缺乏意義和目的性的自我提升文化中,測量給了你一個目標,告訴你可以靠測量獲得更好的生活,這種想法相當適合這個機械化、簡化和分析的世界。我們不停測量各種進展,銷售主任賣給我們指路明燈,幫助我們解釋自我,而他們也在我們數數的同時獲利。那些用來描述自我的數字,讓我們覺得好像掌握了控制權,其實不然。數據資料讓我們倍感壓力,我們在不該干預時進行干預,然後倚賴提供數字的人提出解決方案,以處理被數字創造出來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更靠近答案。我們用測量、比較、縱向研究和預測,混淆了我們自己。所以,我們需要停止計算每一件事,並開始注視它們。我們需要停止計算生活,並開始過生活。我們需要減少測量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而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事。如果我們能保持專注於此時此刻,那麼剩下的部分便不勞我們費心。佛陀說:「智者訓練其心,每次只關注此時此刻的一件事。」我同意他的說法。
關於上述內容,我希望讀者至少有一部分能點頭贊同。我們如何走到眼前這一步?我們之所以走到眼前的這一步,是因為數字改變了世界,人們在硬科學的幫助下學會了控制周遭的物質環境,看似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了。但我們對數字的依賴已然失控,我們誤信科學方法能獲致真相,導致我們將量化擴展到那些不屬於它們的領域。我們越是相信數字能描述超出數量範圍以外的事物,越是在欺騙自己可以掌握確定性,但情況並非如此。
「確定性」是一種假象,因為我們唯一能確定的事,就是無限。意思是,它是無窮無盡的,我們絕無法憑藉計算搆著它的輪廓,以及我們自身的存在。此刻你存在,接下來的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因此你是無限的,你就是宇宙。
我不是出身於某些反數學的詩意領域,我最早喜愛的智力活動與數量有關——編碼、化學、微積分。我從前研究金融,因為我被它的數學基礎所吸引,現在我迷上偉大的阿根廷詩人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他的小說建立在哲學、數學和邏輯的基礎上。不過近年來,我對數學的喜愛已經轉變成關切數學化的問題,我寫過兩本書,一本是《你所不知道的麥肯錫》(The Firm),寫的是關於麥肯錫公司的運作,另一本《金色護照》(The Golden Passport)寫的是哈佛商學院,這兩本書都對日漸支配我們社會的分析力發出了警告。資本主義過度吹捧分析力的結果,造成了文化批評家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所稱「優秀的羊群」(Excellent Sheep),這個社會現象是說,在錯誤的教育下,一群計算能力不輸任何人的菁英,卻像無頭蒼蠅那般汲汲營營,這理論在探討遇到重大問題時,我們如何進行批判性和創意思考,以及如何找到目的感。
菁英份子偏好看績效,因為績效比較容易測量,而且會出現可預測的結果,這代表我們不去找尋旅途中的滿足感,反而專注於目的地。還有,當我們給予目標過高的優先順序卻未達成,我們會因此沮喪,甚至可能降低目標。如果再度沒有達成目標,那更是陷入了深淵。可以說,我們最常見的失敗經驗,直接源自於那些我們用來測量自己的數字。換言之,你原本不知道自己出了問題,直到有人(或許是你自己)告訴你,說你沒有達標。
別誤會我的意思:測量狂熱對我們一直是有價值的,硬科學讓大自然在無數方面為人類屈服,還有,統計學家將人類從以猜測為基礎的生活中解救出來,推進到以預測為基礎的生活;測量的確在許多領域帶來了巨大且持久的正面效應,從為天氣作準備到安排火車班次。然而,當我們執迷於給「未來」安上某個數字,就脫離了「現在」,即使我們沒有做著關於明天的夢,也不停地與數字牢牢綁在一起,讓當下就這麼溜走。也就是說,試圖測量,扭曲了我們的真實經驗。
換言之,一旦我們面臨需要加以理解的處境,而處理方法是進行測量,那麼,很可能我們從中唯一學到的東西,就是測量的結果本身。如果你將測量結果誤認為答案,你會忽視掉對真相的追尋。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特定處境——這件事為何發生?——還有最終的提問——我為什麼會存在?光憑一個數字或一串數字,都不足以回答上述問題。就像作家希爾(Nathan Hill)說的:「看清自我是一輩子的功課。」
本書主旨在成為一部智力的測量史,它將記錄我們如何透過數字,以固執(且徒勞地)期盼能出現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作為動力,在誤導下對於確定性的追尋。一路上我們從設法了解自己到設法控制自己、使自己趨於完美和進行自我分類,這麼做的同時,我們創造出極為強大的某種正統和觀點,多數人甚至無法看見那些背後被建立起來、用以支撐的假定和設想。我們是我們所設計出來的體制中——許許多多的體制——的囚犯。
只是,我們要弄清楚,這不是一個現代才發生的問題,我沒有將它的根源追溯到社群媒體,也沒有追溯到演算法,後者是我們現代科技生活的構成基礎。確切地說,這是許多個世紀以來,人類在智力方面的主要追尋。西方思想界的早期主角之一柏拉圖認為,我們可以利用某種正式而抽象的方法來計算倫理學,但亞里斯多德在檢視了所有涉及在內的人性變數之後得到的結論是:數學上的精準(在倫理學領域)純屬妄想。所以,我們老早就在爭論這個問題了。
如果你將目光投往更遠的東方,看向古印度哲學,你會發現一些精妙且仍然切題的論述,指涉了我們精心打造了一個心之牢籠:「我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的臨時小宇宙,它提供了一個避風港,代價是自我被困在它自己所建構的無知之中。」在凝望過一個無限可能性的深淵之後,我們選擇躲在可以計算的或然性假象背後。在那個長達幾個世紀的爭論過程中,我們做對了許多事,也做錯了許多事,不過近來錯的比對的多。我們搖搖晃晃地失去了平衡,被數字給壓垮。根據我的計算,最強有力的典範轉移發生在資本主義縮緊了對我們的掌控,以及減少了晉升到最高權力等級的人數,這時,為了測量而測量開始變得普遍,留下來的是如今被視為「進步」的尾巴搖狗現象。
資本家拼命的量化一切以找尋充分的獲利機會,導致我們被禁錮在一個以數字為基礎的現實中,但,那不是真的現實。當我們需要理解某事,我們的直覺是先測量它,然後再建構出理解,並策劃一些行動,這些行動無不以我們如何操縱那些被測量的事物,或以測量本身為重點。這樣的體制低估了所有無法被測量的事物,也不利於那些數學傾向較低的事物,還有最重要的是,它限制了我們全面了解自己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