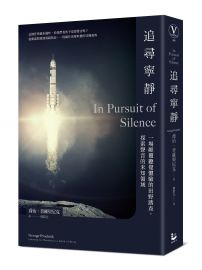前言
某年春天,我從布魯克林市區出發追尋寧靜。我住的地方距離追尋起點不遠,街道枝葉扶疏,在熙攘的城市裡,相對稱得上是一處靜謐天堂。我家有一座小花園,我睡覺、工作、陪伴摯愛家人的房間,都有陳舊但厚實的牆壁圍繞。但即使是這樣,我還是會被交通管制直升機吵醒,警笛和施工噪音也會令我升起一把無名火。
最近這陣子,比起實際施工的聲響,工地播放的音樂往往更惱人。這些也就罷了,還有公車尖銳的煞車聲,來往貨車震得人孔蓋轆轆作響,鄰居的音響系統更會不時爆音,防不勝防。我很怕自己變成聽到一丁點噪音就暴跳如雷的怪人,我其實只是素來喜歡安靜罷了。我喜歡聊天時不必繃緊神經,深怕聽不見對方說話。老實說吧,我喜歡書看到一半抬起頭,望著空氣發呆,任由思緒馳騁,不必擔心任何聲響當頭砸落,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探尋寧靜的第一個目標是貴格會。幾乎每種信仰都有眾多信眾在神明、虔心與寧靜的關聯之間求得心安。甚至,如果想在不同宗教間找到共通的神學(而非道德)立場,寧靜會是個很好的出發點。為什麼寧靜能喚起神聖虔誠的心境,比如一種祥和而適於冥思的感覺?對此我們或許都能舉出各式各樣的理由。
但若稍微深入探究,兩者間的關聯就沒那麼不言自明了。為什麼一個想像中無限且全能的形體,會與全然無聲有關?那些沉默代表漠不關心,甚至沉默就是與邪惡共謀的說法,又該怎麼解釋?為什麼這些想法會與沉默是金、靜默見神聖的想法共存?我想了解是什麼原因使得寧靜在人心目中,既是通往上帝的途徑,也是神性的反映?
我走訪布魯克林區的貴格教友聚會。聚會地點是一棟精巧可愛的石造建築,興建於十九世紀中期,屋內有高窗嵌在檸檬糖霜色調的牆壁上。一眼看去,室內安靜到異於尋常。直櫺窗框落影子,每當雲朵飄過天際,影子就在淺棕色的地毯上時隱時現。周圍沒有人發出聲音,一聲咳嗽也沒有。大家安安靜靜坐著,大多挺直了背脊靠著座席椅背,雙腿併攏,雙手合握成杯狀,或交疊在膝蓋上。陸陸續續有更多教友走進會堂,最後齊聚一堂的會眾不論種族或年齡,都十分多元。
我發現貴格會強調的安靜,最動人之處在於主要的訴求對象似乎與個人無關。雖然很多人閉上眼睛,但並非每一個人。而且,那種寧靜比起向內關注,更像是一種共同意識。時間彷彿過了很久,現場別無其他聲響,只有大門偶爾敞開又關上,讓更多教友加入。人們在座席上挪動身體,調整座位,長木椅吱吱嘎嘎發出輕響。
過了約二十分鐘,響起一陣數位震動,重複了幾次才被切掉。沒多久,一個四十歲出頭、身材魁梧的男人站了起來,赭紅色捲髮向後紮成馬尾,看上去很和善。「不好意思,剛才是我手機在響。我來的時候忘記關了。但在它響之前,我滿腦子正想著各種雜事——各種等著我去做的事在我腦中奔馳,我甚至問自己,我真的有時間來這裡嗎……然後手機就響了。」屋內迴盪起笑聲。「我們不能任由自己被世俗事物占用太多心思,忘記真正重要的事。無論如何,我
們都該騰出時間來上教會。」他坐回原位。
接下來的半小時陸陸續續有幾個人起身發言。會後不少人與我分享對貴格教會注重安靜的想法。一位蓄著濃密落腮鬍,活像邊境貿易商的男人告訴我,安靜也有程度之分,「有的時候,你覺得人人都沉進去了,也有的時候,安靜在大聲吟唱。」一位謙和有禮的女教授從事中世紀研究,她談到在安靜中禮拜是一種對抗因噪音而分心的手段。還有一名矮個子禿頭男子,眉毛很黑,戴著一副墨鏡,他形容安靜「絕對是一種傾聽」,因為貴格教友基本上相信,上帝在每一個人心中。
聖經《列王紀》第一章說,上帝不會現身於狂風暴雨或山搖地動,而是在災變過後,在那寧靜的細語中。究其要旨,很多信仰都有這個想法。對很多人來說,神正是透過寧靜對我們說話,當我們置身於寧靜,我們說的是靈魂的語言。
我的經驗不盡相同。我和宗教生活的短暫交會屢屢充滿希望,也每每以失望告終(不是對特定信仰失望,就是對我自己失望;不是對我自己失望,就是對特定信仰失望)。但事後回想起來,我走進天花板挑高的會堂,被沉默靜坐的人們環繞也才不過短短一會兒,卻已經比方才站在建築物入口處更能意識到陽光。
※
在探索寧靜之初,我也有另一次經驗,說明寧靜可以影響人對大自然的欣賞。我有個念頭盤桓不去:我覺得要研究這個主題,不去訪問太空人實在說不過去。在我想像中,太空人置身在人類所能想像最壯觀的噪音與寧靜並存的空間裡。世上還有比火箭發射更大的聲音嗎?又有哪裡能比太空深處更安靜?我猜想這兩種經驗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先後出現所產生的鮮明對比,想必會讓太空人對寧靜的本質有獨特的洞見。
跟休士頓交涉了幾個星期,我接到好消息,太空人威廉斯(Suni Williams)願意接受十五分鐘的採訪。我事先瞭解了她在美國太空總署的經歷。她乘坐過三十種不同的飛行器,登入太空時數超過兩千七百七十小時,而且有好一段時間是太空漫步的世界紀錄保持者。除了效力於直升機戰鬥中隊和美國海軍潛水小組、協助開發國際太空站的機械臂,她列舉自己的嗜好還包括跑步、游泳、單車、鐵人三項、風帆衝浪、雪板滑雪、弓箭狩獵。不論威廉斯會發表什麼看法,看來都不容小覷。
殊不知,威廉斯三兩句就謙虛地駁回了我九成的推測。火箭升空的噪音近年來幾乎已不值一提,比搭飛機聽見的噪音大不了多少。甚至,美國太空總署多年來潛心研究地球上最先進的減噪技術,因此,現在太空站上的就寢區是你所能期望找到的最安靜的地方。通風系統經過重新設計,貼合耳型的新款耳塞也不斷改良;吸音材料則內建於艙壁和艙門內部。
威廉斯告訴我,火箭升空其實不如想像中大聲,而漫步太空也沒有想像中安靜。地面指揮中心時時刻刻都會保持通話—「如果地面上不時有人要你做這個做那個,你不太能感受到太空的寧靜。」說得也是,我心想,地面支援團隊的聲音會直接灌入太空人耳裡,確保他們不會漂離航道,或以其他形式脫離原定任務。我為自己的無知羞得面紅耳赤,正打算提前結束採訪,但威廉斯沉默了一下又開口了。
「現在想想,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太空中感受到寧靜。我們在艙外活動,地面要我們等待黑夜通過再繼續。」(行星自轉一圈九十分鐘,其中太空船位在星球暗面的四十五分鐘,稱為「黑夜通過」。)等待的同時,休士頓傳來的嘰喳交談逐漸減弱,最後通訊暫時切斷。我們就這樣懸在太空站邊緣,靜靜的,只聽見自己呼吸。」威廉斯說,「那感覺就像戴上眼鏡……所有的景物忽然變得好清晰,就像大雨洗滌之後,忽然看見星星明亮無比,忽然可以望見太空深處。」在那短暫的寧靜中,威廉斯瞧見了我們這片宇宙的明亮無垠浩瀚。
※
梭羅曾寫下乘船遊歷康科特河和梅里麥克河的見聞。文中寫到,萬籟終歸為寧靜所用,也帶來更多寧靜。他在靜夜裡划船,船槳嘩啦濺起水花,水珠滴答落入水面,他不禁抬頭凝望,山谷回音將聲響傳入星空。他說各種聲響不過是寧靜的細語呢喃,唯有與寧靜形成對比,襯托出寧靜時,我們的聽覺神經才接收得到。這個對比互補的概念,作用是雙向的。某些聲音能突顯環繞著我們的寧靜,同時寧靜也會塑造聲音。我在旅程之初還有另一次遠征,去到了一間實驗室。我看到寧靜的音波如何在話語之下流動,讓我們能把聽見的聲音分割成有意義的詞句。
史維斯基博士(Mario Svirsky)是聽覺科學教授,任職於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的耳鼻喉科學系。提到他的專業領域,不免會注意到帥氣的史維斯基博士有一對大大的招風耳。他也願意突顯特色,在耳垂上打了洞穿環,耳環晶亮閃耀好比土星環。我請史維斯基博士說明聲音的過濾流程,想了解人何以能在嘈雜擁擠、尚有其他人在說話的室內,挑出自己想聽的聲音。
他對電腦螢幕比劃:「來,我秀給你看。首先製造一個聲音。」他對著連接電腦的麥克風說話:「哈囉,哈囉,哈囉。」就在他說話時,分別代表聲音不同頻率和時域調變的多色曲線也在螢幕上橫向躍動起來。「你看這裡有很多小小的峰尖—這些是波動群集,另外也有接近平坦的長直線。」他說,「這些長直線是聲音開窗的區域,也就是相對安靜的區段,能量較低的區段。因為有這些窗口排成一列,所以即使同一時間不只有一個人說話,我們也能分辨出單一個聲音。」
我盯著史維斯基博士分析話音波長的圖像良久。原來就連我們說話的同時,也有安靜嵌在字句之間,這個概念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當我們發出聲音,往往是內嵌在其中的片段安靜,讓聲音能夠發揮出溝通訊號的作用,而不至於化為噪音。至少理論上是這樣。史維斯基博士指著螢幕上一個波峰尖點聚集的亮部,再度開口。「在能量波峰重疊處,很明顯最難分辨所有聲音在說什麼。」他聳聳肩。「現在環境噪音增加了,危及的可能是我們話語之間安靜的窗口。」
英語「silence」一詞有多個詞源,從不同面向滲入語言之中。這個詞前身包含哥特語動詞「anasilan」,代表風漸漸止息,以及拉丁語「desinere」,意思是「停止」。這兩個詞源都顯示寧靜與行動中斷的概念有關。同理,追尋寧靜與追尋其他事物不同,因為對寧靜的追尋通常始於放棄追逐,放棄繼續將我們的意志和目光強加於這個世界。追尋寧靜不只是靜立不動,似乎還包含從紛擾的生活中後退一步,鮮有例外。
最先讓我了解到寧靜可以帶來什麼好處的幾個故事,重點都放在只有中斷忙碌循環時,才會發生的一種聆聽。但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我們就好比學會了要「注意月台間隙」,而且已經滾瓜爛熟,乃至於月台間隙好像根本不存在了一樣。我們活在一個從不間斷的時代,聽過即忘早已成為常態。兩相對照下,聲音似乎是一股將人固定在時空中的力量。聽到有人叫喚名字,我們會轉頭看;警報聲、寶寶的哭聲、垃圾車刺耳的絞輾聲等,會令我們夜半驚醒;鐘聲、鑼聲、哨聲、鼓聲、號角聲、鳴槍聲「響起」,則昭告一天的某個時刻,或宣布重大典禮活動開始。
我的畫家朋友亞當有次告訴我,他覺得聲音能引領人進入此時此地。亞當小時候因為生病導致全聾長達幾個月,他對那段時光記憶鮮明,並堅決認為這段經歷不全然是壞事。事實上,耳聾為他開啟了一個新世界,比起過去所知,他看見的景象能以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原創性交織在一起。這段經驗的影響力強烈到令他甘於將一生浸淫於視覺藝術。「聲音會把故事強加於你,」他說,「但那永遠是別人敘說的故事。我所經歷過的寧靜,則像在一個我能指揮的夢中清醒著。」
亞當的經驗很極端,可能只會吸引到願為寧靜獻身的追尋者。相形之下,把寧靜視為一種中斷和休息,或通往反省、更新與個人成長之路,這種相斷廣泛的概念對多數人就更容易產生共鳴。而且,除了我聽到許多故事見證了寧靜的這種潛能,神經科學界也有越來越多例證支持「寧靜是能產出碩果的暫停」的這種想法。
新近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技術的研究顯示,習慣安靜冥想的人,大腦運作效率明顯比無此習慣的人高,這可能和寧靜在各方面減去分散腦力的聽覺干擾,增強了我們的注意力有關。史丹佛大學的神經科學家以實例說明,當人在聽音樂時,是樂音之間的片刻靜默,激發了最激烈正向的大腦活動。這部分也反映人的大腦無時無刻不在追求完結。遇上寧靜,我們的心思才能向外延展。
※
無數個人故事和大量科學證據都顯示,寧靜對個人生命和人與世界的關係發揮了正面的影響。我訪問過的每個人幾乎都異口同聲說他們有多麼喜歡安靜,同時感嘆未能擁有更多的寧靜,好讓身、心、靈充電。但是,既然人人都重視寧靜,為什麼寧靜卻如此稀少?我很納悶,人們對於寧靜的好處似乎挺有共識,但為什麼與此同時,這個世界卻越來越吵?很多人被飽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噪音巨響圍攻,深以為苦,不論在陸、海、空,交通噪音無疑最能代表這個超出個人掌控的問題。同樣的,工程噪音、重工業,以及發電機的聲音,這些型態的噪音造成的壓力足可致死,尤其在開發中國家,轟隆作響的發電機無所不在,現今已有專家指出,在這些國家,每年或有四萬五千起心臟病發死亡可歸因於與噪音相關的心血管壓力。
要減低這些噪音巨響對人的侵擾,有更多可以採取也應採取的措施,但若只討論這些巨幅噪音,並不足以涵蓋故事的全貌。甚至,最龐大可恨的噪音源,也許掩蓋了一個更細微難察的深層噪音問題。我與聽力專家、人工耳蝸手術醫師、神經科學家談到寧靜的好處時,我認為真要說這些人與非專業人士有何區別,可能就是在他們眼中,我們的世界日益喧囂,而他們更知道要擔憂喧囂世界所帶來的危險。
二○○八年七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了研究,說明聽力喪失的發生率在美國正逼近傳染病等級。這份研究聽來難以置信,但現代美國人中,的確每三人就有一人患有程度不一的聽力障礙,而且多數是噪音所致。然而,與我對談的醫師和科學家,他們議論的不是電鑽和噴射機,也不是高速公路和工廠,反而是個人音響裝置。
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的人工耳蝸植入科主任羅蘭(Tom Roland)告訴我:「凡是有人戴著耳罩式或耳塞式耳機,你還能聽到音樂流洩出來,那個人就是在傷害自己的聽力。」聽力學專也提到手機和電子玩具。你能在市面上買到歌聲達一百零三分貝的孟漢娜公仔,或笑聲貫耳高達一百分貝的艾蒙搔癢娃娃—音量與一台雪上摩托車發動的聲音相當。至於電腦遊戲,音量往往飆得更高。
不過當神經科學家與我談到噪音,討論的就不是單次飆高的音量了,而是成人及兒童暴露於裝置的時間長短,例如冷氣空調和白噪音播放器,開啟裝置的人同時也正在喪失聽力。專家還提到一種噪音危害,上個世代的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奢侈的噪音,那就是我們選擇用來包圍自己的聲響。我們自願允許某些噪音存在,保護我們免受外界不請自來的騷動侵擾。
***
夏天的一個週末,我忽然明白了新時代這種噪音的特色。當時我隨大都會警察局的警員開著車在華盛頓特區巡邏,我想知道警方如何處理民眾的噪音申訴。史賓塞(John Spencer)長得人高馬大,人很客氣也很健談。他兒時在市內高犯罪率的街區長大,努力奮鬥多年終於當上分局的員警。不過,對於人性,對於法律管束人性的能力,他已經不抱太多幻想。
約莫凌晨一點,第一件噪音申訴傳來,指示我們駛進一條陰暗狹窄的巷弄。史賓塞警員把巡邏車的車速放慢到接近爬行,然後關掉轟轟作響的冷氣,因為如果依他喜好把冷氣開到最大,絕對聽不見車外半點聲音。不過即使關了冷氣,一樣什麼也沒聽見。史賓塞警員把車窗敞開一條縫,瞇眼望向周圍住家,還名副其實地豎起耳朵,但最後只是搖了搖頭。
車子一直駛進巷尾,他聳聳肩關上了車窗,我們繼續在街區漫無目的地兜圈子。不久我們開進一條酒吧林立的街道,音樂震天價響,顧客三五成群在人行道大呼小叫,推來擠去,滿溢到馬路上。我滿懷期待看向史賓塞警員,但他一樣聳了聳肩。對警察而言,只要沒有民眾抱怨,等同沒有噪音。
我們繼續巡邏。雖然適逢週五,又是七月四日國慶日前夕,我在警界的聯絡員警原本還跟我說,今晚肯定噪音不斷,但照目前看來,至少在執法人員耳裡,今晚將是平靜的一夜。車用無線電每隔一陣子會爆出聲響,聽見調度員回報某處有人鬥毆,但史賓塞員警聽了會搖搖頭,跟我說那不在我們的管轄範圍。即使調度員再度通報,他也只是搖頭,用些許被惹毛的不悅語氣重申,那是其他巡邏警的問題。
到了凌晨三點,史賓塞警員忽然轉頭對我說:「我跟你說件事吧。我們最近接到的家庭糾紛通報,絕大多數是噪音申訴。」什麼意思?我問他。「我去到這些人家裡,可能是夫妻、室友、或一家人,他們彼此吵成一團,大吼大叫,電視也開得很大聲,螢幕聲光四射,你根本無法思考。而且加上收音機的吵鬧,正巧又有人下班回家想休息或睡覺。
他們為什麼吵架其實很明顯。他們是為了噪音吵架。但問題就在於,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他們只是一回家就把所有設備全部打開!所以,我第一件事會告訴他們:『聽好,現在不用跟我解釋你們在吵什麼!先去把音樂給關了。遊戲機關掉,電視也關掉。』然後我會讓他們坐下來冷靜一分鐘,再問他們:『現在心情不一樣了吧?你們吵架的真正原因,就是家裡太吵了。現在還有話要說嗎?有嗎?』你一定會驚訝,事情往往這樣就解決了。」
這種新時代的噪音讓我意識到,我的追尋必須分為兩個方向。除了理解人對寧靜的追尋,也有必要探究人對噪音的追尋。這兩者是相生的—各自以各自的方式對彼此反應。似乎有某種因素讓我們這個社會整體愛上了噪音,我們往往會否認有這麼一段狂熱而澎湃的戀情,或傾向一笑置之,彷彿那只是夏夜裡餘音繚繞的一時放縱。但意外的是,這一段情似乎頑固地緊跟不放,如果我們真要對養成寧靜做出重大投資,就得明白我們是如何與噪音糾纏上的。我們必須探討寧靜予人的好處,以及刺激我們日益喧囂的多重因素。這是問題的一體兩面。
這兩方向的追尋帶我前往許多地方:從神經生物學實驗室到禪園、大賣場及隔音材料商大會;從熙篤會隱修院到噪音測量器材製造商,乃至極限汽車音響大賽。我走過的每一處都為故事添加層次,我也在最終逐漸明白追尋寧靜之難—但這也是此刻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追尋寧靜的原因。我希望我的見聞可以啟發不同思維,思考社會投資寧靜對我們的生活也許能有哪些貢獻,也能多一分意識,想想我們在哪些方面可能正以高速飛馳,離我們自稱珍惜的寧靜遠
去。
這個發想有一部分的難處在於,如果是追尋噪音,我有無比信心會成功,但若要追尋寧靜,以寧靜一詞的嚴格定義來說,沒有人能夠真正勝利,除非他們心跳停止,生命終結。在這一生中追尋寧靜注定沒有盡頭也難臻完美,這也是追尋寧靜往往會將我們帶往內心深處的原因之一。
有鑑於此,舊金山灣區靜修禪院的住持魯西塔克(Gene Lushtak)跟我說了關於阿姜查(Ajahn Chah)的一段故事,阿姜查是二十一世紀泰國佛教界最著名的領袖。一日,一名年輕僧侶住進阿姜查住持的寺院。當時正逢附近鎮上的居民連日舉行慶典,徹夜載歌載舞。清晨三點僧侶晨起靜修時,民眾前晚的歡騰依然勢頭未減。終於有一天,年輕僧侶忍不住向阿姜查訴苦:「尊者,噪音妨礙我修行——外面那麼吵,害我不能好好靜坐!」「不是噪音害你煩惱,」阿姜查回答,「是你在為噪音煩惱。」魯西塔克解釋:「寧靜,不是我們心中以為的寧靜終於起了作用。而是當我反應平靜,那一刻就是寧靜。寧靜是我對事物本
應如何的抵抗。」
我在追尋過程中一再想起這股動人的情懷。事實上,這正表現出倡議寧靜背後的兩難:要如何有效地倡議寧靜,又避免比自己抗議的噪音源頭呼喊得更大聲?若說有方法破解這道難題,我相信必定包含我自己在探索之初認識到的那種敏銳聆聽。寫作本書一路以來,我發現我不時自問,大家想聽見的是什麼聲音?想阻隔的又是什麼聲音?也許,能夠反思那些不發聲則有不被聽見之虞的事物,就是對寧靜最響亮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