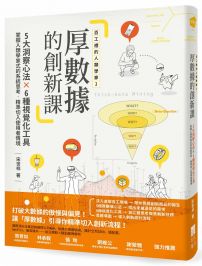Chapter 15
精靈寶可夢:當「異想體系」化為真實的集體經驗
從掌上型遊戲機Gameboy到智慧型手機, Pokémon以可愛為基調風靡全球 。
透過擴增實境技術,遊戲原本的異想體系、狩獵採集、社交互動,
在虛實整合的世界裡形成真實的集體經驗。
《精靈寶可夢GO》(Pokémon Go)是一款在二○一六年發售的遊戲,時至今日熱度稍退,但影響力依舊。以台灣來說,二○一八年元宵節在嘉義舉辦的台灣燈會,藉此多吸收了五十萬遊客。同年十一月於台南奇美博物館所舉辦的寶可夢活動,短短五天內吸引了百萬玩家前往。
回想一下這款遊戲剛上市的那一週,在遊戲開放下載的當天,紐約中央公園在半夜突然湧進難以計數的人潮,只因爲突然有人在網路上通知在那裡可以捕捉到「水伊布」這隻寶可夢。還有人因為這款遊戲跌下山谷受傷,或是被搶劫,全球報導《精靈寶可夢GO》相關現象的新聞在那幾天不絕於媒體。
這款遊戲的爆紅幾乎已經是「社會現象」等級,以至於不論從哪個方面切入似乎都不足以完整解釋它成功的理由。而身為人類學家,在關於《精靈寶可夢GO》的眾多現象之中最先吸引我注意的是:為什麼較少看到小孩在玩?為什麼極度熱衷的玩家多是二十五歲以上的大人?或許從這些玩家的成長背景出發,可以探索這個現象的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鍵概念1】可愛文化
「可愛」為日本消費文化的特徵之一。以皮卡丘為首的神奇寶貝有著以可愛為基調的強悍,藉非擬人化形象塑造「模糊性」,讓角色們帶來了「收服」與「順從」的想像,陪伴玩家或觀眾進入異想世界完成冒險。
【關鍵概念2】社交性・社交貨幣
意指一項事物是否具有促成社會互動與形成社會關係的功能。Pokémon的原始設計關切孩子們社交互動的可能,透過遊戲機的連線功能「交換」神奇寶貝遂成為重點,除了增加遊戲本身的「社交性」,並使其快速成為一種社交貨幣。
【關鍵概念3】AR虛實整合
《精靈寶可夢GO》的擴增實境設計(AR, Augmented Reality)讓我們重新定義空間,在移動過程之中體驗到前所未有的真實感,路上遇到的遊戲角色不再是虛擬的,而是現身真實空間,和所有人一起看到,人類的社會關係被延伸到虛實整合的空間之中。
【關鍵概念4】狩獵採集
「狩獵採集」是人類最早期的生存覓食模式。《精靈寶可夢GO》在整體設計上回應並喚醒了這項能力,帶我們進入虛實整合的世界,化身獵人捕獵野生動物,到處翻找Pokestop好補充工具,以求延續自己在這個遊戲世界裡的生存。
【關鍵概念5】遊戲的外掛性
在當代強調理性的社會裡,成人不同於孩童,更需要借助某種「外掛」,即別於常態的外在機制,來進入遊玩的狀態,找到孩子般玩的樂趣,這個機制往往就是遊戲。也就是說需要透過遊戲進入遊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神奇寶貝在美國:可愛卻強悍的戰士
一九九○年代「神奇寶貝」註1不僅流行於台灣與日本,在美國引發的風潮也引起學者們的重視。美國杜克大學人類學家安.艾莉森(Anne Allison)在二○○三年的論文〈Portable monsters and commodity cuteness: Pokémon as Japan’s new global power〉中便指出,神奇寶貝代表著日本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的影響力,不僅對美國兒童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成為跨國的語言,形成全球孩子的集體經驗與溝通方式。 (註1:Pokémon在台灣原稱為「神奇寶貝」,後來官方改為「精靈寶可夢」,為了還原語言使用的脈絡,本文除了遊戲名稱之外,使用「神奇寶貝」與Pokémon,以表示對於文中人物、空間與歷史脈絡的尊重。)
艾莉森對神奇寶貝的分析,首先著重在「可愛」之上。「可愛」已經成為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相關的商業應用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年代,伴隨著漫畫的流行而逐漸成熟,並且快速地應用在各種商業領域。一九八○年代,日本的全日空航空率先運用「史奴比」與「大力水手」等角色來吸引女性消費者。從消費族群來看,一開始消費「可愛」的多為少女,但隨著這個文化逐漸成熟,「可愛」也演變為整個日本消費上的特徵之一。
以皮卡丘為首的神奇寶貝,造型上有別於迪士尼動畫角色的擬人化(如米老鼠與唐老鴨),讓神奇寶貝的形象擁有一種「模糊性」(ambuiguity),於是這個有如真實生物的角色帶來了「收服」與「順從」的想像,使得角色們能陪伴玩家或是觀眾進入一個異想世界,讓玩家能從現實中脫離,完成一場又一場的冒險。如同艾莉森指出:「皮卡丘不只可愛,而且極度強悍。牠像是個依賴的小孩一樣站在小智的肩膀上,但在牠柔順的外表下卻是一名強大的戰士。」
然而,這樣一個異想世界,還是得呼應到現實世界的差異性。艾莉森分析美日兩國在動畫內容設定上的差異,在美版動畫中,弱化了神奇寶貝的重要性,反而更強調男女主角的英雄性格:「美國版的小智更像一名領導角色,也更像是一名英雄,這符合了美國文化。」
★ 遊戲的「交換」設計增加社交互動
《神奇寶貝》遊戲設計師田尻智在遊戲的設計過程中,注意到一九九○年代後成長的兒童,他們的父母親屬於戰後嬰兒潮世代,對於兒童的教育極為重視,很容易過度看重學業成績。因此在遊戲設計之初,便強調要讓小朋友從後工業時代社會的壓力中解放,找回消失的遊樂時空,並且滿足當代孩童需要陪伴的需求。
為了讓孩子們有社交互動的可能,「交換」成為《神奇寶貝》遊戲的重點之一,讓孩子們可以透過遊戲機的連線功能交換到各自擁有的神奇寶貝。這樣的設計除了增加遊戲本身的「社交性」,也讓這款遊戲更快速地成為一種社交貨幣(social currency),讓不少小朋友能在同儕之間真的擁有「神奇寶貝大師」的地位。這些細節都讓Pokémon成為爆紅的遊戲角色,並且超越了遊戲,如同艾莉森所說,成為一種「口袋裡的親密」(pocket intimacy)。
★ 一九九○年代兒童文化浪潮的成年延伸
《神奇寶貝》當年也同時在台灣的小學生之間形成一股旋風。我還記得大學時期在救國團擔任兒童夏令營營隊服務員時,為了和當時的小學生學員打成一片,還特別去買了一張大大的「神奇寶貝圖鑑」,背下所有神奇寶貝的名字,並依據當中的分類體系與生態做成考題,好在遊覽車上或是活動空檔和小朋友們玩搶答遊戲。
若從數字上來看,更可以看出這樣的文化散布得有多廣。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一九九六年第一代《精靈寶可夢紅‧綠》,截至二○一一年,全世界的同名作品遊戲銷售量已達三千萬套。而本編系列,即由《精靈寶可夢紅‧綠》到任天堂DS《黑‧白》的十九個版本的銷售量,到二○一一年為止已達一億六千萬套以上。換言之,《神奇寶貝》已經不只是一個遊戲,而是一個世代的代表,更是一種文化。甚至曾經在遊戲中體驗到的內容,也感染了其他原本不在這個文化體系中的人。舉例來說,我們的日常生活語彙出現「捕獲到野生XXX」或是「解開XXX的成就」,都可以說是受到相關遊戲的影響。
拉長時間脈絡來看,兒童的成長過程往往是下一個世代價值觀的建立過程。如同迪士尼早期主打戰後嬰兒潮的兒童市場,時至今日迪士尼早已成為美國文化的代表之一,在美國的文化生產中至關重要。以美國文化為例,如果《星際大戰》是一九八○年代的童年重要回憶,那麼說一九九○年代出生的孩子是「神奇寶貝世代」一點也不為過。這些當年在Gameboy上玩《神奇寶貝》的小孩都已經長大成人,在美國多半已經是進入社會好一陣子的青年,伴隨著個人的行動能力與經濟能力的提升,伴隨著童年記憶的召喚,《精靈寶可夢GO》這樣的遊戲怎麼會不爆紅呢?
換句話說,這款遊戲不是只給小孩玩的,真正感受到其中的意義與召喚的,是那些一九九○年代後出生的孩子們。《神奇寶貝》是他們成長的共同歷程,是曾經居住過的宇宙。而今,藉著《精靈寶可夢GO》,他們不是與自己的童年相遇,而是記憶深處對這個遊戲世界的想像,終於活生生地實現了。回頭來看網路上的《精靈寶可夢GO》玩家影像多半是大人,我們當然可以推論那是由於小孩子不被允許像這些成人一樣到處亂跑,但若從上述角度來分析,這個「為何極少看到小孩?」的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 虛擬遊戲的真實空間體驗
此外,我們也應注意到,隨著行動裝置的發達,手機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神奇寶貝球」(Pokémon Ball),我們早已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手機機體的相機,來捕捉各種生活裡的人物與景象。我們也透過各種分享機制,如LINE或是微信等通訊軟體分享手機上捕獲的資訊。Facebook、Instagram等社群軟體,基本上也像是一本本的「神奇寶貝圖鑑」,記錄著我們的捕捉紀錄。而擴增實境(AR)技術的發展,更讓手機不單是想像上的「寶可夢球」,而是真正地帶領人走進神奇寶貝的世界,向著成為「寶可夢大師」 的頭銜前進。
當然,我們也從《精靈寶可夢GO》這款遊戲當中看到了人對於「空間」的全新體驗 。擴增實境的設計讓我們重新定義空間,對於空間的探索向前進了一個維度,更重要的是在移動過程之中,我們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實感。路上遇到的皮卡丘不再是虛擬的皮卡丘,而是現身在真實空間的皮卡丘,並且是和所有人一起看到的皮卡丘。遊戲釋放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把人類的社會關係延伸到虛擬的數位空間裡,又進入到這虛實整合的空間之中。當有越來越多人在真實世界裡透過這款遊戲得到了集體經驗,我們還能說這只是虛擬的遊戲嗎?難道這不是真正的社會生活?
★ 虛實整合時代的狩獵採集
《精靈寶可夢GO》帶我們進入到虛實整合的世界,同時讓玩家們彷彿重新回到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的「狩獵採集」(hunting-gathering)階段,化身為獵人捕獵野生動物,也到處翻找Pokestop(驛站)好得到工具的補充,為的就是能夠延續自己在這個遊戲世界裡的生存。
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策略之一,狩獵與採集始終隨著基因遺傳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也是人類最為基本的求生本能。《精靈寶可夢GO》在整體設計上回應了這項能力,甚至像是要喚醒這樣的能力。當我們開啟遊戲在路上行走,就如同走入一個真實的生態世界,這些神奇寶貝也宛如真實的生物一樣神出鬼沒,突然在手機上的地圖裡冒出來。隨著遊戲時間越來越久,玩家們也逐漸累積經驗,就像一個熟練的獵人一樣,漸漸地能歸納出哪些地方比較好抓,甚至哪些地方可能出現什麼樣的神奇寶貝。我們甚至可以說Pokestop上灑櫻花其實就是獵人的陷阱,幫助自己用便利的方式捕捉到神奇寶貝,提升狩獵的效率。
如果我們接受了《精靈寶可夢GO》是一個狩獵採集的遊戲,那麼到底玩家們在狩獵採集些什麼?說穿了,手機上的每一隻神奇寶貝其實都是虛擬空間裡的畫素與程式編碼,但為何這些角色符號卻是如此真實?在我看來,借用人類學家阿佛瑞德.吉爾(Alfred Gell)的概念,每一隻神奇寶貝在遊戲的娛樂效果之外,都可以是一個「索引」(index),觸發了玩家們的回應(response)、推論(inferences)或詮釋(interpretations)。牠們是整個神奇寶貝生態系統的一種虛擬生物,是許多人童年的代稱,還是一連串動漫所累積起來的故事,更是這個網路時代的一個代表性事件。因此,在《精靈寶可夢GO》中用手機抓神奇寶貝,除了是參與整個事件之外,更是把自己放在故事之中,回到一段童年時光,並且進入到一個龐大的生態體系裡。於此,發揮動能(agency)影響我們的不單單是一個手機遊戲軟體,而是龐大的文化意義符碼叢集。
從這個角度來看,《精靈寶可夢GO》是社交貨幣也是文化貨幣(cultural currency),參與其中的人就像部落裡的狩獵採集者一樣,但他們不是感受到生理上的飢餓,而是感受到社交與文化上的需求,進而投入遊戲歷程之中,好換取相對應的社會與文化資源。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可以說安裝了《精靈寶可夢GO》遊戲的手機就是虛實整合世界的手斧。在靈長類的演化史中,南方古猿與早期人屬就開始使用手斧,從一開始的刮器刮下骨頭上的肉,逐漸伴隨著人類的演化轉變成為石斧等石器,成為人類在蠻荒世界最重要的生活工具。而今,智慧型手機也如同祖先們所使用的手斧一樣,成為我們探索虛實整合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但從人類發明器物的演化軌跡來看,或許也能大膽預測在這當中的探索適應過程裡,人類對於手機本身的依賴,會像曾經對於手斧的依賴一樣,將越來越低。
★ 長輩玩家調劑生活
《精靈寶可夢GO》不只讓台灣不同世代的人都有機會接觸到擴增實境這項科技,還讓不同年齡的人有機會「玩」在一起。以我的親身經歷為例,二○一六年光復節晚上十一點,雖然隔天要上班,在蓮池潭的高雄物產中心前廣場,還是擠滿了快一百個人,在那邊撒花抓寶。大部分人都靜靜地和自己的朋友坐著邊抓寶邊聊天,但有七、八位中年大哥、大姊聚集在一起熱烈討論。一般來說,《精靈寶可夢GO》玩家不會這樣互動,但當一個「事件」發生,比方說某個稀有怪在地圖上出現,玩家開始集體性地移動,就會在過程中開始有些交流,交換彼此的情報。
我湊過去聽,原來其中一位大姊在教其他人如何下載一個還能用的「抓寶雷達」。這位大姊說要搜尋「P~O~K~E~T~R~A~C~K」,但現場有些長輩對於英文和手機操作都不是很熟悉,更看不懂英文介面。於是,大家就在那邊討論起來,旁邊一位大哥便請我幫忙下載這個應用程式。趁著這個機會,我好奇地問其中兩位大姊怎麼踏上「抓寶」的旅程? 「這是我兒子幫我下載的。」大姊A說。「我也是兒子幫我下載的,一開始我還覺得怎麼會有人愛玩這個,結果現在他都沒在玩了,但我還每天在抓。」大姊B回答。
我繼續問他們為什麼想玩這款遊戲?「遊戲裡的角色很可愛」、「收集到沒有抓過的,很有成就感」、「就用這個讓我自己運動」,這些都是他們的回答,但隱藏在答案背後的其實就是對於生活的調劑。原本的生活就是當家庭主婦,或是下班之後回家做晚餐、吃晚飯,然後看電視、睡覺。現在,有《精靈寶可夢GO》讓他們願意出來走動,偶爾還能跟一起出來玩的玩家聊上幾句,顯得自己很能跟得上時代,心情也變得比較好。雖然年輕人或小朋友也有在玩《精靈寶可夢GO》,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款遊戲在台灣中年甚至老年人口之中有了自己的功能角色。
如同前文曾經提過,年輕人對於《精靈寶可夢GO》的認知與接受,往往先來自於童年的動漫經驗,以及之前的電玩回憶,加上同儕的力量,讓他們成為這款遊戲的玩家。但是這些長輩玩遊戲的經驗完全不同,他們沒有動漫的經驗,對於遊戲背後的符碼內容所知甚少,對他們來說,他們更想在遊戲當中去享受「收集」的成就感,或是單純玩遊戲的快樂。
★ 大人的遊玩需要「外掛」機制
對於人類學家來說,遊玩(play)並不光只是嬉戲而已,而是人類在經濟或邏輯理性之外重要的社會行為。遊戲、藝術、運動,甚至語言上的玩笑,其實都是遊玩的各種表現形式。人類學家愛德華.諾貝克(Edward Norbeck)在回顧許多民族誌資料之後指出,人在遊玩的時候,往往在認知與心理狀態上,都不是處於一般的狀態。創意、愉悅等特殊的心理或情緒反應其實都是遊玩非常重要的特徵。在這裡,似乎可以從《精靈寶可夢GO》的遊玩做一個人類學式的推論:「遊玩的外掛性」。
人類隨著成長發展,「遊玩」的本能不斷發展,我們一方面透過遊玩認識世界,世界也透過遊玩形塑了我們每一個人,甚至是集體性的文化(參見〈電玩上癮〉)。然而,在另一方面,伴隨著我們智力發展與社會化,也可以發現「遊玩」越來越需要「外掛」的道具。
「外掛」在線上遊戲領域原本指的是一種應用程式,來獲取遊戲內的成績或成就。但在這裡,我所謂的「外掛性」指的是我們必須透過某種儀式化的機制,才有可能進入到遊玩的狀態。而這種機制往往就是「遊戲」(game)。
舉個例子來講,小孩子往往自己就能玩得很開心,一個玩偶,一塊石頭,他們都能發揮出想像力,用這個玩具「玩」了起來。然而,在大人的世界裡,我們依然需要「玩」,但一方面不被允許隨時能玩,另一方面也失去了隨時進入遊玩狀態的能力。因此,我們越來越依賴遊戲來帶領我們進入遊玩的狀態。
延伸下去,遊戲主機、球賽、音樂會、演唱會、派對等等,都可以看成是一種「遊玩的外掛性」。特別是在當代強調理性的社會型態裡,日常生活中往往都是已經排定好的行程與計畫,讓我們變得更需要一種別於常態的「外掛」(外在的機制),把我們拉入遊玩的狀態。
玩《精靈寶可夢GO》所帶來的樂趣,讓我碰到的大哥大姊玩家們樂此不疲。他們或許不懂背後的動漫故事,但他們在遊戲中的成就感與開心再真實不過。從中我們也更能理解「抓寶雷達」地圖對於他們的意義:他們的人生因為「外掛」重新找到了孩子般的「遊玩樂趣」,他們期待之前的成就感與遊戲樂趣能快快再回來。
不管你有沒有玩過《精靈寶可夢GO》遊戲,它帶來的集體經驗已經成為一種基礎或是入口,宣告一個虛實整合世界的到來,宣告人類必須適應這樣的文化變遷。未來的數位設計會在這一次全球性體驗之中產生劇烈變化,後續開發的擴增實境應用程式勢必會在人類社會與文化的各個面向發揮更重要的功能,而我們都將目睹這個演化的過程,也要決定自己在這樣的變遷過程當中所在的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創新應用思考題】
Q1. 你能否運用「懷舊」的元素,發想一個結合現代影音科技的遊戲,召喚出現代人的童年記憶?
Q2. 你能否運用一個新的視覺科技,發想出一個寶可夢遊戲的新玩法,讓這些角色更能融入當代的生活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