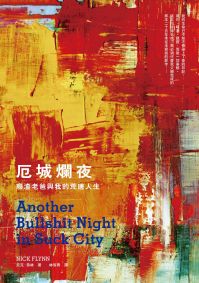辯解者
如果你當時問我關於父親的事──那些他住在門口、收容所和銀行提款機小房間的日子,我會說,他死了,或說,失蹤了,或是,我不知道他人在哪。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全都算實話。我會說,我不認識他,我出生沒多久我媽就離開他,也可能是在臨盆前。不過這說法撐不了太久便動搖了。
早在他成為遊民前我便聽過耳語,察覺他越繞越近,我們彼此環繞周旋,像兩顆沒有下錨漂流的行星。我知道他開計程車,這點我媽可能提過,雖然她幾乎不說他的事,除了他不在我們身邊更好以外。我甚至知道他開哪種車,城市車隊,黑白雙色。二十出頭,我從大學休學並搬往波士頓後,我會不由自主地察看每台經過的計程車,我不確定這代表什麼,或者我會怎麼做,萬一車裡的人確實是我父親的話。我知道他原本住在燈塔山一間出租公寓,幾年後他被掃地出門,之後搬進計程車,連續開上二十四小時,直到他狂飲伏特加喝到茫,撞到某人或某物,或被警察取締駕照。他被趕出去的前一天,是我成年以來頭一回和他面對面,記憶中是這輩子第二次:他打給我,叫我開我的貨卡車去他公寓。這是我第一次在電話裡聽見他的聲音。兩個月後他在我工作的遊民收容所出現要我給他一張床。
松樹街會館曾經是(現在也仍然是)波士頓最大的收容所。最進步的。我爸來的時候我已經在那工作了三年,剛開始是諮商師,之後當社工。最初接觸我爸時他不算無家可歸,確實算邊緣化,但並非無處容身。我記得他來的那天,夜裡仍稍帶寒意,他高舉雙手走進來,因為每個「訪客」都得被搜身,禁止攜帶瓶罐和武器。這是頭條規則。
現在問我他的事我會說,有房子住。十二年。領津貼。符合第八條款 。身心障礙者。我要感謝你繳稅幫他付房租,除非你也符合第八條款,或是你讀到這本書時他又被趕出去。現在問我,我會說他是根幹他媽砍剩的老樹幹,得用炸藥才能擺脫這混帳東西。
在他失去房子前,如果我願意,我隨時都能見到他。他從不難找。沒有人真的那麼難找。即使是他被禁止進入收容所的那幾個月,我也知道三四處他在外頭休憩的地方,每處都深深烙印在我腦中的城市地圖。現在我看看日曆,便能約略標出他的所在地。我見過他公寓內部,了解他的日常作息。月初他領到支票後,(但願他會)用支票付清房租,然後買一或三加侖伏特加。要是接近月初他會在屋內喝酒,此時很容易找到他。要是接近月底他就得出外碰運氣,到熱食發放處 解決三餐,那就較難掌握他的行蹤,至少中午時分如此。他沒電話,要是我想見他必須到他公寓樓下按門鈴,門鈴上用膠帶貼著我的姓。大約一分鐘後他才會開門讓我上樓,他的手指在按鈕上結結巴巴。要不然他的公寓便空無一人,沒人開門讓我進去,那我就會漫步聯邦大道沿途找他,或在當地的Dunkin’ Donuts坐等他出現。
要是我能將這些年淬煉成電視遊戲節目,我要叫它辯解者。本日節目:「遺棄街頭乎伊死的父親們」。我會穿著不合身的西裝,坐在三四個參賽者之中,在槁木死灰的燈光下看起來一臉悔不當初,或目空一切,或諱莫高深。時機一到,等我敘述完精簡版的故事後,主持人便介紹我父親出場,攝影機一邊移動拍攝場內觀眾的反應,我們一邊在全國觀眾前上演大團圓之類的戲碼。進廣告前我的臉下方會打上一行字幕──他希望他爸翹辮子。
精簡版的故事:
我在1984至1990年間在遊民收容所工作。1987年我父親成為街友,接下來五年都是如此。
要是下了雪我便會開暖氣,我住的閣樓在風化區,是一棟大樓的一整層,底下是廢棄的脫衣舞廳,從窗外望出去便是波士頓所謂的「成人娛樂區」。
「裸眼」的招牌,女人霓虹的雙腿在一隻閃爍的大眼睛上開開闔闔。玻璃鞋。花花世界。
車子微微打滑,足跡簇簇而至。微光在雪白的街道上跳躍。我清楚那蘊含的風險。
許多(大部分)無家可歸的遊民死去,或遲或早,就這麼死了,以最難想像,又最常見的方式。羅伯特庫努曼在南區靠牆直挺地坐著,看來像在等公車,硬生生被凍僵。佛格斯伍茲睡在他姊妹家車庫的紙箱中,試著用一罐斯特諾酒精膏取暖,點燃了酒精,也燒死了自己。
夏日,我會聽聞在車站附近鐵軌發現臉朝下趴著的人,並懷疑那具屍體是不是我父親。反射作用。白人男性,五十幾,六十多,任何人都有可能。
偶爾我會看見我父親,在前往另一處不知名所在的途中走路經過我家。我大可給他一把鑰匙,提供他容身之處。沙發床,普通床。但我從未如此做。要是讓他進屋我就會變成他,會模糊我們之間的界線,我腦中慢動作播放的車禍事故會加速發生。搬家公司卡車側邊有句標語寫著「與你同行到哪都行」,被某個破壞公物的傢伙或心懷不滿的員工塗改成「與你同行下地獄去」。倘若我接近溺水的人他會拽著我下沉。我不要當他的救生艇。
梭魚
(1956)強納生,幾年後他會成為我父親,又一個夏天北上回鄉。過去幾個冬季,自他從大學輟學,便在棕櫚灘 外一艘有照漁船上工作。當他回到麻薩諸塞州,便在西楚伊特父母家和波士頓友人家之間遊走。如蒸氣。無處不在。無處可尋。西楚伊特(來自美洲原住民語西圖伊,意思是「冷冽的小溪」),一處距波士頓南方約三十英哩的漁業小鎮,是城裡一些政客夏日避暑之地,他們封它「愛爾蘭蔚藍海岸」之名。平日週間強納生住家裡,替當地營建業大亨工作。到了週末他北上溜去波士頓,借住燈塔山的朋友家裡,雷是他最好的朋友。雷是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藍領階級的後裔,他準時繳帳單而且對朋友很慷慨,這點對像強納生這種人來說變得越來越重要。可靠的雷。你的口袋裡用不著有很多錢,也沒人期待你多有錢。你可以過得像個落魄藝術家,也可以振作或隨波逐流。深色頭髮向後梳成油頭,一副臭屁樣,強納生要發達了,還幫自己取了個名號──「下一位美國大詩人」──掛在嘴上並往這條路邁進,懷抱一股披頭族 年代被視為雄心壯志的抱負。 他常身穿白色網球裝在哈佛廣場晃蕩,手臂挾著網球拍,儘管他根本不會打。可以釣雷德克里夫學院 的女孩,他說。他一直都不太起眼,用吹牛皮過度補償。雷製作珠寶,折彎叉子做戒指,用月長石做網裡的蜘蛛。往後幾年雷會開一間自己的工廠,製造飛彈內的塑膠大賺一筆──「沃巴克老爹 」,他的家族會這麼稱呼他。
某天下午在查爾斯街強納生用手肘碰了碰雷,向擁擠的人行道點了點頭:你看著,他說,等等會有個女孩走過來,她家會很有錢。她渴望成為藝術家但沒什麼天分。她來燈塔山為了感受這種氛圍,尋覓某個有天賦的人黏上去,想成為未經雕琢的鑽石背後那股力量,即使她依舊相信自己才是有天分的人。強納生瞇起眼睛想像他陽光普照的未來。她還不曉得,但她找的人就是我。
裘蒂,十七歲,暑假返鄉,在西楚伊特港口的咖啡館打工。一禎當時的照片秀出一位綁著深褐色馬尾的女孩,墨綠色眼睛,一抹難相處的微笑。強納生點了杯咖啡,和她攀談。他回憶:我想我們初識那晚就去約會了。你母親好美,老天!我有輛車,一台我借來還是搞來的爛東西。頭一晚我們便開車去約會。他的魅力,當時還沒那麼殘破(之後就會),也還沒在幾杯黃湯下肚後破功,在某種程度上吸引了裘蒂。她是有錢人,桀驁不馴又漂泊不定,在寄宿學校之間轉來轉去(目前從丹娜荷女中轉到松林之家高中)。她父親經營她爺爺的羊毛生意,在戰爭期間──制服、毛毯、毛氈──這類羊毛製品可是金雞母。強納生告訴裘蒂他回鎮上過暑假,做營建業,雖然實際上只是個工人,挖排水溝的。在棕櫚灘人人都知道他是「梭魚巴克,當地導遊」。當地?裘蒂問。他告訴她他還沒開始動筆的小說,他對小說的信念。梭魚。一半是大話,除了西楚伊特是個小鎮。她告訴他動身的時間;她離開後他一直等著。他們開車去佩嘉帝海灘,停車望海,此時夕陽在他倆身後西沉。他認識了她的家庭,知道他們在第一崖有避暑別墅,全鎮最大的房子。他以前在海灘上見過她,但當時她還小。他拔去一小瓶威士忌的塞子,給她幾口。他們聊彼此的家庭,他告訴她自己如何逃離父親(那個禿頭的下三濫,拉啥小提琴),遠遠逃離這個小鎮,為了蛻變成真男人。要是我留在這裡就死定了。她同樣和父親抗爭,覺得他不了解她,從沒試圖理解過。過去幾年來他一直跟祕書搞在一起,裘蒂發現了封信(「快了,親愛的,我們馬上就會在內華達州的雷諾遠離這一切。」)他們倆都讀沙林傑──她包包裡有本《麥田捕手》。她大聲念出目前為止最愛的段落:
「當我真的醉了,就會重新幹起想像腸子中彈的傻事。酒吧裡
就我一個人腸子中了顆子彈。我不斷把手伸進外套,捂着肚
皮,不讓血滴得滿地都是,我甚至不願意讓人知道我受了傷。
我努力掩飾不讓人知道我是個受了傷的豬娘養的。」
強納生把手伸進外套痛苦地彎腰。不對啦,她說,他是要掩飾痛苦耶。他的表情轉為堅忍。他們大笑。強納生認為他的小說就像這樣,用力剖開世界,而裘蒂願意相信他,至少今晚,和日後許多夜晚她會。剩下的暑假他們都在連結兩邊山崖的海灘碰面,倚靠著海堤,背著風,背著旁人,互比腳丫子大小,手心彼此交疊。他會告訴她更多關於小說的事,關於佛羅里達,關於碼頭的生活。當個挖水溝的詩人和當個只會挖水溝的差得遠了。他的家族在大蕭條年代飛黃騰達,他也會如此,不過是走自己的路。對作家來說燈塔山是最好的地方,他在那有朋友,有名氣──他承諾會帶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