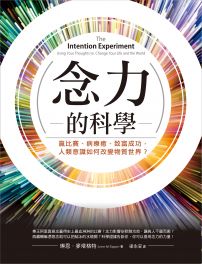第5章 進入超空間
6.對的心緒(結錄)
米契.克魯科夫(Mitch Krucoff)一九九四年回到美國時,滿腦子想著他從印度學來的各種醫療新觀念。他是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的心臟專家,先前與他的護理師蘇珊.克拉特(Suzanne Crater)一道接受邀請,前往布達巴底(Puttaparthi)的「聖諦醫院」(Sri Sathya Sai Institute of Higher Medicine)參訪指導。聖諦醫院開幕才一年,是印度教導師賽巴巴(Sathya Sai Baba)為了讓窮人得到現代西方醫療照料而創建,費用全免。院方邀請克魯科夫當心臟科顧問,看看需要添入哪些最先進的設備。
克魯科夫和克拉特對他們看到的一切大吃一驚。整家醫院無論是特殊的聲響與光線都充滿濃濃的宗教味,與各種先進的醫療設備顯得很不協調。牆壁上到處是印度教神祇的畫像。宗教味甚至就表現在醫院的建築本身。距離賽巴巴的修行處五英里,整座醫院看起來彷如一座泰姬瑪哈陵,兩棟側翼大樓彎成弧形,像是要給前來的人一個歡迎擁抱。一進大門是一個圓形大廳,造型肖似倒過來的心臟,尖端指向天空。
逗留期間,克魯科夫和克拉特注意到這種宗教氣氛對病人產生的奇特效果。許多病人來自極偏僻的鄉下地區,以前從未見過自來水。然而,雖然被診斷出得了威脅生命的重症,得去面對模樣嚇人的二十一世紀數位心臟儀器,他們卻無一流露出害怕表情。這與克魯科夫在美國習慣看到的病人大為不同:後者都是驚恐而絕望。
克魯科夫想要把這種設計引入美國的醫院。但要說服心臟科的同僚,他必須有堅強證據證明宗教氣氛有助於心臟手術,證明宗教信仰可以產生測量得到的生理效果。回美國的十八小時飛航途中,他與克拉特構思一個實驗計畫。他們知道,想要說服得了別人,就得把禱告的效果付諸測試,進行一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禱告實驗。
回到美國以後,克魯科夫開始翻查科學文獻,看看是否已有證明禱告具備療效的證據。他發現有十四個設計良好的實驗顯示禱告有正面效果。最著名實驗是一九八八年由藍竇夫.伯德(Randolph Byrd)進行,他找來一群基督徒,在冠狀動脈加護病房外為病人禱告。得到代禱的病人症狀明顯減輕,需要的用藥量和醫療介入都變少。「美國中部心臟研究院」(Mid-America Heart Institute)的一項實驗則顯示,各宗派基督徒的代禱可減少心臟病人一○%的症狀,復發現象也更少(這實驗差不多與塔格的愛滋病實驗發表於同一時間,被認為可以佐證塔格得到的結果)。
禱告被視為一種超級念力、一種攜手合作的努力:由人發出,由上帝執行治療。而在某些圈子,念力則被視為禱告的同義詞,而禱告又被視為治療的同義詞︰由你發出意念,由上帝付諸實行。事實上,許多意識研究者把早期的禱告實驗視為一種念力實驗,而且是種群體念力實驗,因為它們全都企圖用一群人在同一時間去影響同一事物。
不管這些早期實驗的結果多麼鼓舞人心,克魯科夫知道,他還需要更大規模和程序更緊密的實驗。為此,他發起了一個小型前導研究。他從鄰近的「德罕退伍軍人醫療中心」(Durham Veterans Affairs Medical Center)招募了一百五十個志願者,全是準備接受血管重建術和冠狀動脈支架手術的心臟病人。除了想知道禱告的效力以外,克魯科夫還想看看遠距治療等另類療法是否有效。他把病人分為五組,其中四組除接受標準醫藥治療以外,還各接受一種另類療法:
緊張放鬆法、療癒性接觸、心靈想像法和代禱。第五組病人只接受一般醫藥治療。每個病人的腦波、心跳、血壓都受到持續監測,以了解他們每一刻受影響的程度。
克魯科夫決定把禱告的「聲量」開到最大。在徵求志願的禱告團體時,他的護理師克拉特向全世界發出呼籲。她寫信給尼泊爾和法國的佛寺,又寫信到VirtualJerusalem.com 網站,請對方安排一些人到哭牆禱告。她還打電話給巴爾的摩的加爾默羅會修女,請她們在晚禱時為病人禱告。到最後,她共徵到七個禱告團體,包括基要派信徒、摩拉維亞派信徒、猶太教徒、佛教徒、天主教徒、浸信會信徒和聯合教會信徒。
每個禱告團體分配到幾個病人,他們只知道病人的姓名、年齡和病症。雖然克魯科夫讓各禱告團體自行決定禱告內容,卻規定禱告時必須說出病人的名字,以及祈求病人得到治療和康復。病人與參加研究的人員都不知道誰將被代禱。而在血管修復術進行後一個小時,將再進行身心療法。
實驗結果讓人印象深刻。接受另類療法的組別住院期間健康情況得到三○至五○%的改善,與對照組相比要少些併發症和血管硬化。但也有二五到三○%的病人情況變糟:死亡、心臟病發、心臟衰竭或血管硬化,或需要再做一次氣球擴張術。但在各種另類療法中,代禱是效果最顯著的一種。
不過,這個實驗還是太小了,不足以提供決定性結論,畢竟只有三十個病人得到代禱。
儘管如此,實驗結果還是讓克魯科夫深受鼓舞。他把這實驗命名為「智思訓練的監測與落實」﹝Monitor and Actualization of Noetic TRAinings,簡稱MANTRA(咒語)﹞,將結果發表在美國心臟協會。就連最保守的心臟科醫師現在也開始半信半疑遠距治療也許是有效的,而禱告又尤其對心臟病有幫助。
克魯科夫知道,他的實驗要更有影響力,必須擴大規模加以複製。於是,他發起了第二次實驗,取名「咒語二號」(MANTRA II),從杜克大學醫學中心和其他九家美國醫院招募來七百五十個病人,又找來十二個禱告團體。這一次禱告團體的人數更多,宗派背景也更紛紜,包括了英國的基督徒、尼泊爾的佛教徒、美國的伊斯蘭教徒和以色列的猶太教徒。受到前一個實驗的成功鼓舞,克魯科夫和杜克大學這一回大肆宣傳,號稱那是遠距禱告效力的一次超級實驗。
在「咒語二號」中,克魯科夫把病人分為四組。一組得到代禱;第二組接受經過特別設計的MIT療法﹝MIT therapy,包括音樂(Music)、想像(Imagery)和觸療(Touch)三部分﹞;第三組則是「MIT療法」加上代禱;第四組為對照組,只得到標準的醫學治療。接受「MIT療法」的病人在動血管重建手術之前被教導放鬆呼吸、想像自己身處最喜歡的地點,並聆聽自己選擇的安靜心神的音樂。之後,他們從專業治療師那裡接受十五分鐘療癒性接觸。
這些病人動手術時也可以帶著播放音樂的耳機。
這個新實驗的目的,是想看看代禱或「MIT療法」是否可以防止或減少病人住院時發生事故的機率。所謂的「事故」,是指死亡、再度心臟病發、需要動額外手術、再次住進加護病房,以及顯示心臟受到傷害的肌酸磷激酶竄升等。這一次,克魯科夫還想測試禱告的長程效果︰包括是否可以緩和病人情緒,是否可以減少病人出院後六個月內的死亡率和再入院率等。
克魯科夫的實驗恰恰進行於九一一恐怖攻擊和其餘波蕩漾期間。有三個月時間,死亡的病人相當多,讓克魯科夫不得不修改實驗的設計。他發展出一個兩梯隊的代禱策略,招募來十二個第二梯隊的禱告團體。一有新病人加入實驗,第一梯隊的禱告團體將為病人代禱,而第二梯隊的禱告團體則為第一梯隊的團體代禱。克魯科夫希望,這可以讓新加入的病人得到較多的禱告「劑量」,以期能與早已加入實驗的病人獲得相同「劑量」的禱告。
正因為宣傳做得很大,實驗得到的結果也加倍讓人失望。五個組別的病人住院期間的病情沒有任何差異。只有在動手術前接受過「MIT療法」的病人稍微減輕一點沮喪感。不管怎樣,大規模的「咒語二號」實驗仍然算以失敗收場。代禱看來並沒有讓任何病人的情況好一些。
在長程效果方面,代禱的確顯示出一些效力(例如病人的情緒較舒緩、再住院的比例減少,以及手術後六個月內的死亡率降低等),但這些效力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而且也不是實驗當初的焦點。
為了從巨大失敗中扳回一城,克魯科夫設法讓實驗結果刊登在英國知名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文中,他宣稱實驗結果讓他感到「振奮」,又認為人們對這些結果的解讀有誤。儘管如此,在懷疑論者眼裡,克魯科夫的實驗結果所傳遞的信息再簡單不過:生了病找人代禱是不管用的。
差不多同一時間,在一九九七年,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展開了一項為期兩年的禱告效力實驗,對象是一些最近才離開加護病房的心臟血管疾病患者。近八百個病人被分為兩組:一組是高危險群(帶有一個或以上危險因素的,如糖尿病、心臟病發過等),一組是低危險群(除既有的症狀外沒有危險因素)。兩組病人又再各分為兩組。其中各有一組除接受一般醫藥照料外,還會由五個人一週代禱一次,為期二十六週。另兩組則只是繼續接受標準醫藥治療。
研究者在實驗後得出的結論是,禱告對死亡率、再發率、需要再接受治療或再住院的機率,都毫無影響。雖然「被代禱組」和「未被代禱組」的表現是有一些小差異,這些差異並不被視為是顯著的。
為了一勞永逸解決禱告是否有效的疑問,本森想出一個雄心勃勃的計畫。本森是主流醫學與另類醫學這兩個敵對陣營理想的和事佬人選︰他一方面是哈佛醫學院的教授,另一方面又對另類療法的研究深感興趣,還為此創立了「身心醫學研究院」(Mind/Body Medical Institute),以研究身心療法的效果,甚至創造了一個新詞來描述身心療法的效果:「放鬆反應」(the relaxation response)。有他的名字背書,禱告實驗的結果將可望獲得保守陣營認可。為了這個實驗,本森找來另五個美國醫學重鎮參與,其中包括梅約醫學中心。他把實驗取名「代禱治療效應研究」(Study of Therapeutic Effects of Intercessory Prayer, STEP),預期它將是歷史上最大規模和最嚴謹的禱告實驗。
這實驗招募來一千八百名準備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病人,分為三組。其中兩組一組有人代禱、一組沒有,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有沒有人代禱。另一組有人代禱且被告知。本森之所以如此設計,是為了分離開兩個可能產生作用的因素:一是禱告本身效力,二是病人的預期心理。這樣子,他就可以對照出預期心理的效力。
禱告團體方面,本森招募來天主教修士和另外三個基督教派的成員:密蘇里州的聖保羅修道院(St. Paul Monastery)、麻塞諸塞州一個加爾默羅會修女團體,以及堪薩斯城外的「寧靜合一」(Silent Unity)傳道會。禱告團隊裡沒有伊斯蘭教徒或猶太教徒,是因為本森找不到願意配合他實驗設計的非基督徒團體。禱告團體會被告知病人的名字和姓氏首字母。禱告內容並無特殊規定,但必須包含以下字句:「手術成功,復原迅速,無併發症。」禱告團體持續禱告三十天,這期間病人若發生任何重大事故(如出現併發症或死亡),禱告團體都會接獲通知。
研究結果震驚世界,卻讓研究者感到困惑。最困惑的人是本森,因為一直以來他投入許多時間鼓吹心靈的治病能力。研究團隊本來預期,獲益最大的應是「有人代禱又被告知」的組別,其次是「有人代禱但未被告知」的組別,至於「沒人代禱又沒被告知」的組別則受益最少。但實驗結果卻顯示,有沒有人代禱或有沒有被告知的組別,表現沒有多大分別。不只這樣,實驗結果還跟研究團隊的預期恰恰相反。「有人代禱又被告知」的組別表現最差:有五九%的病人出現非手術引起的併發症,而未被代禱的組別只有五二%病人是這樣。就連「有人代禱但未被告知」的組別,心臟病發或中風的比例也微微高於沒人代禱的組別。在「有人代禱但未被告知」的病人中間,有一○%出現嚴重的手術併發症,沒人代禱的病人是一三%。
本森和他的團隊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種結果。他們甚至懷疑病人是不是得了「表現焦慮症」(performance anxiety),即因為太期望禱告有效力而增加了心理壓力。許多評論者認為,這實驗證明了禱告不只無益,甚至可能有害—至少是證明了禱告的效力是無法透過科學實驗測試。克魯科夫也受邀為這實驗撰寫了一篇評論,而他指出,這實驗確實顯示出禱告有效果—但卻是負面效果。他建議人們應該摒棄一種普遍想法,不要以為禱告一定會帶來好結果,因為「在某些環境下,好意、充滿愛心和發自真誠的禱告說不定反而造成反效果,會傷害甚至殺死脆弱的病人。」
《美國心臟期刊》(American Heart Journal)把實驗結果公布在線上,而本森團隊也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本森提醒媒體,代禱治療效應研究並不能作為禱告效力的最後結論。不過它確實引發了一個疑問,那就是應不應該讓病人知道有人為他們禱告;這個疑問應該是未來禱告實驗最重要的研究課題。然而,其他人卻懷疑禱告實驗應不應該繼續下去,或能不能繼續下去。要知道,約翰.坦伯頓基金會(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曾提供本森二百四十萬美元實驗經費,但卻得到這樣的負面結果,很可能沒有人願意再資助同類研究。
代禱治療效應研究的結果看來足以動搖我的大型念力實驗計畫。然而,經過細細琢磨,我懷疑之所以有如此結果,說不定是實驗設計不良所導致。雖然該實驗力求嚴謹,卻在許多方面違反最基本的科學規範。
例如,上述所有實驗並沒有清楚規定禱告的內容,任由禱告者自行發揮。本森雖然要求禱告者說出「手術成功,復原迅速,無併發症」,但其他部分仍然一無規定。最成功的念力實驗都把意念規定得高度明確。例如,在塔格的實驗中,治療師接到的不是模模糊糊或泛泛的指示,而是被要求致力於增加愛滋病患的T細胞數目。因此,本森其實應該指示禱告團體,針對某些特定的心臟病症進行代禱,或者在研究期間減少心臟支架的置入,或是其他高度明確的要求,而非含糊請求改善病情的泛泛之言。
上述兩個失敗的實驗也無一嚴格控制禱告團體的人數,或控制禱告的頻率和時間長度。這一點也許會引起群體念力的混淆。由於實驗使用的是高度分歧的禱告團體,這些團隊的禱告效力並非等值。在本森的實驗裡,禱告團體被要求一星期禱告四次,但時間長短則容許從一次三十秒到幾小時不等。他的助手也從未記錄每個禱告者禱告時間是多長。反觀塔格雖然也使用背景大異其趣的治療師,但他們輪流交換病人醫治,所以每一個病人每一次只會接收到一種治療訊息。
就像「禱告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Prayer Research)的主任鮑伯.巴思(Bob Barth)所說的:「你要怎樣量度禱告的劑量呢?例如,一個和尚五分鐘的禱告就一定不如十個修女禱告一小時有效嗎?一天禱告二十次一定比一次更有效嗎?」
在評論克魯科夫的實驗設計時,《柳葉刀》期刊亦語帶保留:「不同宗派的禱告者少一點,會不會導致不同結果呢?」
本森企圖標準化禱告方法的做法也有違各個禱告團體慣用的代禱方法。在一般情況下,禱告團體被要求為某個人代禱時,需要知道病人較詳細的資料,包括全名、年齡、病狀等,也會想定期了解病情進展。他們還常常要求與病人和家屬見面。有了這種個人資訊,他們才能真正知道病人的需要。
本森的實驗設計卻反其道而行,只讓禱告者知道病人的名字和姓氏首字母。有限的資訊讓禱告團體無法與病人發生有意義的連結(施利茨和雷丁相信這種連結是心靈能發生影響力的重要條件)。許多參與實驗的禱告團體反對本森這種設計。正如一個評論者所說的:「情況就好比你想打電話給朋友,卻只有她電話號碼的前三碼,這樣你又怎能指望她會接電話?」
就像代禱治療效應研究實驗一樣,克魯科夫的實驗也不披露任何病人的細節,讓代禱者無法與病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而在塔格的實驗裡,治療師卻能得到病人的照片、名字和病情資料。上述的禱告實驗並沒有測試根據詳細資料進行的代禱與只根據名字與姓氏首字母進行的代禱效力有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