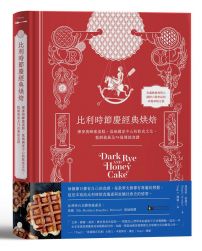一探低地國家迷人的飲食遺產與社會歷史──歷史學家安妮.葛雷博士(Dr Annie Gray)
本書精美無比。書中充滿了我想做的食譜、想吃的食物,以及想連續幾個小時沉浸其中的照片。這也是一本引人入勝的讀物、一封寫給低地國家飲食遺產與富饒社會歷史的情書,有時還能讓你近距離地了解瑞胡菈在過去幾年中的個人旅程。
作為英國歷史學家,我對比利時和低地國家的歷史究竟了解多少呢?其實僅限零碎、片段。我在學校裡學過17、18世紀的戰爭,且非常了解沃邦防禦要塞(Vauban’s barrier fortresses)這個極為特定的主題;在大學讀過歐洲政治史,對現在法國北部、比利時和尼德蘭所包含的地區是如何被撕裂,且無視當地居民的願望與身分認同、分給不同國家的歷史有些膚淺的了解。我愛上了現代早期那些了不起的藝術品(主要來自佛拉蒙藝術家),它們在風格和主題上如此獨特,對食物歷史學家非常有助益。本書中的許多畫作對我來說就像老朋友一般,從布魯赫爾(Bruegel)到佩特斯(Peeters)」,從字母杏仁糕點到香料蛋糕。
這本書帶來的樂趣在於,我現在了解了更多。瑞胡菈的作品一如既往地情感豐沛,讓我大開眼界,了解低地國家語言與政治是如何這麼緊密交織,以及此現象怎麼直接融入其烘焙傳統。她豐富了我的日常烘焙知識,還解釋了我在那些曾經自認非常了解的畫作中,所看到的那些令人垂涎三尺卻早已失傳的塔派及餅乾究竟是什麼。
接著是攝影,瑞胡菈作品的狂熱讀者們絕對期待著將非常美麗的照片。她總是有種經典的大師風格,書中照片宛如栩栩如生的林布蘭作品。我們和她一起走過烘焙的歷史、穿越她祖國的城鎮與村莊。她對比利時烘焙的熱愛逐漸增長、反映在整本書中,每個詞彙、每份食譜和每張圖片,都像說故事般在讀者面前展開。
讀了瑞胡菈的介紹,我對過去幾年中我們究竟失去了多少感到震驚,但也同樣驚訝,失去的或許將會重新變為收獲。在英國脫歐與新冠疫情之間,英國和其歐洲大陸鄰國間輕鬆、開放的關係被重塑。那些像我和瑞胡菈一樣,曾因將自己的一小部分和不同國家結合,因此幸福地生活著的人們,不得不轉向內心,探究究竟是什麼讓我們成為了現在的自己。因此,雖然本書是部歷史書、食譜書及擁有優美照片的作品,它也是希望的宣言。瑞胡菈稍微放棄了一些對英格蘭的熱愛,卻為比利時帶來了強烈的光芒。若當前的動蕩,將會帶來一些和本書一般璀璨的事物,未來的確可能是光明的。
作者序──「對整個世界保持仁慈與善良」
這句話是一本被稱作「布拉邦食譜書」(Brabants kookboek)的17世紀烹飪手稿的開場白。這部手稿收藏在安特衛普的亨德里克.康希安斯遺產圖書館(Hendrik Conscience Heritage Library),為了寫作本書,我在這裡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對一本食譜書來說,這段話並不尋常,它們更像是老祖母分享的智慧之語。但事實或許正是如此。手寫烹飪筆記通常是傳家寶:經常由一人開始,並由後代傳承。
發現這份手稿非常令人難忘,因為它年代久遠,且幾乎全用荷語寫成。它來自我的出生地,也帶來一份親切感。閱讀脆弱的書頁、辨認字跡,讓我不禁揣想那些曾經擁有這部手稿的女士們。有時我會想像她們是我的祖先,藉以填補自己家族歷史中的空缺,因為我並未擁有家族代代相傳的食譜。我出生在一個將食物用來烹煮和食用,而非發現、品味和記錄的家庭。
我經常好奇,如果我的母親是一位熱中烹飪的廚師或烘焙師傅會如何?當我第一次對食物產生興趣時,會有食譜書可供實驗與參照嗎?又或許,因為烹飪近在身旁、不會錯過,也沒什麼好好奇的,我可能會將它視為稀鬆平常?或許所有曾經發生過及從未發生的──那些我從未擁有的書籍、香料、蛋糕模具、指導──都是本該如此,只有這樣,我才可能成為今日的自己。
相較之下,我所有的童年記憶都或多或少和我們家族旅行中遇到的食物有關。我以前認為飲食狂歡屬於出國度假的範疇,父母送給我最大的禮物是帶我遊遍匈牙利、捷克、瑞士、奧地利,後來還去了英格蘭、威爾斯與蘇格蘭。在比利時家中,食物很乏味,蔬菜以80年代的風格煮至爛熟,無論是味道還是質地都消失無蹤;沒有胡椒、沒有鹽,只有罐子裡的百里香。那罐百里香大概在20年後的今天都還沒用光。
食物從來不加修飾,它是為了維持生存而存在,而非讓人開心。這是清教徒的風格,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嬰幼兒食物」。
因此,在暑假旅行中穿越國境,就像世界從黑白轉為彩色,在味道與香氣上都令人大開眼界。
我的前幾本書,出自自己童年時對英國及其歷史和飲食文化的迷戀,隨後變成終生的熱情。對一切英國事物的迷戀,都讓我能藉此逃離比利時,不光是因為那些我聯想到的、缺乏想像力的食物,也是因為審視自己家鄉時,同樣會看到它的缺點。
在比利時,你永遠不可能逃避法蘭德斯(Flanders)與瓦隆尼亞(Wallonia)間的對抗,以及我們的語言鴻溝。這些問題在過去引起了不少動蕩不安,如今也同樣如此。以前我不懂比利時複雜的歷史與政治,本地也只有極少數人真正明白。我逃入珍.奧斯汀(Jane Austen)與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世界,以它們大量餵養我的英倫情結,不受政治與社會問題影響,這些問題可能會污染我對那完美的英國小世界的看法。如果要擁抱自己的國家,我需要變成一個外來者向內窺探,就像我曾經一直以外地人的角度看待英國食物與文化一樣,沒有被現實所破壞。
我在2016年取得比利時啤酒侍酒師資格後出版的《比利時咖啡館文化》(Belgian Café Culture)一書,為我的返鄉之路打下基礎。在一箱艾倫.戴維森(Alan Davidson)的藏書中,我發現了一本18世紀的荷語食譜書。它吸引了我的目光,從那之後,我便開始蒐集與閱讀擁有數百年歷史的荷語食譜書,就像在過去十年中蒐集英語食譜書一般。
過去我將自己的心牢牢上鎖,遠離家鄉,但這些我讀過的食譜書和手抄本,每一本都帶走了心房的一小塊。身為一名作家,你需要絕對熱愛自己所寫的主題與人物,它們得接管你的生活、夢想、清醒時的每一個想法。為了寫出這本書,並使它成為最好的樣貌,不僅得投入其中,更需為此癡迷。
我在生活中為飲食史與自己家鄉的歷史留下一席之地,讓它有充分的時間成長。它就像一粒種子,我一直把它藏在盒子裡,但始終不願種下。現在既然我已經將其種入土中,便希望讓它慢慢生長,養成深入且強健的根。如此一來,從種籽中開出的花朵,就會長出長長的、能夠抵禦強風的莖。本書就是那朵花,而它的莖則是我為了找到回家的路所耗費的那些歲月,也是那些我在2016年被出版商初次拒絕這本書後所做的那些研究。當時我的出版商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但在2020年,她說了「Yes」。
在能開始動筆寫這本書之前,我必須先了解比利時的疆界是怎麼形成的,在過去800年間又經歷了哪些變化。因為當回顧此地的歷史時,不可能只單著眼在比利時──一個在1830年憑藉地緣政治智慧才成立的國家。
研究本地歷史更好的方法,是著眼於「低地國家」(the Low Countries)。因為在政治與飲食習慣方面,低地國家的人們共享這段歷史、這些故事與許多傳統。
若要寫一篇低地國家的飲食概論,我可能會需要四倍的頁數,因此本書聚焦在低地國中心(即我的出生地)與其對廣泛低地國區域的影響,這些區域也反過來形塑了比利時。
烘焙真正體現了飲食文化的核心:城鎮自豪地烘焙當地甜派(vlaai)、香料蛋糕(peperkoek)與地區節慶人形麵包(gebildbrot)。烘焙傳統是歷經艱辛才得以留存,並且找到方法不和現代脫節的傳統。
無論是狂歡節,還是聖尼古拉斯節或聖馬丁節、聖誕節或除夕夜,低地國家的人們都會升起火來加熱他們的烤爐、華夫餅烤盤與煎鍋,製作最愛的節慶點心。
◆每個節日都有自己的食譜
第一本以荷蘭語印刷的食譜書《烹飪名著》(Een notabel boecxken van cokeryen)是在印刷術開展的早期,約1510年時於布魯塞爾出版。整本書皆是獻給婚禮、宴席與其他慶典的食譜。
這也是為何本書會大致圍繞著宴席與節慶安排,從包含華夫餅與冬季麵包的12日聖誕佳節開始,到聖燭節與狂歡節的煎餅、大齋期的扭結餅、園遊會的甜派與油炸點心,再到聖尼古拉斯節與聖馬丁節的甜點──全年的節慶烘焙。
◆食物在法蘭德斯與尼德蘭藝術中的重要性
我不但在自己的研究中檢視了六個世紀的烹飪文獻,也開始研究藝術。16及17世紀的法蘭德斯與尼德蘭藝術將食物放在中心地位,承載各種寓意,向過去開了一扇窗。在老彼得.布魯赫爾的帶領之下,我們見證了〈狂歡節與大齋期之戰〉(The Battle between Carnival and Lent)中慶祝活動的鮮明對比之處。
狂歡節是一段自我放縱期,落在復活節前40天的禁慾期(即大齋期[Lent])開始前一週,以一個在荷語中稱為「齋戒夜」(Vastenavond)的一天告終。這一天在德語中同樣名為「齋戒夜」(Fastnacht),在法語中則是「油膩星期二」(Mardi Gras),英語裡則為「懺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
在左頁的畫作中,從左方進入畫面的遊行隊伍,以狂歡節的化身人物打頭陣:一位頭頂著派餅的男人騎著酒桶,酒桶前方還用刀掛著火腿。這位老兄顯然剛剛享用過豐盛的晚餐,正揮舞著一支串著豬頭、一大一小的家禽以及香腸的烤肉叉。在他身後走著的,則是一些手持蠟燭、炊具和樂器的人物,他們之中有人戴著面具、有人沒有。一位修女扛著一個裝著煎餅、白麵包與華夫餅的盤子在頭頂上,隊伍後方則有一位戴面具的人物手持一盤華夫餅,還有一位孩童在手臂下夾著一個佛拉麵包,另一手則拿著別款蛋糕。越是仔細地觀賞這幅畫,它就顯得越不尋常。畫作前景處有兩位男士在一片華夫餅前擲骰子,其中一位男士頭上佩戴著三片華夫餅。緊接著,在狂歡節遊行隊伍後方,有一位正在明火上用大型黑鐵模烤華夫餅的女人,旁邊放著一桶麵糊。
與之相對,大齋期的代表則是一位瘦弱的角色──可能是位女子──坐在推車上的椅中,頭上戴著象徵神性的蜂箱,手拿一束意在約束、教誨的細樹枝。在這鬥爭場景裡,她的矛是一個掛著兩條鯡魚的大型麵包鏟;她身後則是一盆貽貝、未發酵的麵包與和扭結麵包(與大齋期有關)。主角後方的人們拿著掛在長棍上的扁麵包:其中一位頭上頂著裝有一條鯡魚的盤子,另一位則身背一袋未發酵麵包,在他前方有位女士提著一個裝著麵包與扭結麵包的籃子。與狂歡節的隊伍被蛋殼、肉骨頭和幾張樸克牌包圍相較,這個隊伍旁僅有一些散落的貽貝殼。
布魯赫爾描繪的,從來不僅是一扇展現常民或宗教生活的窗口。儘管我們如今幾乎都是在博物館中欣賞布魯赫爾的作品,但在當時,它並非單純的裝飾,當畫作掛在家中顯眼的位置時,還是宴客時開啟對話的話題。就飲食而言,他的畫可能曾經提醒人們「何謂傳統」:華夫餅和煎餅屬於狂歡節;大齋期要吃鯡魚和扭結麵包。在他關於諺語的畫作中,低地國甜派是豐饒的象徵;在描繪農民婚禮的畫作裡,有著金色米布丁⋯⋯這有點像是在社群媒體上看到別人的聖誕節蛋糕,提醒自己也該來做一個。
為了紀念這位藝術家,在比利時有著醃肉、香腸、水果、低地國甜派與米布丁的傳統宴席,到現在都還被稱為「布魯赫爾的餐桌」。
布魯赫爾曾在我的家鄉安特衛普生活、工作(雖然他也曾於其他地方生活及工作過),很可能也是在此地出生。安特衛普不僅在布魯赫爾的生命及畫作中具有重大意義,在文化與經濟層面上也非常重要:她從14世紀中開始,便是低地國家的應許之地;我們如今依然珍視的許多烘焙傳統,正從此時開始發展。布魯赫爾周圍圍繞著16世紀安特衛普的偉大思想家與創新者,例如人文主義地圖繪師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極具影響力的印刷商克里斯多費爾.普朗坦(Christoffel Plantijn),以及藝術收藏家尼可萊斯.永格林克(Nicolaes Jonghelinck)等。奧特柳斯曾在他1570年出版、令人歎為觀止的世界地圖集中,稱安特衛普不僅是這片土地的首都,也是歐洲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