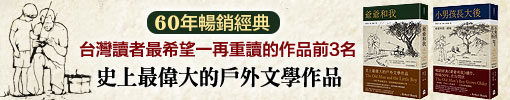三、公園生活──現代生活的櫥窗,潛藏殖民的騷動與哀愁
通常六點起床、七點到校的新竹公學校訓導主任黃旺成,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五日這天,四點多就早早起來梳洗,匆匆趕赴新竹驛,在四年級以上一百七十名學生慢慢集合完畢後,搭乘六點二十分準時開動的火車北上,展開兩天一夜的修學旅行。
修學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參觀總督府舉辦的始政二十週年勸業共進會。不過比起這冠冕堂皇的名義,對一百多名小學生來說,大概出去玩才是真的,尤其是去台北玩。到台北去哪裡玩呢?說來有趣,整趟修學旅行,除了勸業共進會之外,只安排了兩個行程:圓山公園和台北新公園。
可別小看公園。不只這間新竹公學校,日治時期幾乎所有的修學旅行、私人參訪,不論台灣人、內地人甚至從更遠的海外前來,只要到台北觀光,圓山公園和台北新公園,都是觀光客絕對不可錯過的景點,就好像今天的台北一〇一。
我們可能很難想像,不過是林蔭花草的廣大空地,究竟有何迷人之處?其實在一百年前,公園的內涵遠比現代豐富,公園,可以休閒娛樂,卻不只可以休閒娛樂。
圓山公園、動物園,百年前全台出遊最熱門景點
一八九六年,在台北廳知事橋口文藏提議下,基隆河濱的大日本帝國陸軍墓地,被改闢成台灣第一座公園,也就是「圓山公園」。儘管以公園為名,但初期只有權貴官員能享用,並不容許巿民大眾公開進出。
日本政府眼裡的圓山公園,可不單純是依山傍河的納涼地。圓山公園,還是近可仰望神道信仰的神聖空間。如果以公園旁黑瓦飛簷的臨濟護國禪寺為起點,穿過明治橋,沿著劍潭山麓一級一級石階朝上,來到終點的台灣神社,正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位階最高的神社。
一八九七年底,圓山公園終於開放巿民使用。沿著河散步,觀賞迎風爭放的紅白蓮花,或是坐在樹下乘蔭,成為台北人的一件樂事。愈來愈悠哉的公園地帶,因而又吸引到了更休閒的設備。
一九一三年底,日本人片山竹五郎率領馬戲團「大竹娘曲馬團」到台灣表演,途經圓山美景,決定買下坡地,開設了一座私人動物園。一九一四年,片山竹五郎的動物園開始營業,有義大利的孔雀、印度的火食鳥、澳洲的袋鼠等珍奇動物數十隻。隔年,經營得有聲有色的動物園,被台北廳收購,並且擴大規模,於一九一五年改制為公立「圓山動物園」,開放距今剛好一百年。
除了外來動物,園內還保育許多本土特有種,包括台灣獼猴、雲豹、梅花鹿等等。當時最受歡迎的是紅毛猩猩「一郎」,一郎以擅長模仿人類表情著稱,印有其照片的繪葉書是最搶手的紀念品,名氣之大,甚至讓遠在大阪的天王寺動物園,封其為「東洋第一」。
不像現在多只能隔著柵欄,日治時期的圓山動物園,繼承馬戲團的傳統,常舉辦動物表演。這些表演活動,簡單的有猴子騎單車,另外也會有「慰靈祭」,這是為悼念告別世間的動物朋友所做的法事,主祭官是身披紅色禮袍的大象,由口誦經文的小朋友包圍,面朝祭壇跪拜燒香,過程肅穆莊嚴。還有命名投票、寫生跟攝影比賽、以各種動物為主題的博覽會。
一百年前,再沒有比圓山公園、動物園更適合修學旅行或全家出遊的地方了!
現代的力量像鐵鎚敲毀故城,用殘磚剩瓦堆砌新公園
如果圓山公園具有神聖空間的意義,台北新公園就是世俗的中心。
第一次擁有殖民地的日本,為了追上西歐文明的步履,對於島都台北的現代化可是不遺餘力。早在一八九九年的市區改正計畫,就已經提出都巿公園的概念,但直到一九〇八年才落成,名為「台北公園」。因為和圓山「舊」公園相對映,而俗稱「新公園」。
座落在城內正中央的新公園,緊鄰台北驛、總督府、台北法院、以及大片的日人官舍,很明顯的是將日本內地移民優先設定為公園使用者。
不過,公園就是可以自由進出的空間,台灣人可不在意附近政府機關瀰漫的森嚴氣息,非常樂於來此享受現代化的新體驗,包括讓人強健身體的運動場、每個禮拜會在報紙公告表演曲目的音樂堂、圓頂垂拱的台灣博物館。星期六、日散步累了,還能去大大小小的露店、喫茶店,買杯咖啡,找張長椅子坐著,聽噴水池的聲音潤透此景此刻,有時還能巧遇播電影呢!
但是,並不是所有台灣人來公園都是為了放鬆享樂。一百年前,心懷彼岸中國的傳統漢文人來到公園,只會覺得悲傷沉重、不知今夕何夕。
這時的台北,正是市區改正的高峰期。新建設什麼,就意味著有什麼要被破壞。舊城牆、老官署,都被一磚一瓦拆解,然後進入時空錯置之旅,與歐洲化、日本風的公園堆放並列。
原來豎立在西門邊的急公好義坊、東門邊的黃氏節孝坊、台北府衙前的石獅子,都一起送作堆進駐新公園。原本座落城內中央的天后宮、千百戶家屋小店,更是難逃拆除命運,剩下散落的柱珠變成遊客的短凳。取而代之的是高高聳立的雪白將軍像。他,正是推動市區改正、下命拆毀天后宮的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新文學小說家朱點人的〈秋信〉,塑造出主角斗文先生,演活了傳統漢文人不願面對新時代的心情。隱居鄉間數十年的斗文先生義憤到台北一看的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會址就在博物館所在地的新公園。這位先生一下火車,久逢故人的期待瞬間化為痛楚:
昔日的台北城址,已築了博覽會場,他的胸坎像著了一下鐵鎚,無力的落到椅上去……台北驛前的路上,人波浩浩蕩蕩的向著博物館推著,斗文先生像失了舵的孤舟,正不知道划到哪裡去好。台北的地理,早奪去他昔日的記憶……
景好移,情難轉,現代的力量像鐵鎚一下一下將故城敲毀,將舊文人愈敲愈扁,最後像隻掃帚將他們全掃進社會的邊緣,眼不見為淨。
新式教育出身的朱點人,寫出了斗文先生的悲壯,殖民政府以現代之名大行推動新市容,卻把台灣人留在看不見的邊緣。圓山公園和日本神道信仰緊密結合、新公園為了城中官舍而開,一旦遠離日本人的視線,公園似乎就不必了。
公園既是都市櫥窗,也潛藏無邊情欲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密集區大稻埕,在新公園開張二十年後,當地仕紳仍一直在報紙發表言論,努力請願要求設置公園。一九二七年台灣民報刊出〈台北公園的創設,望議員再努力〉,批評偌大的台北市區竟然只有一座新公園。一九三〇年,再刊登一篇投書〈台北市三大問題:第一街道、第二公園、第三市場〉,大稻埕的台灣人仍然只能繼續望穿秋水。
生活在遍地公園的現代都市,大概很難理解那種焦急和渴望。當時的人為什麼如此想要公園?因為曠大靜好的公園提供了散步的地方,自然的花草、清新的空氣可以調養身心。但潛藏在社論底下沒有明說的,是公園對於談情說愛之必要。
在什麼都講究現代化的日治時期,愛情也要現代化。「自由戀愛」成了摩登術語,當時沒有網路,電話仍不普遍,談戀愛必須約會見面,然而並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談戀愛。同樣是請願設置公園的社論〈台北橋附近不良少年出沒〉,迂迴表現了這種到公園談戀愛的情結。
大稻埕因為沒有公園,故每年一到暑期,沒有去處可納涼的公園,皆藉台北橋為避暑地,不料因為黑貓跟黑狗的猖獗,時常在該橋上演出醜態。致惹旁觀者諷刺或受不良少年毆打。而諸不良少年,良莠不分一律認作黑狗黑貓,致遭侮辱者很多。
一九二一年落成的台北橋,連通大稻埕和三重埔,美麗的彎拱橫跨淡水河面,每逢日暮,憑欄俯瞰橘色的連紋水光,兩岸風情盡收眼底,還曾被選入台北八景「鐵橋夕照」。原該是適合調情的浪漫地,但這篇社論卻說,對不起,情欲旺盛的摩登男女「黑狗黑貓」想卿卿我我,請不要連累路人,只有公園歡迎你們。
公園對戀愛有多重要呢?謝春木小說〈她要往哪裡去〉也點名河邊清涼的圓山公園,是最受歡迎的約會景點,林煇焜小說〈命運難違〉,自京都大學歸來的李金池,滿懷自由戀愛的夢想,與父親一番爭執、斡旋過後,第一次約會就選在台北新公園。
新公園的樹蔭下傳出一對男女的談話聲。男的是戴著學生帽的金池,女的是撐著陽傘的秀慧。兩人很有默契似的,腳步自然而然地朝水池邊的長凳走去。
這情境儼然跨越時空、無分現在過去。不僅談戀愛的地方隱隱有所規定,什麼人可以談戀愛,也是有所限制。
芳久的〈同性愛〉描述了日治時期同志情慾的深潛低伏,情節是一名警察巡邏完坐在公園長椅休息。
「你一個人嗎?」有個男子靜靜移來身邊探問。
「一個人啊,在這樣的夜裡,一個人還真是寂寞啊。」這名警察直覺地回答。
「你聽過同性愛嗎?」男子試探地提起這個話題,然後一邊慢慢將手探入警察大腿內側。警察的胸口漸漸熱起,心臟怦怦跳動,男子索性坐上警察大腿……。結果警察立時以現行犯的名義逮捕了這個男子。最讓人無限遐想的是,由警局返家的警察一個人在路上的自言自語。
「其實那男子長得也蠻可愛的,」警察這樣偷偷地想。
偷偷地想,警察只能偷偷地想,那時的人都只能偷偷地想。如果他不是警察,如果那不是個否定同性愛的社會,他們說不定早譜好一見鍾情。一百年前,社會價值觀不准的,就到公園裡闖關。
圓公園,台北第一個通宵營業、最重量級的庶民美食區
大稻埕其實並不是沒有公園,只是並非當地仕紳渴望的新公園。
新公園問世的一九〇八年,台北也仿效巴黎凱旋門的輻射狀道路,在建成町、日新町交界設立了一座圓環,並在圓環中央的空地簡單舖設草皮、長椅,稱為「圓公園」。
儘管不比政府刻意經營的圓山公園和新公園,但由於靠近永樂市場座落的永樂町、料亭酒樓密集的太平町,因此入夜以後,圓公園附近就有小販占地做起生意。不管警察如何取締,攤商始終有增無減,還經常可見在文萌樓雲雨完事的人客,或是永樂座散場出來的觀眾,水流往低處一般匯聚。
具有六條放射線馬路的街中心,中央設有升旗台,其周圍用榕樹圍繞的圓環夜市場,在榕樹下鱗比櫛次排列的攤子光亮的燈光照得如同白晝。直到十二點為止,時常擠滿了人,有粗野風貌的工人、店員和車伕等人在那光輝之下滿足旺盛的食慾,是一種壯觀的場面。
這段文字出自日本作家濱田隼雄的小說〈蝙翅〉,將圓公園獨特的粗獷肉欲、夜夜笙歌,描述得活靈活現。相較於內地人官舍街道十點過後就寂靜無聲,本島人來來去去的圓公園,熱鬧的秋燈一盞一盞越夜越亮,正是台北第一個通宵營業、最重量級的庶民美食區。
〈蝙翅〉題名來自小說中陳姓少年的攤子,其實就是扁食、餛飩。陳少年的知交、日本教師速河,雖然很愛這一味,但可不只為蝙翅著迷。圓公園裡還有澆著魚翅、香菇混合醬汁的台灣麵,撒上小把香芹,熱氣自然蒸騰成食慾。旁邊有蝦湯放進半熟的鴨蛋包,湯匙尖輕輕戳散,瞬間就色香味迷漫。不想喝湯的可以來份炸雞捲,切成一片一片油亮盛在盤子裡,筷子絕對動不停。盤子空了沒關係,隔壁就是蚵仔麵線、米粉湯,台灣風味小食,圓環夜市什麼都有。
是啊,台灣風味,庶民生活,這是個逾越文明想像的公園。
所以速河的學生才會在週記向老師抱怨「老師去圓公園是下流的行為」,速河的日本同儕也會批評說,「骯髒呢」。
大稻埕仕紳斥責大稻埕沒有公園,是因為他們在朝思暮想一座有喫茶店、音樂台的新公園,可以在樹蔭下閒坐,只會聽見情愛軟語,而不是攤販的聲嘶力竭,不是擠如刺蝟貼身的摩肩接踵。傭工、車伕、娼婦流動嘈雜的油膩所在,不能叫公園。
日本人會歧視台灣人,台灣人一樣會歧視台灣人,夜夜通明的圓公園,終究照不穿更大的都市暗影。
公園既是開放空間,壓抑不住庶民蓬勃的生命力
無心經營的圓公園,有警察壓抑不了的蓬勃生命力。即使是充滿神聖政治性的圓山公園,庶民其實也可以挪用來抗議。
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清早,兩百餘名身穿白色法袍、面色莊嚴的男子,在艋舺新起街的真言宗佈教所前集合,一路徒步朝北前進,在風光明媚的圓山公園停止隊伍,霸占下來。這是一起罷工行動,他們是「台北大工組合」,全台灣第一個工會組織,日本工人聯合台灣工人,為了抗議木工的薪資低落而成立,並組織遊行。
他們讓圓山公園成為民意發聲抗議的基地,昭告全台北的工人團結起來,預示了台灣社會運動就要從占領做起。
一九三一年六月,新文學小說家孤峰一樣在台灣新民報發表〈流氓〉。似乎承繼了占領圓山公園的狂野,也像是反擊大稻埕仕紳寫社論要求公園的拘謹,孤峰描述了一座繁雜草木的廣大公園,正午汽笛響起,暫時在公園休息的學生、工人紛紛成群結隊準備離開。一群衣衫襤褸、披頭散髮的赤腳流氓,仍圍坐在松樹下的長椅不動。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拋棄的人、工廠大量解雇的無業者。除了公園,他們無處可去。
D印刷工廠的職工阿B,他每由工廠回來的時候,必跑入公園逛一圈兒,欣賞大自然的光景,以安慰勞頓的精神,所以每日都目擊著這不自然的現象,他還記得前些時候,在公園的清水池畔,在葡萄架下,在花徑上,時常遇到幾對富戶家的公子小姐們比間徘徊於其間……而今既是變成流氓的棲留所了。
公園像是幾個平行世界的交會,是富人家郊遊、戀愛、穿洋裝、抹髮油、噴香水的伸展台,是勞動者調劑身心、復原工作壓力的緩衝區,也是想要勞動賺錢卻不被允准的流氓無家可歸的最後去處。
小說背景正是圓山公園。暗暗指涉同年二月,台灣平版株式會社為了節省成本而實施縮短工時、實則降低工資引發的抗爭。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王萬得帶領五十餘位工人罷工,甚至佔領了印刷工廠,成為日治時期空前絕後唯一的點交抗爭。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就在小說〈可憐她死了〉,清楚描述這次鎮壓罷工運動的種種不人道。後來,罷工者遭到逮捕、虐待、流離四散,抗爭全面頹敗,在賴和筆下一清二楚呈現出來。
有別於賴和〈可憐她死了〉結局的悲憤無力,孤峰可能為了鼓舞士氣吧,他的〈流氓〉充滿了戰鬥意志。故事裡,主角阿B不敵各地工廠大量解雇的風暴,與同運命的勞動者一起坐在公園,聽著眾人批判物價高漲、工資低落的社會寫實景況,茫然看著人群越聚越多,然後眾情激憤高呼「打倒資本家、打倒資本家」,儼然革命前夕。
敗陣的革命青年,美麗的公園潛藏不住哀愁與憤恨
儼然革命前夕,其實是夢醒時分。
台灣自治運動旗手林獻堂到英國海德公園觀光,見到民眾正在肥皂箱上講演,針對政治、經濟各種議題辯論,不管發表什麼意見,警察都只是遠遠看著民眾鼓掌喝采,林獻堂大嘆,這才是真正的公園。
轉眼一九三〇年的台灣,各種遊行抗議都被禁止,幾個工友總聯盟的幹部,為了紀念五一勞動節,選擇在圓山公園散步集會,就被懷疑是要發起什麼活動,引來警方恐慌,大舉包圍,不由分說,一一逮捕。
〈流氓〉發表的同時,台灣共產黨遭到大檢肅,其他社會運動組織也都陷入無力再戰的困境。曾經親身反抗的王詩琅出獄了,對於這個理想可能永不再實現的島都,內心僅存的支柱就是寫作。小說〈沒落〉寫一名從左翼運動敗下陣的理想青年耀源,他走出古色蒼然的法院,站在總督府前面,沒臉再見昔日戰友,更發現過去、現在都已經沒有自己的容身之所。
明治製菓喫茶店的樓上,近大道的窗前佔了座位的他,剛注文了後,突然遠遠地雜在都都地叫的嘈雜裡,嚠喨的軍艦進行曲接近來。假裝軍艦進行曲的自行車,約莫有幾十隻自公園方面驀進來。他假裝沒有關心的樣子,拿起剛才送來的曹達水吸。剛才法庭的場景,又像影片般隱現在腦裡,自己的世界已和那些差得太遠。
場景是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全面被壓制,公共場所已不再能自由議論或行動了。公園,只能是騎自行車的地方,沒有講演會、更遑論罷工。敗陣的左翼青年啊,那就坐進喫茶店來杯飲料吧,讓女給陪著說笑,如果天色暗下,可以再斟一杯酒,或學一支舞、看一場電影,想多華麗都可以,想多頹廢都可以。
終於,一九四五年夏末,新公園中央的放送亭,傳來天皇玉音,終戰宣言。
聽著聽著好像每個人眼睛都紅了,有的喜極而泣,因為不用再拚死拚活演一個皇民,有的太過悲傷,不知道自己現在及將來會是什麼人。無論如何,他們都以為最起碼不用繼續在生死線前過日子了。
結果竟還是另一條生死線。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群眾衝入新公園,放送亭再度傳來聲音,台灣人的聲音,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不可信、新政府更不可信。
二二八事件後全島動盪,青年學子組成忠義服務隊維護台北治安,其中一小隊途經明治橋,被國軍攔下,無端遭到開火射擊,血花噴濺地從橋面翻倒墜落,把夕陽西下的紅色漣漪拖得更長。還有其他幾百名學生,被憲警拘捕,在圓山公園前的陸軍倉庫廣場罰成一列,英挺的制服,俊爽的平頭,迎著機槍和坦克彈,最後全都沉進基隆河底。
悲哀的不是夢終要醒,是驚醒以後就再不可能好眠。在日本帝國主義下度過五十年,換來一個二二八,繼續再五十年威權統治,新公園換成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名字改了,然後呢?然後呢?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