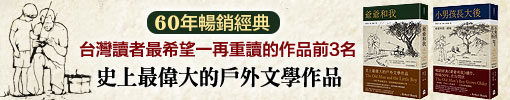這時候是6月21日凌晨2點,離拂曉還有一段時間,可以算是6月20日夜的延伸,看完了產科,吃了兩個粽子,喝了一杯冷開水。一大堆歷史的點點滴滴在腦內去來明滅,太疲睏了,伸了個懶腰,一時心理上累積的倦意及鬆弛。忽然看到兩位校警站在我窗前的草地上,而樓梯上正有3個人,陌生皮靴的腳步聲正要上來,要逃來不及,反而難看。雖然經1年半的生活,我大致可以分辨這新東館60多位的腳步聲,甚至以前本館、西館的老舍生也可以知道,很少人會穿皮靴,一切都太遲了。知道無望逃此劫數時,反而出奇地的沉靜,拿了毛巾把嘴一擦,坐下來,等著陌生客人來敲門的聲音。
這數十年,閱人已多了,無論在什麼觀點,由任何角度,自己不是出眾的角色。論過目不忘不如先父,論話術一向是我的命門,不愛說話,很少說,而且說話的要領奇差。論交友,小學、中學只有不滿五指之數。中學尤其只會向圖書室每日返3本書再借3本書,書就是當時的朋友。去淡水,台灣人只有那麼幾個,患難之交,大家都熟了。在宿舍,除了「雜談俱樂部」,不會主動去找人家閒聊,相遇點頭,一聲問候,不論是七年制的、一年級或高一班的五年級,真是一視同仁。
自從看了兩位校警在下面,就知道形勢已經是不能改變的了。醫學院這邊校警是4位,晚上只有一位輪值,兩位出現在窗前已意味著是非常事了,大家很熟,其中一位也姓顏,女兒小學畢業,聰明,但家窮不能上學,由我介紹到宿舍當13歲的小工友,負責宿舍的小吃部及小福利社的工作。他們的眼神,在遠遠的夜色中,仍可以感覺到意外及無奈。一切都遲了,我聽他們的腳步聲在門前停下來,而後敲門了,知道我在這裡,一定問了宿舍的人,因為校警應該不知舍生的住房。骰子總算拋下來了。
「請進」,還好我的聲音如常。而後3位客人進來了,我只認得校長傅斯年先生的秘書那廉君先生。這件事還得在此深夜讓校長操心,又讓那先生跑此一趟,心內實在過意不去,這意念是一閃而過。
先進來的一位約170公分以上,中等體材,約莫30歲,先開口問;那先生不認得我,不過可能看過檔案。
「有一位顏世鴻嗎?」
「我就是。」
「這麼晚還看書嘛。」
「嗯,考試快到了。」
「你的身份證借看一下。」我就由掛在身後牆上的襯衫胸袋把裝身份證和註冊證的夾子交給他。這兩張自此永遠離開我了。
「有沒有來往的書信?」我蹲去由床下木箱拿出已經紮好的一束信交給他,而後他又來了一句。
「有些話要問一下,請跟我們走。」
「要不要帶東西?」這句話有點試探的意思,不用帶可能是好與極壞雙面的消息。而他真的說:「不要帶。」
我早已經準備好台詞:
「你要帶我走,那就請你明示你的身份,不然你就寫下書狀。這麼說,對那先生是不好意思。」
那一位就默默地在我遞給他的那32開白報紙寫下「提訊狀」,然後簽了名字、日月。我拿円型大理石的文鎮,壓在桌上。
「那就讓我穿衣吧。」
把衣褲,和籃球靴穿上,將褲袋的40元拿出來,又壓到那紙上。我早知同房的老吳已經醒了,本無意思勞駕他,不過這兩樣東西要交到大妹手裡。
「老吳勞駕,明早把這40元交給大妹。」是用日語說的,結果是由另一位黃兄交到女生宿舍的大妹。我對老吳說了日語,而看那位表情是懂日語的,所以應該90%是東北人。後來在刑警總隊時,有一夜來叫我,我還以為是提訊,結果是託我解釋一段台灣農業界出版社出版的日文版《台灣農民運動》。我當時國語還差,還是總算把那一段的意思讓他明白了,所以我這一猜是對的。
另外一位穿警裝,稍胖,口袋鼓鼓的,可能是手銬,手槍是露在腰帶上。而後我把書閤上,把窗關上,順便對外邊迅速地掃了最後一瞥,兩位校警已不在窗下,抬頭看看窗上牆上掛的羅漢圖,深深地吸了一個氣才對他們說:
「那就走吧!」
那位寫提審狀的就開口:
「那先生吩咐,不要帶手銬,請你不要亂動。」
「不會的。」我說了後心內還帶一點慘然的笑意,對自己的潰敗,以此做了總結。由他帶頭,下樓梯,沿著走廊,走過餐廳,進入本館。已沒有人開房門,而後左折拐南館西邊的舊赤十字病院的老舊走廊。
宿舍沿路很靜,按平常2點1刻,考前應還有人看書。那位年輕的走在前面,我也靜靜地走完全程,以後宿舍有人不知是由何處窺看,傳說:「他離開的時候,像一個英雄好漢。」這句話委實對我是太沉重了些。不過總算是一件事,以這種平淡冷靜的方式演完,在我心內已經早有幾次彩排了,到了校門口看到一架中型吉普車,卻是普通的赭色,不是傳說中,及5月28日夜看過的紅色吉普。
這時候那先生對我們一行告別,我就說:
「謝謝那先生,辛苦了。」然後車內還有一位,也說了差不多同樣的話。原來外面除了駕駛以外,另有一個看守守著先被捕的陳子元兄。以後才知道他是農經系三年級,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而後各人坐上去,車就開了。我就在陳子元兄的鄰位,雙面有位看守,那位東北先生坐助手席。
不帶手銬、不矇眼,這算是異數,傅校長對我的厚意。大概不是去保密局。看錶已經2點30分,當天穿的藍與淺藍的小方格襯衫,草綠色的美軍褲子,陳子元兄穿的是黑色的日本學生裝。
這時台北車輛最少、行人最稀的時刻,車很快地就到了刑警總隊。在押房外,要在表格上填上私物,就在那裡錶、腰帶都被收了。陳子元兄身邊約有300元,我連一毛錢也沒有。
(摘錄)七、一九五○年六月,延平北路北所問案
我們一路沒有矇眼,走上延平北路,在一家舊工廠模樣的門進去。紅漆已經剝落褪色成為很平凡的鐵門。它就是日據時代的高砂鐵工所,以後稱為「新高鐵工廠」。因為人犯暴增,我們通稱的保密局「北所」;五月匆促動工,它以此名與舊日本台灣軍司令部看守所的南所分別。入所的手續大致和刑警總隊相同。
北所押房床板約離地面一尺,寬約一丈八,深約兩丈,高約由地面算起約八尺。是紅磚堆砌的,隔間只有一層磚,牆面連水泥粉刷也省了。押房最外面是木條,門寬約一公尺,一公尺半高。押房之間通路是土面,連磚也沒有,工程可見相當匆促。
每個房子約廿四、廿五人,比起南所人還多,但是這裡已經是天堂了。我進B4押房,內有蘇友鵬兄,一進去就問我這四十天外面的消息。大概我說話太多了,這房間有位外役在外面掃地,不到十分鐘,我馬上被「白面」(看守)把我移到A2室,而且以嚴厲的臉色叫我:「不准亂說話」。
白面先生自此似對我印象不好。除了這位白面外,另有兩位,臉稍黑,公事公辦不會找麻煩。再一位胖子,大概三十多歲,動作敏捷又能幹;軍階上尉,好和年輕人開玩笑;偶而曬太陽由他帶班,他會拿出香菸請客,很四海。他出差或休假就有一位高個平頭的來替代。
所以除了白面值班外,我們就每天聊天。最熱門的題目是「吃」。許省六兄就是特具一格,坐在馬桶上,把右腳抬起來,放在左大腿上,雙手一直比一直畫,輔助他說話的內容。家鄉台南市舊稱府城,本來就是以小吃聞名全省。我在家甚少外食,反而比外地人知道的少。台北圓環、龍山寺、祖師廟、新竹城隍廟、台中大橋腳肉圓、高雄愛河邊海產,我都嚐過。五十多年前台南的小吃甚少用味精,現在可能不用的很少了。
白面先生值班,就靜靜地下象棋。我也常下。象棋和圍棋是名副其實的快棋,象棋一局不到十五分鐘。一天發草紙三張,比現在的衛生紙小,稍厚,土色,由竹子造的那一種。贏一局草紙一張或早上稀飯的菜,花生一顆。早上發的花生平均七顆。我贏了掛帳,似乎有點本錢。八月下旬換房就沒有玩象棋了。有些人輸掉早上七顆花生,喝白稀飯。飯量不限,可以加飯,菜最多是冬瓜。軍法處看守所是玻璃菜、豆芽。
這裡晚上睡得剛剛好,腳可以伸直,也不必人人側臥。南所曾經人擠到分三班睡覺,倚牆坐臥一班、坐睡一班、站的一班。看守兩小時換班,我們也換班。約四疊(榻榻米大小)牢房,多時擠了廿三人。五月十三日以後,人暴增才趕建這北所。能不能睡成,看各人造化,比以後軍法處看守所還擠。我在十號押房,最多時卅五人,就如沙丁魚罐頭般,擠得滿滿的。
入北所翌日,六月廿五日上午十點半左右,白面先生來叫。同房的人早已有叮嚀,馬上會問口供,不是很重要的不必否認,反正我似乎是最後一尾網中的魚。資料都有了,爭辯也無用。白面先生帶我到分為兩房的二樓。
當時大家叫這個節目為開庭,其實只是問訊。有一位帶圓圓眼鏡,身材稍瘦,近四十歲穿香港衫的人坐在那裡;桌子上有文房用具及一落十行紙,左邊有一疊卷宗。一進去,他用廈門腔說:「請坐。」我就坐下來。就坐的規矩小學就教過,我是按規矩靜靜坐下,心內似乎平靜。
「請問貴姓?」我也用廈門腔問他。他回姓莊。以後他是以「莊西」聞名,以前是甚麼,我也不想去查,只知道以前可能是中共黨員;谷正文也提到他姓莊。蔡孝乾案,從頭由他問案、筆錄,甚至分析、追蹤。氣氛有些詭異,二樓無其他人。
「抽菸嗎?」桌上一包洋菸,倒忘了什麼牌子。我個性有許多怪處,不抽菸,但對各種牌子價錢很熟;好像與小汽車無緣,也對各種汽車的價錢有興趣。不但是美國菸、公賣局的,連一九四九年以前流行的豐原私菸也要打聽一下。牌子似乎很熟,似是駱駝牌。我坐下來,東邊(左邊)有家相當別緻的三層樓洋房。這時候由頂樓窗口,流洩出了貝多芬《第五號命運交響曲》的四連音。我心中怔了一下,又暗喜。
這個樓上,格局甚小,除這個房間外進去有個不大的臥房。聽了《命運》的四連音,心內一緊,我挺直腰。「謝謝,我不抽菸。」
莊西好似辦公事一般,由卷宗抽出葉兄和楊廷椅的口供部分,放在我前面,往前一推:「看一看。」
當時速讀一小時十萬字,普通五分鐘可以看那兩份五、六千字口供。但這是對我很重要的文件,我小心看;但沒有細讀全部,只看自己有關的部分,現在心中很遺憾。當時心內可能也煩,只想知道自己不能不承認的部分。不過楊廷椅由廖瑞發介紹,葉兄由劉紹光介紹入黨是看到了。不是我沒有鬥志,但在這種場面,鬥志是無用武之地。這時候,《第五交響曲》第一樂章剛剛結束。
莊西一雙眼眸在我看兩份口供時,一直盯在我的眉間,我內心有點不舒服。看完了把口供還給他,也無意去避開他的凝視。他似乎對我看得快有些意外。我的速讀,無師自通,是小學向人家借書,老是被限制時間,一半被逼出來的。速讀好處少,我的一生可能受害比受益多。「有什麼意見?」
我心內想以退為進。「大致沒有,有一點小錯。我的宣誓是一月廿三日。不是二月上旬。」
「哦──那是當然。當事人記得清楚。楊廷椅沒有交代什麼工作嗎?」這一點我不必傷腦筋。
「楊廷椅,這名我不認識。不過以他的口供,可能是自稱『老朱』的那一位吧。」
「對、對,就是那『老朱』。」
「簡單說起來是沒有,我們只見了兩次面。見面第一句話是自二月所有黨員都停止工作。這個你應該比我更清楚的。我只有聽他聊天,他談了台灣農林問題,尤其對台灣農產他似乎很熟。」
我說到這裡是百分之百真話,只是不必說的不說。當時我已看過蔡孝乾被捕後的相片、談話及廣播。當時決定停止工作的是徐懋德還是陳福星,到現在仍然不知。但是二月十一日《中華日報》登的「鄭啟順」的啟事,當時徐懋德先生反對,所以二月十一日他仍在台灣,以後才離開台灣的。徐先生也就是當時我們常聽說的「外省李」。這停止工作的命令還包括:就是中共對台作戰,也不參加。這一點我就沒有對莊西說。
「那你應該知道他們兩個人已被捕了。」
「老朱是想當然耳。葉盛吉於五月廿九日被捕。三十日他們單位出差到瑞芳,三十日夜宿台大宿舍,他吃晚飯時說的,宿舍的人就知道了。」半實半假。
「劉漢湖和林恩魁,你認識嗎?」
「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嗎?」這部分我可能看漏了。
「你認識嗎?」他似乎有些不耐煩了。
「都是點頭之交而已。林恩魁已經畢業了,可能回到南部。平常沒有談話,他也不住宿舍。劉漢湖似乎自六月十五日畢業考就不見了。」
其實劉漢湖兄畢業考沒有參加,因為五月三十日葉兄被捕,他就不見了;而且這消息是我在新東館東南角的廁所遇到他時,告訴他的。
「有沒有很好的朋友?」回答的台詞是準備好了。
「宿舍的人都可以算是朋友。不過沒有深交的。這種年代,我不想去連累別人。等距離的交友,如套句中國老話,也可以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知不覺,我也用廈門腔和他交談,他對此也似不以為奇。
「好個君子之交淡如水,那麼為什麼不自首呢?」
我想問題已立刻來到這一次談話的重點了,也不能擱下太多的時間,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掉。只好單刀直入,可能過於直話直說。
「葉盛吉沒有被捕時我考慮過。我一直等他回到台北,準備和他商量這個問題,他應該五月三十日或卅一日來台北。現在他被捕,我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那又是為了什麼?」他緊追不放。
「怕我到時候說的與他有出入,對他有影響。」這個顧慮半真半假,反正這個題一定會考,真如馬謖《失空斬》的唸詞:「哪怕小小的街亭。」我實在準備得太鬆弛,漏洞太多,他一聽就知道我的含意是什麼。
「那為什麼不逃?」以後才知道人家說他也是中共黨員,被捕後轉到這一途,如谷正文,當然對馬恩的思維系統是內行的。要在國民黨,或前藍衣社、軍統中去找,就稀有了。他這個老手,就看準問題的核心,駸駸(註)而來。
「這個很簡單,你們去抓我的父親,家裡的生活就慘了。反正無論逃到什麼地方,知情不報,包庇一大堆罪名;我又何必去拖累人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眼神如刀,向我一掃,我淺笑而不語。
「不錯,這就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他給我挑了一個也算是光榮的帽子。我只好接受這個挑戰。他把眼睛移到十行紙上,迅速寫下毛筆字,我只說了一句:「你說笑了。」
這時候對面的《第五交響曲》已進入第三樂章,莊西的錶已近十一點。後來看書得知,就是上午十一點正,北韓向南韓宣戰。內戰用宣戰也是初聞,不過實際上雙方在戰爭狀態已近兩年,也許這是韓國人的作風。中國自一九二七年打了那麼久,沒有經過這麼鄭重而難改的手續。八月下旬吧,台南市工委案到了南所,我們也一直不知道這個消息。他們被隔離、封鎖了消息。就在那時候《命運交響曲》的音樂也正結束。莊西手停下來,「好了,你看一看。有沒有要改的地方,然後寫下你的姓名,再蓋手印。」
沒有印章而蓋手印,這是很高段的。用右大拇指的手印,比印章管用而科學。我也只簡單地看了一下,毛筆字不是正楷,整齊而且沒有難字;既然已經使他心內不舒服,再動也麻煩。簽了自己的姓名,覺得毛筆字寫得太差,好似打了兩次敗仗。我默默站起來,把椅子復位,而後不回頭一直走下階梯。白面先生不在,另位看守等著,帶我回到押房區,交給白面先生。大家也不問情況。大致上我是遵守他們的吩咐,每個人在進行審訊有異同。我與莊西的來往問答,也許各人觀點不同;不過我覺得他正忙著自去年八月《光明報》發生以後,忙了快一年的工作,想趕快做一個段落了結;而我這三等貨色,並不值得他重視。
單地看了一下,毛筆字不是正楷,整齊而且沒有難字;既然已經使他心內不舒服,再動也麻煩。簽了自己的姓名,覺得毛筆字寫得太差,好似打了兩次敗仗。我默默站起來,把椅子復位,而後不回頭一直走下階梯。白面先生不在,另位看守等著,帶我回到押房區,交給白面先生。大家也不問情況。大致上我是遵守他們的吩咐,每個人在進行審訊有異同。我與莊西的來往問答,也許各人觀點不同;不過我覺得他正忙著自去年八月《光明報》發生以後,忙了快一年的工作,想趕快做一個段落了結;而我這三等貨色,並不值得他重視。
註:「駸駸」原來是形容馬跑得很快的樣子。也用來比喻時間過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