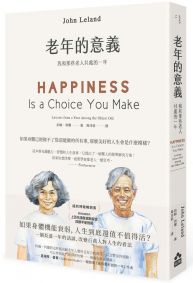第1章 千載難逢的驚喜(節錄)
「給我來杯琴酒!」
「你知道你老了以後想做什麼嗎?」
約翰.索倫森(John Sorensen )回答了我一年問題之後,提出他自己的問題。我們正在他公寓的廚房裡。他的公寓位於曼哈頓上西區,他已經在那裡住了四十八年,六年前他的長期伴侶過世,從此獨居。他四周的壁畫是多年前他種下的樹木,枝條延伸到天花板。感恩節快到了,那是一年之中約翰最愛的日子,他會離開公寓,和朋友相聚。不過二○一五這一年,他覺得他的狀況不大好,恐怕不能去聚會了。廚房看起來和我上次、上上次來訪時一模一樣,因為約翰小心地確保一切都不變──他的視力愈來愈差,擔心如果動了任何東西,自己會找不到。他準備用冰箱旁的小電視和錄放影機看《七對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這部片子總是能讓他開心。他看得滾瓜爛熟,所以不看螢幕也行。
我們當時正在聊生命中令他快樂的事物。約翰總是從黑暗面說起,所以需要一點鼓舞,不過除非他說他想死,否則負面的部分不會說太久。他一旦開始說,心情就會開朗起來。
「我最近在放強納斯.考夫曼(Jonas Kaufmann)唱的華格納歌劇《帕西法爾》(Parsifal)第二幕。」他邊說邊陷入回憶中。「那是我聽過最悅耳的男高音。他長得很浪漫,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華特死後,他正在唱歌,天啊,他唱得真好。」
當時約翰九十一歲。二○一五年年初,我為了報紙的一個專欄〈人生八五才開始〉要追蹤六名高齡的紐約客,為期一年,於是開始拜訪六名陌生人,而約翰正是其中一人。他們意外地改變了我的生命,他們想必沒想過自己會扮演那樣的角色。
所有故事都一樣,是從尋找角色開始。我是透過居家照護機構或他們個人的網頁,在安養中心和護理之家和他們碰面。有些還在工作,有些足不出戶。我見過忠貞的共產主義者、麻將牌友、大屠殺倖存者、現職藝術家,和一位九十六歲的女同志金工,她還在籌辦茶舞會。他們全都曾失去一些東西──行動能力、視力、聽力、配偶、子女、同輩友人或記憶,但很少人失去一切。這樣的人,在美國是一個迅速增長的年齡層,現在人口眾多,因此有了一個特別的名稱:老老年人。
我也曾失去過。我將近三十年的婚姻破裂了,這一生首次獨居。我當時五十五歲,交了新女友,對自己在這世界的身分有些新疑問──關於年齡、愛、性和父親角色,以及工作與滿足的疑問。
我也是八十六歲母親的主要照顧者,父親過世後,母親從她位於紐澤西的牧場房舍,搬到下曼哈頓(Lower Manhattan)的一棟老人公寓。我這角色扮演得不怎麼理想。
我盡可能每兩星期和母親吃一次晚餐,偶爾她晚上進急診室時,我會陪著她。我假裝沒注意到她要的可能更多(我告訴自己,最好尊重她的獨立性),而她也是。我們倆一同跌跌撞撞地走進人生的這個階段,而我們都沒做好充足的準備──她八十六歲,完全不曉得該怎麼找到意義,我也不知該怎麼幫忙。但我們已經身在其中。
我第一批訪問的人中,有位女士珍.戈德堡(Jean Goldberg),她一百零一歲,曾在繪畫用品公司繪兒樂(Crayola)擔任祕書,我們開始聊的時候,她喊道:「給我來杯琴酒!」接著說起虧待她的男人──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但仍然和她人生中其他事一樣歷歷在目。這時的她住在護理之家,坐著輪椅,不過之前是在自己的公寓住到了一百歲,直到接連跌倒,覺得獨居不安全為止。美妙的第一次會面之後,她不舒服,希望延後我們的第二次訪談,改訂的日期來臨時,她已經不在了。不論她是怎麼活到一百零一歲,她發展出的那些策略都隨她而去了(我想大概是幽默感吧,還有即使必須付出代價仍然頑強地不肯屈服)。
那六人都有個故事可以說──有的是美國大蕭條時期的家庭生活,或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性生活,或參與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的經驗,或聽父母說他們不是「唸大學的料」。但我最有興趣的是他們現在的人生,從起床到就寢之間的情形。他們如何度過一天,對明天抱著怎樣的期待?他們怎麼處理藥物治療、子女和持續變化的身體呢?他們的身體正在重返童年的軌跡,身體功能在兒時曾經突飛猛進,現在卻直直落。是否超過了某個底線,人生就不再值得活下去?
正因為他們還活在其中,所以有資格成為專家。英國小說家潘妮洛普.賴芙麗(Penelope Lively)八十歲時說得好:「年紀大的好處不多,不過有個好處是說起年紀,你有一點權威,你現在身在其中,而且很清楚這裡是什麼狀況……我們的經驗對有史以來的大部分人類都是未知。我們是先驅。」我到他們家中、他們看醫生的路上、醫院裡、爵士俱樂部、酒吧和澤西海岸的海濱小屋去找他們。我見過他們的孩子、愛人、醫生、居服員、朋友,還有一位退休的地方檢查官,他很久以前曾經以猥褻罪起訴過其中一人,現在想道歉。後來這之中有一人突然失蹤,電話打不通,我透過布魯克林的醫院系統追蹤他,原來他兩隻腳趾部分截肢了。我在這些過程中傾聽、學習。
在這之中我逐漸注意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不論談話內容變得多麼黑暗(有些時候頗為病態),但每次拜訪都令我振奮,我別的工作從來沒遇過這種情況。
我預期這一年會為他們帶來很大的改變,卻沒料到也改變了我自己。
這六人成為我的代理長輩。他們溫暖、壞脾氣、難搞、健忘、好笑、睿智、會跳針,有時候累得說不了話。他們因為我拜訪得不夠勤快而責備我,餵我吃巧克力,寄剪報給我看。我替他們的公寓換燈泡,聽以色列的事、同情點頭,把我和母親的關係告訴他們。他們時常令人欽佩。他們會記恨,會為了記得吃藥而發展出魯布.戈德堡式(Rube Goldberg)那種過度繁複的系統──這有防呆功能,前提是沒弄掉白色的心臟藥丸,藥丸小到他們手指拿不起來,而且一掉到地上就看不見。
我和他們在一起,必須拋下自以為是的想法,承認我並不了解人生。這是令人謙卑的體驗,但也令人振奮。我用不著當專家或評論家來質疑他們告訴我的事。我只要讓他們引導我見識他們眼中的世界。有時我直覺抗拒某些觀念,但接受那些觀念時,我的收穫最大。我直覺認為自己知道九十歲是什麼情況,其實不然,而我一旦平息那些念頭,要學習就輕鬆多了。身為專家是很累人的。當學生(不再執著於自尊)就像是去這輩子去過最好的餐廳參加宴會。
每位長者就像所有傑出的文學角色一樣,都有所求──我也一樣,只是我一開始不明白。
我最後選定的這六個人有著不同的背景,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我見到弗瑞德列克.瓊斯(Frederick Jones,簡稱弗瑞德)時,他八十七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也是退休的公務員,思想骯髒,心臟孱弱,因此前一年多半時間都待在醫院或康復中心。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跟我說他在一家百貨公司釣到一個比他年輕三十歲的女人,但他不記得是哪家了。
弗瑞德是個花花公子,雖然裝備已經不行了,但他仍然活躍。公寓的老照片裡,他穿著俐落的西裝,留著粗獷的鬍子,不過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為了要穿著矯正鞋上教堂而尷尬,因此大多時候都待在一間凌亂的公寓四樓,對那三層樓梯幾乎莫可奈何。弗瑞德對於年老的意義有獨到的看法。他祈求上帝讓他活到一百一十歲,而且從不懷疑他的願望會不會實現。他說,他每天一早醒來就感激自己又見到一次日出。
我問,他人生哪個階段最快樂,他毫不猶豫地說:「就是現在。」他最能逗我開心。
海倫.摩瑟斯(Helen Moses)九十歲,她不顧女兒大力反對,在布隆克斯(Bronx)一間護理之家找到人生的第二個摯愛。我遇見他們的時候,那段感情已經談了六年。
「我愛霍伊。」海倫說著向著霍伊.季默(Howie Zeiner);他住在走廊底。
「我也愛她。」霍伊說。他坐在她床邊的輪椅上,握著她的手。「妳是我此生的唯一,我說真的。」
「我聽不見。」她說。「希望你說的是好話。」
約翰.索倫森相戀六十年的愛人華特.卡隆(Walter Caron)是書商,愛人過世之後,約翰就了無生趣。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約翰說:「你不會從我這裡得到多少智慧。很多事我都只知道皮毛。」我們聊歌劇和火島(Fire Island,他一九六○年買下那裡的海濱小屋,房價:一萬美元),還有他因為無法做以前常做的事而感到挫折。他很慶幸能在華特衰老時照顧華特,但現在卻無法原諒自己的身體逐漸衰退。
他覺得助行器或輪椅太難看,不肯用,所以從來不出門。他的關節因為痛風而腫脹,彷彿不成對的抽屜把手,而且像把手一樣鬆動。然而談話總是能讓他開心,即使聊他想死的事也一樣。他天天運動,對自己的身體堅持撐下去似乎有種病態的驕傲。
他說:「親愛的,我比很多人好多了,這我很清楚。但我還是受夠了。我不是不快樂,但這一切結束時,我會很欣慰。」約翰說,死亡唯一的缺點是,「我無法活著享受我終於死去。」
王萍八十九歲,幸運掉入社會安全網的有效區──她每月花兩百美元住進格拉梅西公園(Gramercy Park)附近的一棟社會福利公寓,有一週七天、每天七小時的居服員,費用由醫療補助保險計畫(Medicaid)支付。王萍說,工作和照顧丈夫忙得她精疲力竭,比起來年紀大輕鬆多了。但她想念她的亡夫,和她在中國遇害的兒子。她說:「我盡可能不想不好的事。老人家最好別抱怨。」
相較之下,露絲.威利格(Ruth Willig)很乾脆地承認她不滿意自己的人生,但之後她在報上讀到此類的性格描寫,又不高興了──她說她不是那樣。這一年來,我漸漸把露絲的抱怨,看成她試圖影響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發生在身上的事。她原來住在布魯克林公園坡(Park Slope)的一家昂貴照護機構裡,但機構的所有人決定把那裡賣給人蓋更高價的公寓,因此我遇到她的不久之前,她剛被迫遷離。
之前,她為了搬去那裡,放棄了她的車、她的隱私、自己安排時間的自由。過了五年,行動能力更差之後,她卻又失去了那個家,以及在那裡交到的朋友。她以九十一歲之齡,在布魯克林羊頭灣(Sheepshead Bay)更偏遠的一間照護中心重新開始,周遭都是陌生人,身處在不熟悉的地方,就連最近的女兒也離她好遠。
一天早上,露絲說:「這裡有人叫我好勝的老小姐。她沒說『老小姐』,她是說『好勝小姐』。『老』是我自己加的。我不會輕言放棄。或許事情就是這樣。我真的很強硬。」
外面的街道覆蓋著三月雪,所以露絲這天又不能出去了。她說:「我告訴大家,我很有自知之明,我九十一歲了。我不怕。有些人有各種失能,比較起來,我還滿自豪的。我非常幸運。我努力維持健康。我常想我會怎麼死去。不過我只是讀書、看報紙,讓自己有事忙。我盡量讓自己開心,但沒那麼簡單。我希望我能更快樂。」
電影人兼作家喬納斯.梅卡斯(Jonas Mekas)九十二歲,擁有三個三十歲成人的精力和心急。他還在拍電影,剪輯紀錄片和剪貼簿,為他的非營利機構籌措經費、經營自己的網站。
一天,他寄來二○○五年寫的一首未發表的詩。
我辛苦一輩子
只為了變年輕
不,你不能說服我老去
我會以二十七歲之齡歸西
他的朋友比我年輕。他說,他完全沒慢下腳步,反而愈來愈快,因為現在他可以專心進行自己的計畫了。他們六位當了我一年的老師。他們當然正在步向尾聲,雖然我們都一樣,但他們夠靠近終點,所以不只會想到死亡這件事,還會想到死亡會如何發生。死亡不再抽象。他們是否能保有認知官能,他們最後的日子是否會沒完沒了?明天就可能跌一跤、髖部骨折、中風,且回想聊天對象的名字,腦子卻一片空白。每次電話沒人接,我就會擔心。十八個月之內,有兩人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