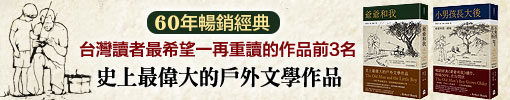一個科學家在好萊塢:《星際效應》的孕育
《星際效應》源自一段失敗的戀情。那份浪漫後來昇華為一段激發創意的友誼與搭檔關係。一九八○年九月,我的好朋友卡爾.薩根(carl Sagan)打電話給我。他知道我是個單親爸爸,獨立撫養一個青春期的女兒(或者應該說,努力試著這麼做,但這方面我不是很擅長),在南加州過著單身生活(這方面我只是稍微擅長一點),同時投身理論物理學家的事業生涯(這方面我就厲害得多了)。
卡爾介紹我一個約會對象,慫恿我去約琳達.奧布斯特一起參加他即將推出的《卡爾.薩根的宇宙》(Cosmos)電視系列節目的世界首映會。
琳達是個才氣出眾的美麗女子,在《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工作,是個反傳統文化、重科學的編輯,最近才移居落腳洛杉磯。她心不甘情不願地被丈夫拖了過來,這後來也成了兩人分手的原因之一。琳達困陷泥淖中,但仍善加利用這看似惡劣的處境,正在構思一部電影,想藉此打入電影界。那部電影叫做《閃舞》(Flashdance)。
《卡爾.薩根的宇宙》的首映在格里菲斯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舉行。那是一場必須打黑色領結的正式聚會,結果我很不識相地穿了一身淺藍色小禮服。洛杉磯有頭有臉的人物全都到場了,而我的穿著跟他們完全格格不入,就這樣風光地度過那一天。
之後的兩年間,琳達和我斷斷續續偶爾約會一下,無奈兩人就是不怎麼來電。她的充沛活力很吸引我,卻也把我累壞了。我心裡掙扎著,衡量值不值得累垮自己來追求激情,但結果這不是我能抉擇的——或許是因為我的天鵝絨襯衫和雙面針織長褲,我不知道,總之,不久之後,琳達就對我失去興趣,不再有浪漫激情,但另一樣更美好的東西也在增長中:來自截然不同世界、大相逕庭的兩個人,培養出一段充滿創造性的長年友誼和搭檔關係。
時間快轉到二○○五年十月,我們再一次共進晚餐。這樣子面對面交談,總會聊起許多話題,從宇宙學最新發現到左翼政治,乃至於美食到變化多端的電影製片業。
琳達那時已經躋身好萊塢最有成就、也最多才多藝的製片,作品包括《閃舞》、《奇幻城市》(The Fisher King)、《接觸未來》(Contact),還有《絕配冤家》(How to Lose a Guy in Ten Days)等。我則是已經再婚,妻子卡蘿莉(carolee Winstein)也和琳達結為最好的朋友,而我在物理學界也發展得不錯。
琳達在那次的晚餐上說了她對一部科幻電影的構想,要我幫她充實細節部份。這是她第二次涉足科幻領域,希望仿效她先前和卡爾.薩根拍攝《接觸未來》電影的模式,來跟我協同合作。
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有幫忙創作電影的一天。除了聽琳達轉述、旁觀她的艱辛歷程之外,我也從不曾夢想在好萊塢占個位置。不過,跟琳達合作讓我很感興趣,而且她的構想還涉及蟲洞——我參與開拓的天文物理學概念,因此她不費吹灰之力就吸引了我和她展開一場腦力激盪。
往後的四個月間,我們又共進了幾次晚餐,加上電郵和電話往來,粗略勾勒出了影片的面貌。內容包括蟲洞、黑洞和重力波,還有一個五次元宇宙,再加上人類與較高次元生物的接觸經歷。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對這部大製作鉅片的想像,打從一開始就根植於現實科學:位於人類知識的最前端,或稍微超前一些的科學。
這是一部從導演、編劇到製片,所有人都尊重科學的電影,而且整個劇情徹頭徹尾從科學擷取靈感,將之編織融入電影的素材中。這是一部能夠帶領觀眾稍事領會物理定律可以與可能在我們的宇宙創造出哪些奇妙現象的電影,以及人類掌握了物理定律後,有可能成就哪些偉大事項。這是一部能夠激勵眾多觀眾投身學習科學,甚至以科學事業為職志的電影。
九年後,《星際效應》實現了我們所有的想像與展望。不過,從當年起步迄今,一路走來倒有點像系列電影《寶蓮歷險記》(Perils of Pauline),過程中的許多轉折點都有可能讓我們夢碎。
我們曾經延攬到傳奇導演史蒂芬.史匹柏相助,接著失之交臂。我們也找到年輕的編劇高手喬納森.諾蘭,卻兩度在關鍵階段失去他,天窗一開就是好幾個月。有整整兩年半期間,這部電影沒有導演,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
然後,它神奇地起死回生,還改頭換面轉為由喬納森的哥哥克里斯多福.諾蘭接掌——這個年輕世代最了不起的導演。
首任導演:史蒂芬.史匹柏
二○○六年二月,琳達和我開始腦力激盪的四個月後,她和史匹柏的經紀人——創新藝人經紀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 caa)的陶德.費爾德曼(Todd feldman)——共進午餐。費爾德曼問她在忙哪些電影,她說了和我合作的狀況,以及一開始就把現實科學融入一部科幻電影的願景——我們的《星際效應》夢想。費爾德曼聞言精神一振,認為史匹柏說不定會有興趣,慫恿琳達送一份電影故事大綱(treatment)給他,當天就寄出!(所謂「電影故事大綱」是用來說明故事和角色的檔案,一般來說篇幅有二十頁或更多),但我們手邊的文字紀錄只有幾封往來的電郵,加上幾次吃飯討論留下的筆記,於是快馬加鞭忙了幾天,草擬出八頁讓我們非常自豪的故事大綱,馬上把它寄出。幾天後,琳達發電郵告訴我:「史匹柏讀了那篇大綱,非常感興趣。我們有可能需要跟他見個面。同意?」
我當然同意!但一星期後,碰面的事還沒著落,琳達就打電話來了:「史匹柏要簽約執導我們的《星際效應》了!」琳達欣喜若狂,我也是。「好萊塢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她告訴我。「從來沒有!」但是它確實發生了。接著我向琳達坦承,我這輩子只看過一部史匹柏的電影——當然是《E.T. 外星人》(長大後我對電影從來不是很感興趣),於是她指定了一份家庭作業給我:「基普必看的史匹柏電影」。
一個月後,我們和史匹柏在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一次碰面——這裡或許應該稱他史蒂芬才對,因為我已經開始這樣叫他了。我們前往南加州伯班克(Burbank),在他的安培林(amblin)製片公司一間舒適的會議室裡開會。
會議上,我向史蒂芬和琳達提出兩條原則做為《星際效應》的科學指導方針:
1 片中不得有任何事項違反已經確立的物理定律,或違背任何我們已經確立的宇宙知識。
2 影片裡對我們一知半解的物理定律和宇宙所提出的想像臆測(往往相當離奇),都必須根源於現實科學,而且相關構想至少得有某些「可敬的」科學家認為不無可能。
史蒂芬對此似乎都能認同,還接受琳達的提議,召集一群科學家來和我們腦力激盪:一場《星際效應》科學研討會。
研討會在六月二日召開,地點就在加州理工學院我的辦公室走道另一頭的會議廳。
議程進行了八個小時,大家熱烈投入討論,題材百無禁忌。與會的有十四位科學家(天文生物學家、行星科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宇宙學家、心理學家和一位太空政策專家),加上琳達、史蒂芬,以及史蒂芬的父親阿諾德(arnold)和我。散會時,大家都疲憊不堪,卻滿懷著興奮之情和嶄新構想,以及對我們先前構想的異議。這是一劑強心針,刺激琳達和我去改寫、擴充我們的故事大綱。由於我們倆同時忙著處理其他事,這次修訂花了我們六個月時間,但到了二○○七年一月時,這份大綱已經擴增到三十七頁,外加十六頁《星際效應》相關科學的討論。
編劇:喬納森.諾蘭
在此同時,琳達和史蒂芬開始進行面試,遴選有潛力的編劇人才。經過一段冗長的過程,焦點最後匯集在三十一歲的喬納森.諾蘭身上,當時他才寫過兩部劇本,而且都是與哥哥克里斯多福合寫的:《頂尖對決》(The Prestige)和《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兩部都是賣座大片。
喬納森(叫喬納也行,朋友都這樣叫他)對科學所知有限,但他很聰明,充滿好奇心,又很肯學習。他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大量閱讀相關書刊,吸收星際相關領域的科學知識,提出犀利又深入的問題,並且提出讓史蒂芬、琳達和我都欣然接受、嶄新又重大的構想。
跟喬納森合作是很開心的事。我們一起腦力激盪了許多次,探討《星際效應》的相關科學。我們一般是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雅典娜神殿」(athenaeum,學院教職員俱樂部)碰面,一邊用餐一邊談個兩、三小時。
喬納森會帶著滿腦子的新構想和新問題來跟我吃飯,由我當場回應他:這一點在科學上有可能實現,那個就不可能⋯⋯我的現場回應有時候是錯的。喬納森會追問我:為什麼?那如果這樣呢⋯⋯?但我的反應沒那麼快。我帶著問題回家,帶著它入睡。午夜時分,在直覺反應受到抑制的狀態下,我反而往往可以想出法子來落實他希望達到的成果,或至少找出變通的方法來達成他的最終目標。我變得擅長在半睡半醒之間進行創意思考。
第二天早上,我會把夜裡寫下的片段筆記彙整起來、解讀它們的意義,然後寫電郵給喬納森。他不是打電話過來、用電郵回覆,就是在下次共進午餐時提出他的回應,漸次整合兩人的想法。我們就這樣逐步向前進展,例如想出種種重力異常,並克服駕馭這些現象的挑戰,讓人類升空離開地球。我還稍微突破現有知識的侷限,使這些異象成為科學上有可能實現的事。
遇到關鍵時刻,我們就邀琳達一起加入戰局。她總是能對我們的想法提出中肯的評論,也很善於引導我們嘗試往各種不同的方向探索。在和我們腦力激盪之餘,她還發揮了神奇的影響力,約束派拉蒙影業以保障我們的創作自主性,同時還投入後續階段的規劃作業,思考如何使《星際效應》的構想落實為真正的電影。
到了二○○七年十一月時,喬納森、琳達、史蒂芬和我已經在故事結構上取得共識——根據琳達和我的原始故事大綱、喬納森的重大構想,還有許多在討論過程中成形的想法,加以徹底改寫——而喬納森也已經全心投入劇本的編寫。但接下來,二○○七年十一月五日,美國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卻發起一場罷工。喬納森因此不得再繼續寫作,也不再現身。
罷工持續了三個月。等到二月十二日罷工結束,喬納森重新歸隊,並跟琳達和我展開密集討論。接下來的十六個月期間,他寫出一份詳細的劇情大綱,然後就投入劇本的實際寫作,接連完成了三版初稿。每一版完成之後,我們都和史蒂芬見面討論,而史蒂芬每次都花一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來仔細提問,接著提出建議、要求或如何修改的指示。他不是那種什麼都要管的人,但他的思慮非常周詳、敏銳,並且富有創意——有時也很堅決。
二○○九年六月,喬納森向史蒂芬遞交劇本第三稿後,又從我們的身邊消失。當時他投入撰寫《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劇本已經有一段時日,但為了處理《星際效應》的事而耽誤了進度,一個月拖過一個月,到這裡他實在不能再拖下去了,於是我們又沒了編劇。雪上加霜的是,喬納森的父親當時還病得很重。喬納森待在倫敦陪伴照料父親好幾個月,直到他父親在十二月裡病逝為止。這段漫長的空窗期中,我很害怕史蒂芬會因此對這部片失去興趣。
但史蒂芬和我們一起堅守到底,靜待喬納森歸來。他和琳達本來大可雇用另一個人來完成劇本,不過他們非常看重喬納森的才氣,決定等下去。
喬納森終於在二○一○年二月回來,接著在三月三日,史蒂芬、琳達、喬納森和我碰面討論喬納森九個月前出爐的第三稿。這次會談的成果非常豐碩。我有點暈陶陶。終於,我們重回正軌。
然後在六月九日,喬納森潛心撰寫第四稿之際,我收到琳達發來的一封電郵。「我們和史蒂芬的協議出了問題。正在處理中。」結果問題解決不了。史蒂芬和派拉蒙沒辦法就《星際效應》的下階段進度達成共識,琳達調解無功。突然間,我們沒了導演。
拍《星際效應》會非常花錢——史蒂芬和琳達兩個人都這樣告訴我。而以這等規模的電影來說,其他能讓派拉蒙放心託付的導演寥寥可數。我覺得自己看到了《星際效應》就此陷入絕境,慢慢凋零死去。我整個人心力交瘁,琳達剛開始也是。但她解決問題的本領,實在令人刮目相看。
導演兼編劇:克里斯多福.諾蘭
從琳達發出電郵告知「我們和史蒂芬的協議出了問題」才過了短短十三天,我打開電子信箱,發現一則令人開心的最新進展信息:「和艾瑪.托馬斯(emma Thomas)談得非常愉快⋯⋯」艾瑪是克里斯多福.諾蘭的妻子,也是他所有電影的製片兼合作夥伴。她和克里斯多福都對《星際效應》很感興趣。琳達興奮到渾身顫抖。喬納森打電話告訴她:「這是最好的結果。」但基於諸多因素,這項協議直到兩年半後才終於敲定,儘管我們十分確信克里斯多福和艾瑪都已經決定投入。
於是我們乖乖等候,從二○一○年六月,等到二○一一年,又等到二○一二年九月。整段期間,我焦躁不安。琳達在我面前總是神色自若,自信滿滿的樣子,但她後來招認,她曾經給自己寫下這段話:「經過兩年半的等待,說不定明天當我們醒來,克里斯.諾蘭也走了。說不定他會有他自己其他的想法,說不定別的製片會交給他更讓他喜愛的腳本,也說不定他會決定休息一陣子。這樣一來,我花這麼多時間等他就錯了。這種事在所難免。我的人生,身為創意製片(creative producer)的人生,就是這樣。但他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導演,所以我們只能等。」遠遠高出我的薪等的協商終於正式展開。克里斯多福.諾蘭要求派拉蒙必須接受和華納兄弟(幫他製作先前幾部電影的片商)共同製作這部電影,否則他就不出任導演。於是,這兩家平常競爭敵對的大片商必須達成一份協議,而且內容極端複雜。
終於,到了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琳達發來電郵:「派拉蒙和華納談成協議。鹹魚大翻身!春天啟動!!」《星際效應》就此交到克里斯多福.諾蘭的手中,而且就我所知,一切從此一帆風順。終於!晴空萬里,樂趣無窮,生龍活虎!
克里斯多福很熟悉喬納森的劇本。他們倆畢竟是兄弟,而且喬納森在編寫時也會跟克里斯多福討論。他們合作的劇本全都很轟動,包括《頂尖對決》、《黑暗騎士》和《黑暗騎士:黎明昇起》。喬納森寫了《星際效應》的劇本初稿,克里斯多福接手改寫,一邊字斟句酌,一邊審慎思考他要怎麼拍攝每一場戲。
完全掌握《星際效應》的主導權後,克里斯多福把喬納森的腳本和他手中另一個計畫的腳本結合起來,注入一個全新的視界和一整套重大又嶄新的構想——它最後將把這部電影帶往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方向。
一月中,克里斯(很快我就開始用這個暱稱來稱呼他)邀我前往他的電影製作公司Syncopy一談。它位於華納兄弟片廠裡。我們約在他的辦公室單獨碰面。
從這次的交談可以清楚看出,克里斯的相關科學知識極其淵博,而且擁有很強的直覺。他的直覺偶爾會出錯,但大多數時候正中紅心。他還富有極高度的好奇心,於是我們的談話內容經常從《星際效應》岔到一些他感興趣的不相干科學議題。
第一次見面,我就要求克里斯必須遵奉我提出的科學指導方針:不得有任何事項違反已經確立的物理定律,以及所有想像臆測都必須根源於現實科學。他對此看來抱持正面的態度,但他也告訴我,如果我不喜歡他在科學層面上的某些做法,我也無須公開幫他辯解。這一點讓我當下有點動搖。但現在電影已經進入後製階段,看他如此恪遵這兩條指導方針,又沒讓它們妨礙他完成這樣一部優秀的電影,真的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從一月中到五月初,克里斯埋頭工作,改寫喬納森的劇本。有時候,他或他的助理安迪.湯普森(andy Thompson)會打電話給我,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或他家裡討論科學的議題,或是要我去讀剛完成的劇本,然後再約見面討論。我們每次討論時間都很長,通常需要九十分鐘,有時一、兩天後還要講很久的電話繼續討論。他會提出我必須動腦筋思考的問題,而且就像當初和喬納森合作時一樣,我總是在夜深人靜時想出最好的法子,隔天上午再把這些想法寫成幾頁的備忘,附上圖表和照片,然後帶著它們去找克里斯。(克里斯很擔心我們的構想會洩漏出去,減損了他的影迷對其作品的高度期待。他是好萊塢最注重保密的電影人之一)
克里斯提出的點子偶爾看似違反我的指導方針,神奇的是,我幾乎永遠想得出辦法來落實他的想法,而且符合科學原理,只有那麼一次,以慘敗收場,後來經過兩星期內多次討論後,克里斯才放過我,往另一個方向發展那段劇情。
就這樣,我終於放下所有不安,不再擔心哪天必須為克里斯在科學層面上的處理方法公開辯解。事實上,我根本就是衷心擁戴!他實現了琳達和我的夢想,拍出一部奠基於現實科學,而且從頭到尾交織涵納現實科學的熱門賣座電影。
《星際效應》的劇情在喬納森和克里斯的手中完全改頭換面,最後只剩大架構還看得出琳達和我那個原始大綱的痕跡。改得實在好太多了!至於科學方面的構想,也不完全出自我的手,有許多出色的想法必須歸功於克里斯,是那種會讓我的物理界同行以為出自我本人的構想,那種讓我看了會不禁自問「我怎麼沒想到?」的構想。其他當然還有一些是我和克里斯、喬納森或琳達一起討論出來的。
四月的某天晚上,卡蘿莉和我在我們位於帕薩迪納的家裡,為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邀集了各行各業數百位嘉賓,包括科學家、藝術家、作家、攝影師、電影人、歷史學家、學校老師、社區組織人士、勞工組織人士、創業家、建築師與其他人士。
克里斯和艾瑪來了,喬納森和他的太太麗莎.喬依(lisaJoy)也來了,當然還有琳達。夜深時,我們幾個人站在露台上,遠離晚宴的喧鬧,在星光下佇立良久低聲交談。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認識有血有肉的克里斯,而不是電影人克里斯多福。那感覺實在太愉快了!
克里斯很平易近人,跟他聊天非常有意思,而且他有種古怪詼諧的高度幽默感。他讓我想起另一個朋友:英特爾的創辦人高登.摩爾(Gordon Moore)。這兩人都是自身領域的頂尖人物,卻一點也不裝腔作勢,喜歡開老爺車,愛它勝過他們其他更豪華的座車。他們倆都讓我覺得很自在——這對像我這樣內向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