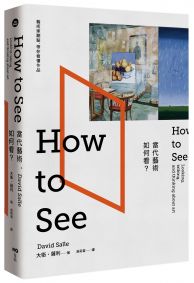〈1980年代,到底好在哪?〉
我差不多七、八歲的時候,有個電視節目叫做《信不信由你!》(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其中有一集我印象特別深刻,內容是有個傢伙說他把自己的車子吃掉了。他花了四年的時間,方法是把車子剁成碎片,每天吃掉一小塊,這個傢伙想辦法把整輛車都吃進肚子,包括方向盤、鉻鋼、輪胎,全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藝術。
這就是今天的情況。當代藝術可分成兩大陣營。其中一邊存在連綿好幾百年不曾間斷的作品,我稱為圖像性(pictorial)藝術;另一邊的數量正在增加,在態度上比較是展演性的(presentational),也就是說,因為意圖和傳遞系統或藝術脈絡而顯得特別的藝術。在這兩種世界觀裡,一種把藝術界定為自我表現,另一種則主要是把藝術解讀為一組文化符號。這聽起來有點像是杜象對於視網膜和大腦的老派分法,但是這個天平的傾斜程度,是六十年前的杜象很難想像的。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因為強調理論而讓藝術的一條基本誡規失去功效,或說受到嚴重侵蝕,那就是以往所謂的臨在(presence),或靈光(aura)。說得直白一點,一件藝術作品之所以能散發靈光,是因為藝術家把能量轉移到作品上,一種美學版的熱力學原則。今天,很少人會去捍衛這種說法。問題是,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呢?
最近,我去蘇黎世造訪友人布魯諾‧畢曉夫伯格(Bruno Bischofberger)的宅邸,他是位大收藏家,也是挪用派藝術家麥克‧畢德羅(Mike Bidlo)的經紀人。在布魯諾的客廳,有一扇窗戶面對蘇黎世湖的景色,窗戶旁邊擺了畢德羅模仿杜象的腳踏車輪。你知道嘛,就是那個上下顛倒安裝在一張簡單木凳上的車輪。杜象的原作本來就是用可以買到的商業品組裝而成,畢德羅仿製的腳踏車輪雖然和原作一模一樣,但卻缺乏「臨在」;事實上,它就跟釘死的門釘一樣死。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它明明就是一模一樣的摹製品啊!我們站在布魯諾的客廳,看著畢德羅的這件雕刻時,布魯諾的太太幼幼(Yoyo)提出一項精闢觀察:「藝術家的作品有的有臨在感,有的沒臨在感,雖然任何東西都可以有臨在感,但沒有任何東西必然會有臨在感。」這聽起來好像魔法,但是看著杜象的腳踏車輪原作——在這個案例裡,原作是個有趣的字眼——你會感到滿足。它有一種靈光。但這個摹製品就不然。單用脈絡,以及隨之而來的預期,真的足以解釋其中的差異嗎?
老派觀點和後來追隨杜象的許多徒子徒孫的觀點,兩者的差異不只是表現的藝術和抽離的藝術,或是暖藝術和酷藝術之間的分別;酷藝術也可能是極為圖像式的,而許多藝術,也許該說我們記得的大多數藝術,都會設法讓自己同時具有圖像性和展演性。就跟生命中的許多事物一樣,這是把重點放在哪裡的問題,換句話說,是一種感性問題。藝術經常是想法的產物;關於空間和物質性;文化史和認同;時間和敘事;再現風格和影像本質等等。在我們今天依然會談論的藝術裡,這些想法都是由形式來體現。當然,在藝術裡沒有什麼東西是非此即彼;甚至連這個說法本身都可以是矛盾的。大多數的圖像性藝術也都包含某種展演性的成分。展演性會以某種方式包含在裡頭。成熟洗練的繪畫都是具有自覺的,它們會表現自我。事實上,我會說,藝術就是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彼此牽制。
然而,自從1968年杜象去世隨之被奉為聖人之後,展演性的藝術開始暴增;開始取得上風。隨著當代藝術的觀眾逐漸增長,受過大學教育的藝術家快速膨脹,以傳輸系統(delivery system)本身做為努力目標的藝術,開始蓋過傳輸內容的風采。這種藝術走向之所以繁榮興盛,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跟簡單的人口統計學有關:去唸藝術學校和參與策展工作的年輕人大幅增加。另一個原因也是受到人口統計學影響,那就是國際藝術博覽會和雙年展的旅遊模式興起——藝評家彼得‧施捷爾達(Peter Schjeldahl)把這稱為「節慶主義」(festivalism)。藝術的脈絡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它的產物。
我們也看到有種藝術大量繁殖,該種藝術的功能就是用來傳輸某種具體清晰的內容。你們聽過那個笑話,有人問畫家他的作品有什麼意含時,畫家回答:「如果我想傳送訊息,我會打電話給西聯電報(Western Union)。」在1930年代的社會寫實主義繪畫裡,我們對作品的評斷,是根據它對階級衝突發表了什麼樣的看法。今天的視覺元素已經改變,但我們還是習慣用作品承載了哪些訊息做為評判標準。
坦白說,展演式藝術的大量增生讓我的心情隨之下沉。我們不願面對的真相是:展演藝術比創作藝術容易。挑選藝術比創新藝術容易。這麼說可能會把你們搞糊塗,因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幾個圖像創新者,例如安迪‧沃荷等,看起來除了挑選之外什麼也沒做——但這是錯覺,借用美容業的說法,你在化妝椅上畫了半天,就是為了化出看似沒化的自然妝容。想做出真正能吸引目光的東西,特別是要讓人重複觀看的東西,需要用獨一無二的充沛活力把知識、視覺和文化的面向整合起來。迴避這項整合工作的藝術,不太可能長久吸引人們的關注,原因很簡單,因為它下的賭注比較少。當你心存僥倖,不敢繃到極限,情感的力道就會減弱。久而久之,這樣生產出來的作品就會有點評論的味道。
有時我覺得,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想要哪種藝術家,而你們會問:「我們為什麼要想?」永遠都有那種藝術家,把自己展演成我們這個文化時刻的化身,彷彿那就是他的工作內容。對某些人而言,這的確是。今日,大多數的展演模式都進一步演化成圖符奇觀(iconic spectacle),非但不否認藝術靈光的存在,甚至還把靈光閃閃的概念轉化成可以把某樣東西搬上舞台供人拍照。也許它本身就是一種新形式,一種藝術,它的圖像價值就是要被人理解,也許只能在雜誌或螢幕這類框架下被理解。我指的並不是普受推崇的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的編導式攝影(staged photography)。我指的是更受限於社交和編輯傳輸系統的圖像運用。我發現,現在的藝術系學生不願在藝術與廣告之間做出任何區分。可能有點以偏概全,但這的確是個明顯的轉變。今天的藝術系學生分不太出兩者的差別,也不認為有必要去區別。也許這只是一種不一樣的靈光。例如義大利裝置藝術家莫里奇歐‧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在西西里島巴勒摩(Palermo)的山丘上重新翻製了好萊塢的標誌;《藝術論壇》(Artforum)上的那張照片讓我們發笑;我們可以領會那種複雜多層的厚顏無恥。但有多少人真的覺得有必要跑去西西里看它呢?
從不逃避戰鬥也不怕說刻薄話的法蘭克‧史帖拉(Frank Stella)說:因為讀了杜象,過去二十五年來,如實主義的藝術(literalist,即低限主義)透過展演行為來界定自己。藝術家試圖小題大作,歌頌自己有能力從日常生活中挑出一些物件和活動,把它們擺放到不同的脈絡裡,也就是美術館或藝廊的脈絡。如實主義認定,展演的藝術和創造的藝術可以平起平坐,藉此對繪畫提出挑戰,但我們必須認知到它的輕率不認真。我很想把這種如實主義的變種打發走,但它已經變成藝評家的新寵兒,因為藝評家一眼就可以認出來。也就是說,藝評家很快就發現,他們可以輕輕鬆鬆處理這種藝術,因為那種藝術很積極地想用打字技巧來界定自己。
1980年代,紐約藝術市場繁榮了一段時間,吸引了主流媒體的注意。當時,藝術圈已經有一陣子沒被當成有趣的話題,枯燥的觀念藝術讓人覺得自己是個笨蛋,而現在,終於有些東西可以拿來妝點了。八卦很有娛樂價值,有些人的個性也很鮮明。與1980和1990年代藝術有關的話題,多半都是把藝術圈當成某個社交系統來閒聊,這雖然也有點趣味,但藝術圈不等於藝術,也不像藝術本身那麼有趣。當時的藝術市場在一段長到被視為常態的寂靜期之後,出現過短暫的茁壯,等到情況轉壞時,有些人不願把眼光放遠,反而開始大發牢騷。他們不再關注作品。我記得在1990年代初,有個《北歐藝術評論》(Nordic Art Review)曾對我提出一個非常直白的問題:「1980年代;到底好在哪裡?」
至少從文藝復興開始,藝術圈一直住滿了怪人和一些奇異甚至令人害怕的個人習慣——例如,據說義大利矯飾主義畫家羅索(Il Rosso)跟一隻人猿住在一起,把牠當成家人。卡爾文‧湯姆金斯(Calvin Tomkins)在他的杜象傳記裡,也舉了一些比較近期的案例,他把紐約1920年代末杜象圈子裡一個比較外圍的藝術家形容成「神經不正常」,她是一位原型行為藝術家,習慣把活鳥別在裙子上,沿著第五大道閒逛。我不覺得,我們希望藝術以其他模樣出現。就像我前面說過的,也許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想要哪種藝術家。藝術作品取得意義的途徑之一,是當它的形式和圖像模式能與大環境的關注系統產生共鳴。另一種途徑,是當藝術家的傳奇性格發揮相同的作用。當某樣東西被認為過時,真正的意思是,編碼在那些樣式裡的藝術家形象不合時宜。裙擺不是太長,就是太短。
流行變來變去。藝術圈令人沮喪的一點是,它願意容忍人身攻擊,假裝是在捍衛某種價值。對1980年代藝術的批判,大多都是赤裸裸的菁英主義。人們不喜歡某幅畫,是因為不喜歡畫畫的人。藝評家羅伯‧修斯(Robert Hughes)對1980年代藝術的惡意攻擊,還包括對收藏家的蔑視,而那句自鳴意滿到處亂噴的「為新貴打造的新藝術」,說得好像法爾內塞(Farnese)或波各塞(Borghese)家族在他們那個時代有什麼不同似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出,修斯那些修辭的本質就是討人厭的勢利眼。
不過,讓我們回到再現的問題。一件作品複製得好不好,對它的普及度有很大的影響力,這種情形已經維持了一段時間,至少從畢卡索開始;例如1960年代以來最受好評的藝術家,他們的複製品看起來都很棒。這並不表示,那些作品沒有同樣強大的實體臨在感,而是說,大多數民眾主要還是透過複製品來熟悉藝術品;有幸能親炙畫作的人畢竟是少數,而那些奢侈到可以和畫作一起生活的人,更是有如鳳毛麟角。不過這種情形和我接下來要說的並不相同:有些具體存在於三度空間裡的藝術,出現在雜誌裡的模樣似乎比在實體更吸引人。兩者到底差在哪裡?把藝術當成一種奇觀是來自不同脈動,特別是藝術總監(art director,藝術指導)的脈動,可說是觀念藝術的遺澤和圖像反諷的融合。
藝術指導是一門指導關注力的科學,但往往是騙人的;那個地方往往會讓人以為你比真實的你更聰明或更有吸引力。藝術指導的大獲全勝,讓藝術界越來越受到它的束縛,讓藝術淪為替反諷服務,替反諷式的形式展演服務,兩者的差別就在於藝術的訊息。就像我先前指出的,現在藝術學校裡的孩子根本不在乎廣告和藝術的差別。你也許會問,他們為什麼該在乎?特別是其他人都不在乎的話。
在1970年代初加州藝術學院的承平時期,當時學校還很有錢,學生可以申請補助金,進行專案計畫。有次我擔任評審,負責挑選優勝者。有個傢伙申請三千美元,在當時這是很大一筆錢,他計畫把一部電視和一台發電機搬到遙遠的山頂上,在那裡看完影集《豪門新人類》(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重播,然後用一把十二口徑的散彈槍把電視螢幕轟掉。我們給了他三百美元,並建議他在洛杉磯下城找間最糟糕的廉價旅館住進去,用BB槍射電視螢幕就好。有些時候,少就是多。自從那個純真時代結束之後,世事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博物館現在會定期付錢給藝術家,讓他們飛到世界各地創作作品,然後拍下照片,透過藝術刊物和社交媒體散播出去。就像俗話說的,如果你能拿到那真是好差事,而留給我們的,就只有雜誌上的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