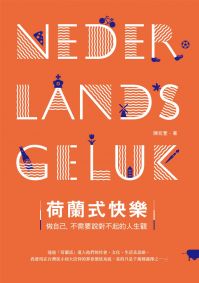Ch.2荷蘭好生活
007 如何養出一個快樂的孩子?Voor het geluk geboren(生而快樂)〔節錄〕
望子不成龍
希望與期望,是父母寄託於兒女身上最重要的情感環節,就算是一向精打細算、嚴肅務實的荷蘭人也是如此;然而觀點卻與台灣社會有著天壤之別。我認識一個讀高等職業學校系統(hbo)的電腦工程師,因為他在學校表現優越,老師問他要不要做碩士研究計畫,商討後他的父母覺得他的個性太孩子氣(kinderachtig),做這樣的工作太費心力,勸說他拒絕。相較於台灣父母望子成龍、學歷越高越好的思考方式,荷式價值觀強調個人意願與性格主宰職場發展,而職業亦無貴賤之分(雖然的確有收入高低之分),實在有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少了拉拔子女成龍成鳳的苦心,荷蘭父母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拿這個問題去問荷蘭人,很多人會這麼回答:「照顧陪伴兒女,讓他們健康快樂地長大。」就這樣嗎?中國式的親情總與責任與義務混為一談,讓人不禁懷想在一個不把「養兒」當「防老」手段的社會,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似乎較有可能建立在純粹的親情之上。但什麼又是「親情」呢?儘管荷蘭子女沒有義務回報父母,父母對子女還是有單向的義務與責任,為什麼荷蘭父母要吃這種虧?荷蘭父母聽到這樣的問題總會哈哈大笑,「到底為什麼呢?」他們自問,「單純就是為了開心吧!(voor de gezelligheid!)」
愛就是陪伴
荷蘭父母是否比台灣父母懂得愛?這個問題涉及到「愛」的定義與愛的實踐方式,我無法回答,可以確定的是,荷蘭兒童日子過得比台灣兒童快樂得多。首先,當台灣中產階級的小孩三歲就被送進雙語幼稚園,從早待到晚上七八點,荷蘭十來歲的小孩還天天回家吃午餐;當台灣父母誇耀自家五歲小孩可以倒背九九乘法,荷蘭父母驕傲地把七歲小孩畫的「抽象畫」貼滿客廳;當台灣父母含辛茹苦不辭風雨接送小孩上心算鋼琴芭蕾繪圖補習英語數學理化,荷蘭父母帶著小孩騎腳踏車漫步樹林原野同樣不辭風雨少了茹苦含辛。
再者,童年在荷蘭被視為人生中最關鍵的時期,需要公私領域共同保障呵護;換言之,在這人生的春天裡,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會孩子信任與愛。兒童在荷蘭社會中地位之重要,可以從一句俗語中看出端倪:「als kind in huis」,意指在某地被當作自家人看待,就像一個孩子在家中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備受寵愛。父母表現愛意,除了逢年過節的禮物、每年策劃昂貴的慶生活動,最重要的是找出時間陪伴孩子成長,這也是為何雖然荷蘭政府努力解決兒童托育機構短缺問題、提供津貼補助托育費用(kinderopvangtoeslag),68%的荷蘭母親仍然選擇兼職工作,就算是全職工作也常只有四天到辦公室上班,一天在家工作。連父親也時常在有小孩後選擇少一天工作,因此就算父母都要上班,孩子一個禮拜還是有兩個整天可以與父親或母親一起度過。這天通常就被稱為papadag(爸爸日)或mamadag(媽媽日),讓爸媽輪流帶著孩子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又可以躲避假日的人潮。
生而快樂(Voor het geluk geboren)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最新報告,荷蘭兒童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兒童。雖然荷蘭在物質享受、健康與安全、教育、行為與風險、居住環境等五個項目都不是第一名,卻是唯一在每個項目都名列前五名的國家。然而荷蘭孩子的幸福其實不僅始於生長的環境,事實上從誕生的那一刻就被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荷蘭的基本保險(basisverzerkering,政府規定必須包含的低階保險項目)包含最少24小時(四至五天)、最多80個小時(十天)的生產後居家照料與協助(kraamzorg),如果是剖腹產則產後照料的護理師也會到醫院協助,生產協助的時數另計。雖然使用基本保險另需支付每小時四歐元左右的自付額(較高階的保險有的會全額給付),對沒有做月子習慣的歐美世界來說,荷蘭的產後照料系統還真是個天堂啊。
這些居家照料護理師不僅提供清掃、洗衣與做飯的家戶協助,還扮演了教育新手父母的重要責任,如包尿布、母奶或配方奶、洗澡與睡眠安全須知等。她們也是助產士與產婦之間的橋樑(在荷蘭產前照料、生產與產後護理通常由助產士負責),擔負起第一線的照料與觀察工作,務求在最早時間發現問題並給予協助。比如說嬰兒若在出生後體重減輕超過標準,她們就會立刻通知助產士,並協助產婦尋找適當的解決之道。然而這麼好康的設計可不是每個媽媽都領情,很多荷蘭婦女會在產後照顧預定結束時間前就提前終止合約,「真是受不了有人在我家裡走來走去的!」荷蘭媽媽憤恨不平的說。至於台灣流行的坐月子中心,對荷蘭婦女來說更是難以想像,她們迫不亟待地想跟寶寶開啟家庭生活的另一頁,哪捨得把孩子交給別人照顧呢?
好教養不如好自在
雖然荷蘭父母照顧孩子不假他人手,花費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心血不可數計,荷蘭卻很少有靠著爸媽吃穿的啃老族或不肯長大的媽寶。關鍵或許在於他們的教養方式極端地強調自由、強調個人體驗,爸媽雖然是孩子安全的港灣,廣闊的世界才是他們的舞台。當一個孩子在遊樂場跌倒了,荷蘭爸媽不會急著抱他起來,天冷了不會追在孩子身後為他穿衣。他們的邏輯是小孩子不需要「聽話」,父母的責任是提供充滿愛意的環境讓孩子自由成長,而非透過規訓與懲罰來要求孩子「聽話」;相反的,孩子必須在與社會同儕的互動中,學會分辨是非,尋找自己可以認同的價值。
為了確保兒童的純真快樂,體罰不管是在學校還是在家中,都是件荷蘭社會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情,面壁思過或被逐出課室,就已經是懲罰的最高表現。老師也不會介入學生之間的爭執,決定誰該被處罰、誰是受害的一方,要求兩造自己尋求解決之道。雖然我們似乎也可以從此推論荷蘭人之沒有禮貌,可能是荷蘭社會近年來對「教養」的輕視,對「自由」的過度推崇;但反方面來說,荷蘭人對權威的漠視、對非黑即白的絕對是非之無動於衷,也要歸功於這種教育方式,讓他們保持了獨立思考與極具彈性的思維能力。或許因為如此,面對社會上重大的爭議與危機時,他們可以迅速脫離「誰對誰錯」互相指責的階段,直接面對問題的核心,尋找合作與解決之道。
Ch.3轉變中的荷蘭
016 荷蘭人的金錢觀Geld stinkt niet!(銅錢不臭)〔節錄〕
「Geld is geld! (錢就是錢)」、「Geld stinkt niet! (銅錢不臭)」我常聽荷蘭人這麼說。說完他們通常就一頭栽進百貨公司的花車裡去了,任憑是從頭到腳一身名牌的少奶奶,還是每月領救濟金的失業單親媽,翻起打折架上物來都是一般的狠勁,老實說從外表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別。街頭上的荷蘭窮人你是認不出來的,每個人都是一樣光鮮走起路來一樣地抬頭挺胸。你看不見的,是那些落在社會溝渠裡的真正的畸零人,還有那些住在百坪豪華別墅裡的豪門巨富;這兩種人每個國家都有,只是在荷蘭的比例比較低就是了。
荷蘭人雖然對打折與特價懷有強烈的熱情,無法躲避貪小便宜這種人格缺點,但說荷蘭人小氣(gierig),卻是一個天大的謊言。首先我舉雙手贊成趁打折時購物,同樣的東西能夠用較低的價錢購買,何樂而不為呢?(還是因為我已經太過荷蘭化,看不出其中的問題了?)再者,關於荷蘭人小氣的傳聞,確確實實是一個刻意捏造出來的謊言,這就是所謂的「Go Dutch」(各付各的)。
Go Dutch(各付各的)
Go Dutch這個謊言已經流傳了三、四百年的時間,始作俑者就是當時和荷蘭人打仗爭海權的英國人,除了比船堅炮利,英國人也努力在嘴皮上取勝。他們先是酸溜溜地說荷蘭人的勝利靠的是酒鬼的勇氣,荷蘭人是灌飽了琴酒(jenever)才敢上戰場的懦夫,隨後卻偷偷地把琴酒帶回國,甚至仿造起荷蘭琴酒來了,但缺了配方做得四不像,卻無礙於用來調配他們的國民英雄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熱愛的馬丁尼。英國人也捏造了荷蘭人小氣的謊言,把Go Dutch(用荷蘭方式付帳──各付各的)這個詞用數百年的時間推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去,讓人們以為荷蘭人真的就是這麼錙銖必較。
其實「各付各的」這個概念在每個西方文化都有,英國也不例外,事實上埃及就把這種付帳方式稱為「英國分帳」。在分開付帳較不通行的亞洲、非洲、南美洲與南歐地區,每個國家都把這種「不夠意思」的付帳方式歸咎給它們自己眼中冰冷沒人情的「西/北方」,比如說阿根廷、哥倫比亞人說這叫「美國方式」,土耳其人則叫它「德式付帳法」,南義大利人說這是「羅馬人的作風」,我想台灣南部的民眾應該也會毫不遲疑地把這種沒人情味的舉動推源到台北人頭上吧。
小氣的荷蘭男人?
「各付各的」在女權運動中被大力地推廣,認為是女性表現經濟自主的指標性作為,如果有男性在約會時主動買單,甚至會當作一種冒犯的舉動。因為「荷蘭」(Dutch)就出現在「各付各的」(Go Dutch)這個詞眼裡頭,自從六○年代的這波女權運動風潮後,世人莫名其妙地得到一個印象,就是荷蘭男人約會是不買單的,還會斤斤計較地跟女生拿著帳單一筆一筆算。我也曾經聽過許多台灣留學生言之鑿鑿的證詞,一再確定荷蘭男人不請客的形象,但我真的必須為荷蘭男人喊喊冤,基本上荷蘭男人其實還挺老派的,他們相信約會時應該幫女士推門、穿脫外套,付帳當然更不必說了,「我媽就是這樣教我的,約女生出去當然要付帳啦!」
但同時荷蘭男人也領受過女權運動的洗禮,所以如果妳吃完飯後出於「不好意思」掏出自己的份付錢,他們也不會跟妳推來推去,他們會以為妳是想表現女性的經濟自主,默默地收下妳的錢。不過這種「紳士做派」的確在年輕一代中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由其他歐洲國家傳入的,強調公平的算帳方式。比如說,男方付了晚餐錢,女方可能就要支付之後上酒吧或看表演的費用。另一個危機重重的作法,就是「誰約誰誰就付錢」,我個人覺得這種方式非常地惱人,有時候還有被陷害的感覺,比如說對方約妳出來卻讓妳挑地點,事後便要妳付費。「是妳約我來這裡的啊!」他們一臉無辜地說。
荷蘭人的金錢觀
另一個可以用來證明荷蘭人非小氣一族的證據,就是荷蘭人是世界上最熱衷於人道救援與慈善事業的民族。粗估荷蘭共有近三萬個慈善組織,其中有117個是全國性的大型機構。以2009年的數據來看,高達87%的荷蘭家庭定期捐錢給慈善機構,其中約莫一百五十億歐元是金錢餽贈,加上價值四億多歐元的物資。荷蘭人不僅出錢,也樂於出力,近五成的荷蘭成人參與義工工作。不僅如此,還有許多荷蘭人到第三世界國家的窮鄉僻壤度假時,看到窮孩子肢障者受虐動物大發惻隱之心,隨即就留下來不走,設置起學校開醫院收容所來了,這樣的人我認識的隨便一數就有一打。
其實不必特意捐錢,荷蘭人平日已經奉獻出大量的收入幫助飬養社會裡的老弱病殘、失業者與低收入者。荷蘭個人所得稅從33~52%不等,視收入高低收稅,收入越高所得稅越高。光是在2014年,就有近一千五百多億歐元的鉅額支出花在醫療與社會福利系統,約佔荷蘭政府總收入的58.5%。荷蘭的高福利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仰賴全民一起支付,這樣的體制對認真工作不老不病的人來說,是不是有點不公平?一般來說,荷蘭人對這點想得很開,或許是受到喀爾文教派的倫理觀影響,他們認為努力賺錢、照顧好自己家庭的需求是首要之務,若有餘力,則應該幫助社群中的其他人。畢竟事業上的成功並不全是個人的成就,實是上帝的賜福、社會條件的許可,因此坐擁金山卻任憑鄰人飽受飢寒之苦,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
經濟危機下的荷蘭福利
是經濟危機逼得荷蘭人不得不自掃門前雪,還是這新時代的美式自由主義荼毒了荷蘭傳統價值,或是兩者都有一點,總之荷蘭的高福利時代似乎已然到了盡頭。在二十多年來最右派的政府主導下,荷蘭開始了一連串的預算刪減,第一個被砍的就是文化藝術經費,接下來他們還想取消荷蘭學生傲視全球的天堂福利──學生津貼(studiefinanciering)。針對高等教育給發的學生津貼金額取決於父母的總收入,此外不與父母同住者可得金額亦較高,每個月可領96至509歐元不等,再加上一張可免費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通勤卡。基本上學生津貼只是零花錢,一般公立大學約莫一、兩千歐元的整年學雜費通常還是要從父母的腰包裡出來。
這聽在台灣人耳中可能感覺不出厲害,畢竟幹嘛政府要發零花錢給學生呢?未出社會工作的孩子跟父母拿零用錢,似乎挺天經地義的。然而在荷蘭因為高所得稅以及各式各樣的高額民生支出(如健保費、政府稅等等),一般家庭每個月剩餘下來的錢少之又少,因此凡是沒有津貼的事,大抵都做不了。因此學生津貼一旦被取消,大多數的學生必然得申請貸款,要不然就算他們打三份工,也付不了租屋費、書本費與交通費,更別提年輕人的一點小娛樂,看看電影跟朋友吃吃飯了。
後記:Geen aardappeleter(不吃馬鈴薯的人)〔節錄〕
我還記得抵達荷蘭的第一天,清早下了飛機整個人昏沉沉的,坐在車裡望向窗外,透過車窗上的霧氣還有我濛濛的疲倦,只看見公路兩旁夢境一般無止無休的油綠,綠上點綴了一點又一點的白。那是一隻又一隻或站或坐,或低頭吃草,或淡定地甩著尾巴的牛;是一隻又一隻或跑或踩著步,或翻攪著糧堆,或快活地在主人的撫愛下嘶鳴的馬。有時候則是裹著一身毛的白羊瞇著眼,身邊圍繞跪著依偎著的小羊羔;有時候是野鹿睜著受驚的棕色眼睛,縱身躍過盛夏翠綠的玉米田,瞬間消失在森林的邊界處。
我記得我從來沒見過那樣空曠的原野,牛馬羊愜意地在偌大的綠地裡悠遊漫步,牠們的籠子到哪裡去了?圈圍牠們的柵欄到哪裡去了?還有成千上百,推擠著觀賞牠們的人們呢?我腦中浮現一張清境農場的新聞照片,一邊是佔據半個山頭烏鴉鴉的群眾,一邊是零星幾隻嚼著草的小綿羊。我狐疑了起來,這真的是荷蘭嗎?難道它不是西歐地小人稠、人口最密集的國家嗎?那連延的綠地是怎麼一回事?那一棟又一棟散落在小鎮裡、有著前院後院的透天住宅是怎麼回事?難道它不該是布滿了灰黯蒼白的公寓高塔,像天啟故事裡等待著被災難擊碎的巨人之國?
如果我再用力回想一下,我會說連光線也很奇幻呢,一道一道的,像童話書裡畫筆刻畫的天光,從層層堆疊殿堂一般的雲層裡探出身來,渾身帶著橙金色的光澤,灑在原野上的時候,會輕輕拍醒草地裡的一群精靈。天空似乎比南國近些,車開在公路上,像是要駛進白雲裡了,藍天隨時就在手邊。
當然有可能,其實我只是在做夢罷了。
每次回台灣,一推開機場的玻璃大門,炙熱的薰風辣燙燙地貼上臉來,瞬間逼出額頭上的幾滴汗,空氣濃沉地呼吸不動,計程車客運車引擎轟隆隆地響,像陳年的煙鬼一般嗆咳著灰撲撲的廢氣。就在這一刻,一直到十年後的現在,我的內心還是會突然浮現夢醒了的「錯覺」。像是在荷蘭的生活是一場夢,而十年間越來越破舊的機場大廳,以及大廳裡逐漸剝落的皮沙發,才是真正的「現實」。
我時常自問這所謂的「現實」是什麼,「虛幻」又是什麼?何以我這些年來居住生活的國家,相對於這塊我經年闊別的土地,顯得如此地「不真實」?這絕對不是因為國外的生活如夢幻一般美好,好像每天都是玫瑰般的芬馨、揚起小指頭手捻著咖啡杯啜飲的優雅。這也不是因為許多台灣人自己鎮日批評謾罵的「鬼島」事蹟──擁擠、混亂、壓力、超長工時、黑心食品、貪污、政治鬥爭、群族對立、污染與貧富不均,好像黑暗的醜陋的才是「真相」,光亮的美麗的必定是難得的奇蹟,亦或尚未被戳破的幻覺。
事實是,每個國家都有美好也有黑暗的一面,不同的是人們面對它們的態度。在台灣,我們與社會的連結非常緊密,人們相信自己與國家是一體的,國家像是自己、家庭的擴大延伸,但連結的方式並非是一種專業性的關係,是一種情感性的家庭關係。因此我們可以對政治人物的言行極端重視,卻對政策與法規、以及其牽涉的權利義務不甚關心,除非它與切身相關或直接影響到自己的權利。我們相信人治,我們相信一票選總統是民主的最高表現,我們對制度充滿懷疑,我們義憤填膺地走上街頭,卻一再投給那些不斷背叛我們的政客。
在荷蘭呢,我時常有一種漂浮在空氣中的輕盈感,像是在科幻電影裡穿著白衣玻璃面罩的太空人,不論自身如何躁動,四周依然波瀾不起,我滿溢的憤怒與不滿就這樣徐徐滲入那片黑絲絨般的真空,不知不覺地也就漏光了。這裡的空氣裡總是有種漠不關心的氣味,無論再重大的事件發生,人們還是面無表情地呼進那空氣,然後吐出更無關緊要的氣息來。國家是什麼呢?對荷蘭人來說,國家絕大多數時候是一個人們集體組成的公會組織,扮演著保護集體權益、統籌物資、極大化其效能的角色。它是一個體制,它沒有面孔,人們透過選舉來微調其走向,但鮮少極端地改變政策,更別提台灣最愛提的政黨輪替大搬風與事後清算。
但荷蘭人絕非自掃門前雪的冷漠民族。事實上,在這裡居住生活工作的每個人,都付出大量的金錢與心力,挹注給需要協助的弱勢族群,無論是離婚後陷入困境的單親媽媽、逃亡到此暫時居留的難民、無法自理的失智老人,還是罹患重大疾病需要特別照料的病人。這一切都被包括在體制裡,透過增收高所得稅支付。不需要拉著布條到政府部門哭訴陳情,不需要戴著口罩邀請民代喉舌,也不需要仰賴少數善心人士寒冬送愛心。體制因此維持了接受者的尊嚴,也將施予者從高高在上拉到地面,腳踏實地地落實平等社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