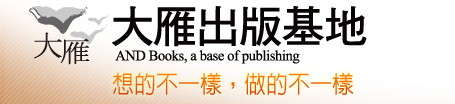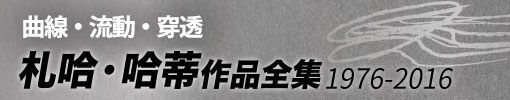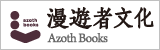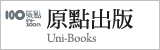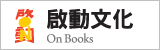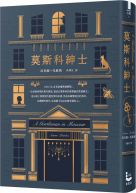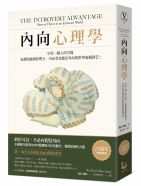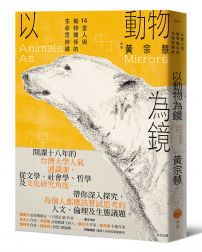增訂版序
遇溺歸來
《以動物為鏡》出版五年後的暑假某天,編輯辰元透過臉書訊息敲我,問我是否有意為這本書再多寫一兩篇文章,推出增訂版。相較於當年對於出書邀約的猶豫,這次我幾乎是一口答應。「態度丕變」的主因說來或許有些好笑,就是我終於有機會反省之前寫書過程的拖延,還辰元一個「公道」了。
當年遲遲不開始的原因,在【作者序】中已有交代。事實上,那時我不但寫作過程拖拖拉拉,終於完稿之後,還像是被逼著寫作業、備感辛苦委屈的小孩一般,對辰元說我決心再也不要寫書,並且要把立志當「一片歌手」的誓言寫在序裡──還好她成功勸阻了我,讓我免於在日後成為言行不一的人,因為在那之後,我不但和妹妹宗潔對寫了一本《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近期還又共同編著了《動物關鍵字──30把鑰匙打開散文中的牠者世界》。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因為曾經有《以動物為鏡》帶來了好的開始,原本傾向於把寫書的優先序排在各種工作後面的我,才有了這樣的改變。
而所謂好的開始,倒不是指這本書為我帶來了什麼殊榮,而是它讓我體認到,原來透過出書確實可以讓「文學、動物與社會」這門課的影響,拓展到學院以外。迄今六年間,我因此認識了更多同樣關心動物的人,他們的回饋成為暖心的支持。也因為這本書的「牽線」,《天下》雜誌針對這門通識課程做了專訪報導、TED x Taipei邀我以動物主題進行短講,之後我又陸續參與了包括二○一八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在內,不少因出書而促成的演講活動。對於心心念念想改變動物悲慘處境的我來說,長年在動物研究上的成果,能觸及同溫層以外的地方,是始料未及的幸運。
但仍不得不誠實地說,「成也動物,敗也動物」好像是我的某種宿命?這些年透過撰寫動物倫理的相關書籍、進行專題演講,雖讓我得以實踐大學教師的社會責任,但在日常生活中,真實動物的遭遇卻常常令我揪心,不管是不時聽聞的動物慘況,或者是自己身邊動物的老病離世。目睹台灣社會的野保與動保更趨對立,野生動物與流浪犬貓的困境卻無緩解的時刻,我常感灰心;而摯愛的KiKi來不及過牠二十一歲的生日(我當年還在【作者序】中,慶幸高齡的牠仍陪在我身邊)、原本貌似健壯的小橘無預警被惡疾帶走(【〈光球貓〉裡的共感】後記中,像龍套角色般出現在文句中的牠,其實是我口中「千年一遇」的此生最愛),更使我不斷「遇溺」。
遇溺,是作家韓麗珠對於「無法向外界求助」「人只能獨自泅泳於凶暴的失喪之海洋」那種失去所愛之殤所做的精準形容。但我終究還是沒有在哀傷的汪洋中窒息,或許,就是因為在回望這段辛苦的、以幫助更多動物為使命的日子裡,總還有些足以讓我鼓勵自己游上岸的力量吧。而那些力量,弔詭地,也來自於不同處境的動物之殤。因為還有那麼多我看不過去或放不下的動物際遇,所以不能放棄努力,得把自己的體認化為文字、化為改變的契機。而這也是我爽快答應為增訂版再寫新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在「心情告白」之後,簡單說明一下增訂版選入賞析的文本:分別是卡夫卡的《變形記》與狄西嘉執導的電影《風燭淚》(Umberto D,又譯《退休生活》)。對於在「文學、動物與社會」的課程上曾「曇花一現」的這兩部作品,我在新增的第四章〈羈絆的奧義──無法/不願獨活的人類動物中〉以「沒有救贖的人類動物」及「被動物救贖的人類」為之定調。這當然不足以涵蓋它們豐富深刻的其他意義,但作為一本以動物為主軸的書,卻剛好可以凸顯因變成蟲而被人類拋棄,以及人因無法拋棄動物而存活這兩組相當戲劇性的對照情境。尤其是《變形記》(Die Verwandlung),當初因為考量通識課程的性質,課堂多半選取能延伸思考人與動物關係問題的短篇故事,篇幅較長又較為複雜的這部經典,只選讀過一兩次,就成了課程的遺珠。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的此際,透過增訂版選擇他最知名的作品來評析,除了別具意義,對我個人來說,也算彌補了小小的缺憾。
最後,謹藉增訂版序言的空間,感謝在這六年間受邀到我課堂上演講的講者們:詹正德、陳玉敏、陳宸億、譚立安、羅晟文、胡慕情、張徐展、鄧紫云(註)。這門課從開課以來,就有幸邀請到許多專家學者,和我一起為減少動物的苦難而共同努力,也分擔了我教學上的苦難──讓學生們面對動物在社會上遭到的各種傷害,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常得目睹學生們因為上課聽聞了原先未知的動物殘酷而神情黯淡,有時也從他們口中聽到我不曾經歷的操作實驗動物、或是到收容所與保育中心擔任志工時的心情起伏。這些都讓我曾經忍不住因心情沉重,而開玩笑地說我要發展其他專長,要「另謀高就」開一門講的人開心、聽的人歡喜的課。
但是我依然持續開設這門不討好的通識課,也依然在這裡,一字一字敲打這些年來因為動物、因為出書或授課所感受到的點滴心情。儘管曾經堅信「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的我,現在比以前更常出現動搖的時刻,但我想,遇溺之後,我仍會繼續這樣,為動物而努力,在母親、姊妹與先生的守護下。
後記:
辰元寄來一校稿電子檔之後,我始終沒有打開──因為【增訂版序】的標題。十四歲就走到腎衰末期的愛貓Kin獎眼看將離去,我實在沒有信心直面「遇溺歸來」的承諾。不忍讓牠被病痛折磨,也不願接受年初剛安樂小橘,年末又要送走Kin獎的殘酷命運。但終究艱難地選擇了放手。因為牠的痛比我的更重要。可以這樣愛著動物的我,未來還是可以負傷前行的吧?在離別到來前,我在Kin獎的身旁,打下了這段文字。
(註)依應邀講課的學年度排列,已列於原版謝辭的講者們,則不在此重複。
推薦序
發掘屬於自己與動物的關係脈絡──《白熊計畫》作者.羅晟文
八年前的秋天,開學後不久的一個午後,一段巧妙的機緣使我走進了新生大樓二○四教室。那是我第一次到外文系聽課,並不曉得「文學、動物與社會」課程會講些什麼,也很期待能不能讓我那僵化的研究所生活有些調劑。最初兩周,宗慧老師分別介紹了〈峇里島的雞為什麼要過馬路?〉與〈雨中的貓〉兩篇故事;我很驚訝原來文學能被分析得這麼精彩,而且可以和生活中曾接觸到的動物,或動物事件作對應思考──我未曾作過的思考。
第三周,當我還在想著前兩篇故事時,我們讀到了史坦貝克的〈蛇〉。故事中的女主角闖入了一位年輕科學家的生物實驗室,並下達了想買蛇、想看蛇吃老鼠等一連串命令,讓科學家難以招架。蛇女與科學家的對峙猛然喚起了我兩段埋藏許久的回憶。
國中一年級時,自然科學是我熱愛的科目;我想當科學家,也喜歡作實驗。當時學校有「獨立研究」的課程,我們必須自己找一個科學題目來研究一個學期。由於家住高雄,離海不遠,我和一位同組的朋友選了寄居蟹作研究對象。我們打算研究寄居蟹的選殼機制,或是牠們的視覺與嗅覺。那時網路搜尋引擎並不發達,而研究台灣寄居蟹的文獻也不多,我們不知道該怎麼開始。
隨後,我們很幸運地聯絡上一位研究寄居蟹的海洋生物學家;他十分熱心,也歡迎我們參訪他的實驗室。在實驗室裡,他和我們分享了他在潮間帶的研究、探險經歷,以及他整齊、潔淨的大規模實驗裝置,令我們大開眼界,十分興奮。當我們請教他關於研究選殼機制時該如何讓寄居蟹先暫時離殼,他說「用火焰稍微加熱貝殼尾端」,但要很注意,因為「有時一不小心,寄居蟹會被燒死」;而若要研究視覺、嗅覺的影響,為了控制變因,最簡單的方法分別是「剪眼睛」和「剪觸鬚」。我當時很錯愕,想了很久但終究沒有提出質疑,心想也許這就是專業科學家做研究的正確程序。回校後,我們跑去問生物老師,她認同了海洋生物學家的說法。雖然我沒有故事中蛇女的霸氣,可以直接挑戰科學家的權威,但這段訪問讓當時我景仰「科學」的心,首次產生了些許動搖。最後我們決定不研究那些東西,改研究牠們的記憶能力,讓寄居蟹練習走迷宮。
第二段回憶同樣發生在我們的寄居蟹研究。有一回寒流來襲時,我在海邊採集了數十隻寄居蟹(註),傍晚回室內時,我擔心夜晚太冷,所以調製了室溫海水給牠們。結果隔天早上,這群寄居蟹死了大半──寄居蟹是變溫動物,夜晚根本不應該用室溫海水;更讓我難過、懊悔的是,我竟然誤用人類的感官知覺來斷定另一個物種的感受,從而害了牠們。當時數個月實驗期間,我把寄居蟹當成我的寵物看待,許多甚至還取了名字;然而因為我的無知,最終實驗結束後,存活、放回海邊的寄居蟹並不多。
這項在我國中時以科學之名進行的「動物實驗」給了我很多遺憾,但卻沒能記載在最後的科學報告中;隨著課業量增加,我回想起這件事的頻率也逐漸減少。直到讀了〈蛇〉,我才驚覺,如同宗慧老師在【一種寂寞,兩樣投射?】文末提及的那隻她不曾伸出援手的「雨中的狗」,寄居蟹事件在我心中,其實一直都沒有結案。
每個人的心底,可能都深藏了一些無法結案的動物事件或疑問;它們也許被封存了好一段時間,且值得被重新面對與思考──並非為了結案,而是持續探索事件背後的人與動物關係中,還存在哪些可能性。但如何催化、喚起這些思考?宗慧老師在文學的脈絡下,以短篇故事巧妙地映照了動物在當代社會中的許多面向。雖然這些故事本身並未試圖訴說任何動保理念,但讀完後,許多情節仍不時在我腦中繚繞,並允許我慢慢推敲出自己的提問與想法。
在「文學、動物與社會」課程結束後,我發現身邊不少修課同學也逐漸釐清了自己的定位;有的甚至投身第一線,親身協助動物。佩服之餘,我也不斷問自己:那我能做什麼呢?我會做什麼呢?我是否能將「獨立研究」轉化為視覺創作,探索動物問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其脈絡與專長,而《以動物為鏡:12堂人與動物關係的生命思辨課》宛如一面明鏡,讓讀者有機會以多重的角度凝視、發掘屬於自己和動物間的關係!
羅晟文/二○一八年九月十五日,荷蘭海牙
(註)任意在野外採集生物會破壞生態,應與所屬管理機構審慎討論,並申請採集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