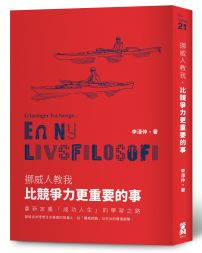第一部分:價值觀
02:褓母證
眼前出現了一道棘手的難題。兩個孩子,一個剛滿兩歲,一個才三個月大,返抵台灣後,我們必然是緊鑼密鼓,為了安頓接下來的生活忙得不可開支,勢將無暇費心照料這兩個還不足以離開你視線過活的小丫頭。於是,我們決定將老大送往未來住家附近的幼稚園,另外再聘請專業褓母看顧小女兒。總之,一切只求度過初期的兵荒馬亂。
由於和台灣已脫節超過六年,要在茫茫人海中尋找合適的褓母,剛開始仿若大海撈針。幸好過去這些年為解決雙薪家庭托育問題,各縣市政府已建構起「社區褓母系統」,我們得以依照預期中的托育所在地和時數要求,透過存列在這套系統中的人事檔案尋找可能的人選。
但問題來了。我們開始逐一面試有意願的褓母,希望利用當面會談的機會,確認將小孩交到對方手上的可行性。首先,我們被紊亂的市場行情攪得一頭霧水,關於托育細節,我們即便提出相同的照護需求,對方卻各有高低不一的薪資價碼,又或者請我們自行開價。有時差異甚至達數千元之譜,我們因而無法確認其間的價差,是否意味著某種不可預測的風險。
我們似乎還未從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情境裡回過神來,以為應當會有依照勞僱條件和托育環境所訂下的「公定價格」,避免自己顯露出一副市儈的模樣,暗自揣想各方褓母受託價錢有高有低,是否代表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尤其事涉一個毫無自保能力的小嬰兒,我們當然不可能認為哪位褓母願意以較低的報酬挺身而出,會是什麼幸運的事。
我相信前來面試的褓母,有些人多少也是帶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不光是我們對她一無所知,她對我們同樣也完全不了解。她們也會擔心我們是不是一對摳門的父母,以為支應薪資,就可對她予取予求,或者動輒交待諸多超乎褓母職責的家務瑣事,乃至把她當下人一般使喚。這種不確定感有時是雙向的,所以換個角度,我們其實也是屬於「被列入考慮」的一方。
這種隱隱然相互懷疑、觀望的氛圍,就像我們日後定居在北投山腳下,偶爾竄入家中客廳的硫磺味,它不會久久揮之不去,卻又不能說它完全不存在。尤有甚者,前來面試的褓母,或許為了取信於我們,有些人會主動出示政府核發的褓母證,以昭信譽。但其中卻有證照上的照片和本人相去甚遠的情況發生,為了不讓對方難堪,我們並沒有當場提出質疑,卻也不打算再與之聯繫。而究竟是誰負責把關,確保不至於發生此類「名實不符」的問題?又或者有人托言褓母證尚待審驗,而意有所指數十年育兒經驗才是最可靠的品質保證,偏偏我們並沒有任何管道可以了解她過往的口碑。另外,還有明顯年紀略長,行動稍有障礙的老太太請纓上陣,而我們是否要基於心底的一絲同情,將顯然會耗費她大量體力的小嬰兒付託予她?
的確,這是我們全然站在僱主一方的觀察。我們負責提供薪水,將幾乎需要時時刻刻對其緊迫盯人的小嬰兒交到對方手上,我們理所當然得審慎為之,以免所託非人。將小孩交給適切的褓母照護,是一對無從全心投入養育工作的父母,對自己小孩最底線的責任。種種顧忌和不安卻因此油然而生,而我也相信,這不會只是單方面的心態,論及褓母受僱時所遭遇過的種種委屈,恐怕也不是以少數個案就能一語帶過。而我,真是厭惡極了這種不信任感。
今天之前,我曾為挪威社會彼此間的高度信任深受感動,他們似乎很輕易就能相信對方不會別有居心。信手捻來的經驗,不乏發生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裡。沒有專人或機器驗票的地鐵閘門;無人看管的路邊草莓販售攤位;乃至歐洲行之有年,卻不再時興的背包客路邊招車行為(因為有過多起臨時起意犯罪記錄),如今在挪威仍相當常見;另外,當地民間組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設計「掉落錢包」活動(將放有一定數額紙鈔的錢包,隨機丟在城市各地,最後統計回收的錢包數量),以測試挪威人的誠實度,結果都是全數找回。至於最為人性化、標榜「信任」,不設圍牆的開放式監獄,則又是社會信任的另一種境界表現。
因為暫居挪威的經驗,我經常有機會和人分享所見所聞,每每提到當地人毫無戒心的表現,與會者總是嘖嘖稱奇,直言果真北歐奇蹟。讚嘆之餘,大家總會忙不迭地繼續追問,挪威人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令人欽羨的這一步?在承命挖掘箇中緣由時,我終究領略出要想創造少有猜忌的社會氛圍,一切原來都是有跡可循。
從小教育小孩「誠實為上策」,只要每個人都能對他人誠實不欺,信任的社會自然水到渠成,這或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陳年道理。挪威社會的實情是很好的佐證,他們總是鼓勵子女凡事誠實以對,為人父母也多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過,除卻「人格教養」的基本訓練,往後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其實還據此培育出了別具意義的價值觀,而那或許才是社會信任度的根本基礎。
按照我們傳統認知,普遍大眾的人生目標,就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個「成功的人」(或者有用的人),「成功」兩字容或有不同的定義和標準,總而言之,我們很容易以某個人的身分、地位、職業、薪資和權勢,去評判其優劣成敗。我們經常以能力好壞與否,聰明機靈與否,作為衡量一個人是良是窳的標準,它使得教育的目光,經常只侷限在單獨個人的成就上,而忽略了每個單一個人的成就,足不足以提振整體社會的氣質。至於挪威式的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僅僅是多參涉了一些元素,就讓自己站上現代文明典範的高度。
也就是在追求個人功名利祿之外,他們還十分看重自己是不是個「可靠的人」。又或者說,對挪威人而言,「可靠的人」,已揉合為成功者的因素之一,甚至他的位階,還高過成功者所能散發出的誘惑。古早維京社會人們為了應付惡劣的生存環境,彼此必須藉由高度互助才能夠保命,這又或者是挪威人願意當個可靠的人,沿襲迄今基因上的遠因。
當多數人不再一味追求自己的成功(尤其其中很可能是建立在偷拐搶騙上),而是以一個值得信賴、且可靠的人做為行事標準,甚至遠比賺取財富或貪得一點點小便宜來得有意義,則社會的信任結構就有望成形。「可靠的人」,會比「有錢的人」「聰明的人」「厲害的人」「有權勢的人」「高學歷的人」更容易在挪威社會取得尊敬,說不定還能得到更多謀事的機會,那麼,誰還會輕易蹧蹋自己的名聲。
在挪威生活數年,我確實大為減輕了因為人我之間的猜忌、懷疑所引來的生活負擔和壓力。當多數人不會利用無人看顧的水果攤揩油;不會因為搭車不用查驗車票就坐霸王車;所有付出和所得皆有公開明確的標準,我們確實就無需成天提心吊膽、緊張兮兮,深怕自己是外國人而容易遭當地人呼攏拐騙。
返居台灣頭幾個月,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回來還習慣嗎?」其實相對來說,台灣才是我更為熟悉的環境,無論氣候、人文和鄉土。只是,久經挪威之旅耳濡目染,我發現回到台灣後,自己便不再保有住在挪威那段時期的天真和自在。基於自我保護,我們有太多機會臆測周遭人士的言行舉止恐怕不會那麼單純坦白,初期它確實讓我有些適應不良。
社會信任感之所以尚難建立,也許真的是有太多的人因為法律漏洞、灰色地帶而謀得羨煞人等的好處,加上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將眼光望向「成功者的光芒」(無論是腳踏實地或欺瞞世人而來),於是便無從體驗彼此都是「可靠的人」(無論達官顯要還是販夫走卒),所能營造出的生活悠適感。當我杵在挪威鄉間一處無人看管的水果攤前,狐疑猜想著難道這水果攤老闆不怕我見有機可趁,逕自當場白吃白喝,沒多久,就看他悠悠哉哉,全身濕嗒嗒地從遠處信步而來,他居然放著水果攤不管,跑去後方湖裡游泳?而他卻從不擔心自己上岸後,會落得一簍空蕩蕩的自動投幣箱。他能兼及生意和一整個怡然自得的下午,不就正是拜可靠的挪威人之賜?
最後,我們終究捨棄聘雇褓母,而是情商自己父母出手相援,至於交涉過程,當然是簡單多了。
第四部分:人格獨立
12:獨居老人
一對挪威老夫婦受台灣親家邀請,一年秋天到台灣旅遊。從台北一○一大樓、嘉義阿里山、屏東墾丁、台東知本溫泉到花蓮太魯閣,短短十餘天,他們就走遍了台灣東西南北。我對他們年近七旬還有這般體力,感到相當佩服。當我問他們一趟台灣之旅,有什麼驚喜的發現,原以為會是五花八門的小吃攤,或是故宮博物院裡的珍藏,結果他們竟然是對捷運和公車上的博愛座最為印象深刻。對台灣人願意起身讓座給年長者的舉動,感到有些受寵若驚,那是他們住在挪威近七十年來極少有過的禮遇。當然,他們夫妻倆如今依舊身體健朗,未顯老態龍鍾,即使站立在搖搖晃晃的車廂,似乎也沒什麼大礙。
移居挪威初期,我最為訝異的幾件事之一,就是當地大眾運輸工具儘管都設有「無障礙專區」,提供給坐輪椅者和推著嬰兒車的乘客使用;只不過,在當地人的搭車禮儀中,卻從未特別強調要讓座給老人家,尤其不見任何「敬老」標示。我相信,其中原因,應該和這個國家多數老人都保有健康的身體和能獨立行動有關。所以就算不讓位給老年人,倒也不具備太大的道德爭議。當一名年近七旬的老翁頂著零下十度低溫,穿著緊身運動服,頭戴毛線帽,拎著雪橇出現在公車上,當下確實不會有人覺得自己應該起身讓座。
根據當地法律,挪威人並沒有奉養自己父母親的義務。就我們看來,似乎有違人之常情,不過,有別於台灣社會的親子觀,卻讓挪威人早自年輕時期就懂得先一步規劃「一個人老後」的生活。於是他們必須讓個人經濟自主,最重要的是盡可能維持良好的身心狀態,挪威人自小養成的獨立人格,事實上是一路伴隨著所有人直到終老。挪威老人或許難得享有子女承歡膝下的天倫之樂;但也因此在人生後半的獨居歲月中,尋找到另一種自我滿足的方法,一如我在奧斯陸公車上所見,那位全副武裝,蓄勢待發準備駕馭滑雪板馳騁山林的挪威老先生。
老年生活品質的維繫,相當程度必然是建立在不假他人的自我照護能力,其基礎除了健康的身體,當然還包括足以供給個人往後日常生活的收入,挪威社會這方面,的確是有賴政府普及全民的退休金制度得以實踐。為了讓人民「老有所終」,挪威政府在二○○六年時,特別將原有的「石油基金」(Oljefondet)修訂改制為「政府年金全球基金」(Statens pensjonsfond utland),它的主要功能即是為了保障人民年老後的收入無虞(這項因石油收益而來的基金,同時也用於其他社會福利),時至今日,所有挪威人一旦規劃退休養老,都可以過去工作的薪資(繳稅)為基準,向政府申請足堪安度晚年的月退俸。
石油收益自然是這個國家得天獨厚的條件,它足以讓當地建造出數十棟超高摩天大樓,但挪威政府卻特別著眼未來世代的老人照護(官方估計,二○五○年挪威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將超過一百二十萬,約占總人口四分之一),因此嚴格限制每年「政府年金全球基金」的使用上限,促使這筆攸關全民的退休老本,能長期維持一定的規模,保障所有國人直到終老,在節制開支下,還能同時用於支付其他社會福利的。
此外,政府對尚無需領取退休金的勞動人口另外又課以重稅,儘管大為限縮了民眾的實質所得,卻又成就了國家機器強制人民為自己存錢養老的手段。政府年金全球基金得以細水長流,不至於出現寅吃卯糧的危機。在沒有子女依法撫養的保障下,挪威老人則是藉由國家系統性的財政規劃,獲致良好的經濟照護。
不過,即使獲致維繫老年生活的退休金,並不表示能全然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挪威政府尚以每年GDP(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點二,用於老人照護措施,包括關切老人健康問題,以及用於翻新養老院的設備,全國且需百分之二點九的勞動力,專以照護老人為業,無怪乎挪威同時也被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評鑑為所有會員國中,老人照護品質前三名的國家。
至於照護老人的百分之二點九勞動人口,主要起於挪威愈加時興的「私人護理院」(omsorgsboliger)制度,意即有別於傳統的養老院,「私人護理院」其實形同個人的私人寓所,且由專業的護理人員親自前往為挪威老人進行居家照護,由於是住在自家公寓,某種程度或許還可省下住在養老院裡必須的環境開銷,然而這也是為了因應當地情境需求。根據挪威官方統計,年齡介於四十五歲到六十六歲的挪威人,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住在自己家裡,六十七歲以上的挪威人,也有百分之七十五仍住在自己家中,對他們來說,自家其實就是最好的養老院,不僅環境熟悉,也可減輕因「養老院」一詞而來的孤寂感,唯超過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因有半數已然失去生活能力,才不得不入住養老院。
為了順應國內老人的需求,政府於是必須培訓大批足以提供居家照護服務的護理人員,讓他們能親自前往老人家中為其打理日常所需,至於居住在自己家裡的老人,體力足堪負荷者,多數仍會積極參與親友鄰里間的社交活動,老人間彼此則彷如互助會一般,交替作東相互邀約聚會,不必然得全權依賴居家護理人員為其規劃活動或安排生活。
於是,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也就是目前任何一間公寓,未來都可能成為某位老人的「私人護理院」,在此考量下,挪威近年新式建築便特別強調空間設計必須符合年長者的行動需求,包括無障礙設施的公寓入口,家中客廳、餐廳、臥室利於使用輪椅,還有浴室的安全措施和戶外活動空間的調配,無非得同時滿足年輕族群的生活形態,乃至其老後依舊能在此悠然自處。
相對歐洲許多國家,挪威老人可謂老當益壯,六十到六十四歲的老人當中,其就業率仍高達六成(歐盟國家平均只有三成);六十七歲以上的老年人,則仍有三成以上寧可從事時薪工作,也不願鎮日領取退休金而閒賦在家;甚至有為數不少挪威人直到七十五歲才開始領取人生第一筆退休金。挪威是一個極為注重個人生活品質,從不強調將青春歲月全拿來打拚賺錢的社會,老來之後卻反向操作,只要體力尚可,他們反而鼓勵老年人不必太早退休,這當然是為了透過活絡的社交活動,維持個人身心健康之故,在獨立自主的餘生中,盡可能不讓自己和社會脫節,亦是挪威老人獨有的養生之道,除了仰仗國家提供系統性的照護措施之外(政府年金全球基金、居家護理人員、養老院),挪威老人們自己其實也過得非常努力。
因為文化上的差異,挪威人打從一開始就無「養兒防老」的觀念,國家機器則適時介入補足了現實上的缺口(經濟供給、人力照護),也正由於舉國氛圍如此,當地老人無論選擇入住養老院,或者甘為「獨居老人」,皆不過是人生另一階段的生活形態。他們仍和多數人無常,會到超市裡買菜,在酒吧裡點杯啤酒自娛,到海邊做日光浴享受午後陽光,偶爾和朋友聚會聯絡情感,「老」或許限制了他們的行動,卻未必同時遏抑了他們心靈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