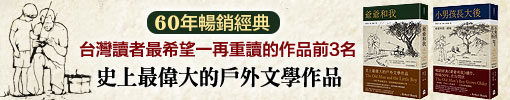最聰明的人,最笨的方法
文/柴 靜
會買這本書的人,肯定像我一樣胡思亂想過一些無厘頭的問題,比如說「為什麼是猴子而不是老虎變成了人?」因為我常常想像一隻老虎坐進計程車,莊嚴地把尾巴掖進來:「師傅,去中友。」自己樂半天。
袁越的解釋是:「因為黑猩猩最耐熱。」
嘎?
「黑猩猩想活下來,它怕夜裡的猛獸,只能中午捕食,而中午最熱。」
這是什麼邏輯?
「哺乳動物最怕熱的部分就是大腦。大腦是單位體積產生熱量最多的器官,也是對溫度變化最敏感的器官。要想為大腦降溫,必須加快血液迴圈,讓血液把大腦產生的熱量帶走。」
「有什麼依據?」
他立刻眉飛色舞:「考古學家通過測量顱骨上的‘蝶導靜脈孔’和靜脈竇穿出顱腔所留下的血槽的直徑,發現越是和現代人類接近的猿人頭蓋骨化石,‘蝶導靜脈孔’越多,直徑越大,血槽也越淺,說明它們的散熱效率也就越高……」
「嗯……不懂。」
「總之吧……靠這套高效的散熱系統,直立人才敢在非洲炎熱的中午四處覓食,靠一頓午飯活了下來。」
「不可能,黑猩猩那速度,能追上誰啊?」
「牛羚的瞬時速度雖然快,但只能維持幾分鐘,否則就會被急速升高的體溫燒死,一個經過訓練的原始獵人可以在炎熱的中午,以每小時接近20公里的速度連續奔跑四五個小時!直到把獵物追得完全沒了力氣,只能站在原地等死。」
哈哈。
他挺來勁。「人是汗腺最發達的哺乳動物,在劇烈運動的情況下,一匹馬每平方米皮膚每小時大約可以排汗100克,駱駝為250克,人可以達到驚人的500克!」
「能排汗有什麼用啊,我就跑不了那麼長時間……」
「你看,長時間的奔跑需要大量的氧氣……」
「……」
「在聽嗎?」
「你說要是老虎坐在計程車裡,會是蹲在座位上嗎?」
「……」
因為袁越有個博客叫做「土摩托日記」,所以我們私下裡都喜歡叫他土老師。土老師在飯局上常常也想談談音樂和文化,但一說話,就被人打趣:「你有什麼科學依據?」
他如果想認真解釋,就引起一陣哄笑。
他嘿嘿一樂,從不反擊。
這句話是他的標誌,因為他有固若金湯的重實證、重邏輯、重量化分析的思維習慣,他寫的這個叫《生命八卦》的專欄,很短,但是每一篇寫得都挺用力。除了他在美國做過十幾年的科學工作的經驗,他還每天去看最新的《科學》、《自然》、《新科學家》和《發現》,《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等的科學版的報導,再動用維琪和穀歌等搜尋引擎,「尋找一切可能找到的相關素材」。
用他自己的話說,最笨的方法。
顧准說過,中國人太聰明,常常追求頓悟式的大智慧,像王陽明那樣,對著竹子「格物致知」,格了七天七夜,什麼也沒格出來,大病一場。
土老師寫這些關於生命的八卦,不追求什麼微言大義,不會動不動就直奔人類的終極智慧而去——我看對他來說,也沒什麼那樣的智慧存在。他只是老老實實地好奇,想瞭解一事一物,所以不帶前提地尋找證據,往往顛覆我自以為是的常識和經驗。
所以,在關於廈門「PX事件」和地震預報的爭論中,他都在提供不同的意見,既不同於官方,也不刻意反官方,他只是忠於他瞭解到的資料,我沒有看到過他因為顧忌而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場上,也沒看過他趕過時髦,他只是展示證據和提供他尋求證據的方式與路徑。
「我在寫作的時候會有意識地在科學思維方式和研究思路上多下筆墨。」他說。邏輯自會將人推向應往之地。
地震時,陳堅遇難去世,他也在場,但他的報導提供的不是簡單的感慨痛惜,而是救助中的科學。「壞死的肌肉釋放出來的肌紅素等蛋白質,以及鉀離子等電解質就會隨著血液迴圈進入內臟,導致腎臟或心臟功能衰竭。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病人幾分鐘內就會死去。」
他引用醫生的話,「面對病人的時候不輕易動感情,這樣才能在冷靜中做出正確的選擇」。
土老師其實也經常試圖抒一下情,前兩天他在秘魯給大家發短信說:「馬楚比楚像個一肚子心事的啞巴,心事重重地坐在山坡上。」
但很快他就對印加人用處女祭祀山神的宗教情感產生了不敬之意:「有個小細節讓我產生了一絲不安,X光顯示,她是被人用尖利的石塊擊中腦殼後死去的,科學家還分析了她體內的血紅蛋白,發現她被擊中後起碼還存活了5分鐘……這不僅是一個宗教祭祀場所,可能還是個謀殺現場。」
在他的世界裡,理性是至高無上的神,一切都在其之下,在這種「求真」的憨態面前,任何感情都要讓步。
他算是歌手小娟極好的朋友了,寫樂評時也直言不諱地批評。寫完還渾然無事去見人家,回來後在MSN上不安地對我說:「她哭了……」
唉。
他也有我看不順眼的地方,就是理科男的優越感。
我看土老師第一篇文章是《我只喜歡和智商高的人聊天》,寫他當天吃飯的物件——「也是復旦的!也是高考數學滿分!」
我這小暴脾氣,立刻寫了一篇我從小沒得過100分、從沒被老師表揚過的人生經歷,還差點把題目寫成《從此失去土摩托》。哈哈。
土老師倒沒生氣,只在MSN上打了個紅臉兒。我幾年後才弄明白,他是打心眼兒裡喜歡智力這回事,這不光是他的樂趣——也許還是信仰?那種興奮之情裡一多半是天真的高興。
土老師的博客座右銘是:偏見源於無知。他的尖銳不是與人而戰,他與他心目中的無知作戰。
當然,有的時候姿態不太好看,男生們嘛,總有點兒覺得自己個兒「站得高,濺得遠」的蠻勁兒,梁漱溟批評過熊十力的「我慢之重」——「慢,就是傲慢,就是覺得自己真理在手,心裡高傲,看不起別人」。
但他同時也是我見過的最講道理的傢伙,即使曾與他論戰的人,即使諷刺傷害過他的人,只要有一個說法有見地,他還是真誠地讚歎。他的博客被老羅從牛博首頁拿掉之後,他對我說:「他刪我刪得有道理」,我原來想過「這廝不是裝的吧……」時間長了,發現還真不是。
用老羅的話,「土摩托是一個極少見的有赤子之心的中國人」。
在胚胎問題上我與方舟子有不同意見時,土老師很不留情面地寫文章批評我。我當時認為我們爭論的點應該在倫理上,但我後來理解了他為什麼那麼來勁,因為他們認為談倫理的基礎是「記者對真相要有潔癖」。
這句話對我來說很有用,以往做一期節目,辦公室裡經常要討論,「我們的落點在哪裡?我們的價值觀能高於別人嗎?」但是,不管你有一千個漂亮的第二落點,有一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真?還是假?」
我在調查中也常擔心觀眾對過於技術性的東西會感到厭倦,但是後來我發現,人們從不厭倦於瞭解知識——只要這些知識是直接指向他們心中懸而未決的巨大疑問的。
所以現在在出發前,我只問「我們能拿到的事實是什麼?這個事實經過驗證嗎?從這個事實裡我能歸納出什麼?有沒有相反的證據?還有,嗯,別忘了,土老師這樣的天敵看了會說什麼?」
我也曾批評他智力上的獨斷與優越感,而從他近來的文字中也看到很大的變化——少有尖銳刺目的字眼,不是「立異以為高」,而是提供更多的材料讓人思考。
我想,這是他約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我們都清楚,人人都有缺陷,所以必須尊重異己,對對方的觀點審慎地觀察和研究,並且公開而有誠意地討論和交鋒,這是糾正偏見的最好方式。
最後說一句。
每次我習慣性地批評土老師文章的時候,他總是非常老實地說:「對,您說得對!」我就不好意思往下說了。偶爾想誇一下的時候,他的反應總是「其實我那篇才叫真的好呢」,雀躍得讓人心碎,也沒法兒接話。
好吧,總算,借此機會,讓我完整地表達一下,土老師的文章裡有一種少見的窮究事理的憨厚笨拙的勁兒,加上他智商……咳咳……智商確實高。
六哥說過,好東西是聰明人下笨功夫做出來的。
這個笨功夫,是必須下的,急不得,急的結果都是油條式的——炸得金光錚亮出來了,都是空心的。
科學如此,媒體如此。
柴靜
記者、主持人。二○○三年爆發SARS時是最早進入疫區的記者之一,同年獲選「風雲記者」。先後擔任央視《新聞調查》記者、《面對面》主持人、《看見》主持人。二○一二年出版自傳作品《看見》,大為暢銷。二○一五年自費拍攝紀錄片《穹頂之下》,討論中國的霧霾,引發熱烈討論,但此片旋即在中國被禁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