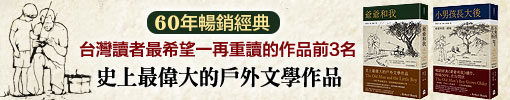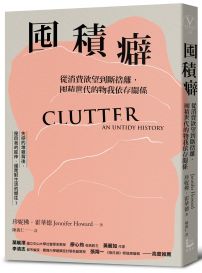前言
在我媽房子裡:一段個人囤物史
我坐在我媽房子裡的地板上,周圍都是東西。
到處都是——一堆堆、一疊疊、一箱箱和一袋袋的東西。報紙和垃圾郵件遍布於客廳的地板。一個個茶杯裡裝著數以百計的一美分硬幣、迴紋針和橡皮筋。一架十年沒彈過的大鍵琴底下,放滿十幾件褪色的檯燈。
我起身穿過災難現場,就像是個評估颶風災損的第一反應者。每個廳室都呈現一片新的慘況。客廳裡的咖啡桌散落著陶瓷杯和玻璃杯,杯底都是褐色污漬。當我拿起堆放在旁的一個披薩盒,披薩邊就像骨頭似的在盒裡格格作響。外帶中式料理在周圍那些保麗龍餐盒裡發爛,我打開一個餐盒,發現內容物已經發臭、還有在動的感覺,上邊爬著蟲。
在這個陪我們度過這麼多上學早餐和節日晚餐的餐廳裡,餐桌成了特百惠容器和空罐子的墓地。圍式門廊堆著塞滿回收物和垃圾的袋子、壞掉的椅子和沒用過的烤盤、自從一九九〇年代就廢棄的貓抓柱,讓人沒辦法從中間走過去。
廚房是衛生稽查員的噩夢。水槽裡滿是髒盤,盤子上的殘渣還有蛆蛆扭來扭去。老鼠屎灑滿了流理台,就像杯子蛋糕上的巧克力米。一打開櫥櫃,我就發現多年沒人碰的專用麵粉和乾貨明顯被老鼠啃過。一具小小的乾屍就倒在角落,命喪於我媽在屋裡到處放的毒藥盤。
***
骯髒和混亂已經滲透到每個廳室——樓上的、樓下的、閣樓、地下室。沒有哪個空間被輕易放過。在各間臥室,臨時建起的路徑得穿過書本和帳單的廊道,以及迂迴繞著成堆的衣服、毛巾和床單。為了搆到備用房間(原本是我的臥室)的層架,我得攀上一座座成袋垃圾堆成的小山,然後爬過床面這片僅存的淨空空間。我看不到我媽辦公間的地板或書桌的頂端,包括窗台,每個能用的表面都被零零碎碎給占領了,像是藥瓶、指甲剪、長尾夾、筷子、鋼筆、鉛筆、優惠券、口袋零錢、雜亂鑰匙和口香糖片。
我媽一直就是這樣生活的,而且差點因此送命,如今這都變成我要處理的問題了。隨著最初的厭惡和驚恐逐漸趨緩,前方任務的艱鉅也變得更加清楚。雜物之多讓我嚇到。臥室的壁櫥裡滿溢著阿瑪菲(Amalfi)和費拉格慕(Ferragamo)的鞋子、四十年來參加藝術盛會和首映會的正式禮服,以及一九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職業婦女的褲裝,還有箱型夾克、絲巾和大到顯眼卻不見得俗麗的金飾。我媽的朋友們以前老是讚美她的品味,還跟她說,她看起來既優雅又會穿搭。那些朋友一定很驚訝,在當前危機爆發前的幾個月裡,我媽居然開始習慣穿上我那已故繼父尺寸過大的牛仔褲和襯衫,因為她無法──或不願意──為自己洗衣服。在地下室階梯的底部,我發現一大堆髒衣服被扔下樓,任其發臭。
我發現情感圈套就像老鼠陷阱般散落在整座房子。我這輩子都覺得我媽是個謎,是個難以捉摸的存在。她確保我有吃有穿,但除此之外,她在情感上遙不可及。現在,當我挖掘她物質生活的廢墟,我卻發現種種線索,那些現地文物依稀著透露她可能是個怎樣的人。
擁有藝術家的眼光,讓她嚮往精緻而昂貴的東西。我媽之所以購物,是為了讓自己感到好一些,感到她在世界上有價值,感受到愛和表達愛。她很會送別人一些實用禮物。她以前常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些我得挖掘的雜物中有不少都是她從事各門技藝的工具。如今她都用不了了。
在我的舊臥室,她的藏書擺滿了三面牆的書架。想要翻翻書,我還得爬過一個個檔案箱、一包包塞滿針織半成品的袋子、一台舊娃娃車、一部縫紉機、一個個裝著她壁櫥已經塞不下各種藏品的鞋盒。我至少點出五百本烹飪書,很多都是介紹地中海菜肴的。其他書籍則體現出老媽「平實」的面向:教人醃製食物的書、收錄甜酸醬食譜的書、介紹新英格蘭小鎮當地美食的書。我媽以前常常像有些人買懸疑小說或言情小說那樣地瘋狂購買烹飪書,她總想要買更多,哪怕她只實際做過少數的食譜。做新菜並不是重點,她希望看到或想像迷人的食物被端進一個優雅的環境中。
其他幾組書架上的內容更令我吃驚。我兒時那些托爾金、勒瑰恩和洛伊.亞歷山大作品被換成了一堆自助書,一本本記錄下她幾十年來試圖弄懂失序情感生活的嘗試。老媽的住家位於一家優良公共圖書館的附近轉角處,但她顯少去借點什麼東西來讀,反而似乎獨力支撐著自助類書的出版產業。她買了很多書,包括談論如何應對身為酒鬼的成年子女、談論如何管控憤怒,談論如何讓婚姻行得通,也有談論如何成為一名成功的女企業家。與此同時,據我所知,她的人生也繼續原本無法預測的走勢:憤怒情緒、婚姻緊張、財務不穩。發現她的自助書藏書,讓我懷疑她是否擁有比我所知更多的自知之明。
如果是的話,那也太少、太遲了。
***
以我對我媽的認識,那禁錮她的極端囤物癖,可謂一場醞釀多年的危機。有一個初步理論是這樣的:童年的匱乏和混亂,養成了她一生都用東西來撫慰自己的強迫行為。「囤物」的習性就跟情緒混亂一樣,能夠在家族裡流傳下去,就像捲髮、藍眼睛或音樂能力那樣往下遺傳。
我媽和雜物的糾葛始於麻州伍斯特,那兒是她從小長大的地方。我媽是家中的老大,父親是個酗酒的工程師,母親是家庭主婦。她曾經告訴我,她和弟弟妹妹一人一雙新鞋要穿一整個學年。難怪她會羨慕舒茲伯利街那些富家女的手提包和時髦鞋子。然而,比起有形的事物,她一定更渴求穩定,那是跟著一對酒鬼父親和消極又愛挑剔的母親時很難獲得的。所以她找了一條出路,利用自身演奏鋼琴和管風琴的才華把伍斯特拋在腦後,在歐柏林音樂學院獲得一席之地。
小時候我很敬畏我媽的創意作風。我會在晚上入睡前聽到她在大鍵琴上練習巴赫和史卡拉第的巴洛克式複雜技巧,一串串音符就從她靈動的指尖傾洩而出。她也作畫,畫的主要是在天鵝絨深色背景前展現最佳自我的瓶花靜物。在畫布和鍵盤上,她容不下半點無序狀態。
然而,在個人生活中,我媽卻一路留下越來越多的混亂。她受不了我外婆的壓力,在非常年輕時就嫁給了我爸,那時她還沒決定要扮演什麼角色、想要什麼。這場婚姻並不持久,我五歲時,我媽就拋下了我爸。她總對我說,她離開是為了自保的不得已,但此舉擾亂了我的世界,震盪我的童年和以後。
跟我爸分開後,我媽又多了兩任丈夫、一連串討人厭的狗、好幾架大鍵琴、數百件書籍和唱片,以及超過任何人可能需要的義大利鞋。她離掉第二任丈夫,送走第三任,但鞋子和狗她都留著。此外,她還留著她所擁有過的幾乎每項物品。
我永遠不會知道我媽是否曾經停止獲取和積累。我只知道她無法或不願丟掉任何東西。她那診斷得晚、卻以十年時間蔓延心智的失智症,一定放大了她的囤積傾向。然而,在心智還完全屬於她的時候,她也從來狠不下心丟掉東西。早在疾病讓她無法克制之前,積聚幾十年的雜物就已經使她無能為力了。
她肯定知道她花了多年製造的那團混亂,總有一天要由我來清理,但她還是買買買,那一堆堆、一疊疊、一箱箱、一袋袋的數量越來越多,留給她的可居空間縮小再縮小,直到幾乎半點不剩,整間房子都塞滿了東西。
***
發生在我媽身上的事,並不完全是她的錯,不過站在她所留下的住宅廢墟,實在讓人很難諒解這點。她的故事是一部警世錄,顯示出一個關於當代美國的不堪真相:這種文化使得我們渴望那些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甚至經常忽略真正欠缺的種種,包括了愛、連結、有意義的工作、對自身以外某種存在的感知,以及對自然世界除了要開發來製造更多的資源買賣之外,還需要關懷。
美國人從生到死都聽人家說物質等於快樂,而當所買的東西沒有我們快樂,或當上一次購物的快感消退,我們就會再買更多、更多,再更多──無論那是快時尚、汽車、寵物用品或智慧型手機。消費引擎燒著寶貴的個人和環境資源,用來餵飽永遠無法完全滿足的慾望,這就是重點。一旦我們覺得自己已經到達物質滿足的程度,我們就會停止採購,那麼引擎就會停機。
消費者的集體和內在生活跟著地球一起受苦。在《我們住在焦慮星球》(Notes on a Nervous Planet,中文版由天下雜誌出版,2019)這本談焦慮的書裡,小說家麥特.海格(Matt Haig)喊出「現代生存的實體雜物和心靈碎屑。」他寫道,「在當前的世界,有著過量的一切。」那麼,我媽房子的混亂可以解讀為某種更大且更雜亂的縮影。每年都有無數的他人──兒女、姪甥、生活伴侶和遺囑執行人──在處理像我這樣的情況。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這簡直是某種過渡儀式,或者,至少是某種共同負擔。
當我穿梭在我媽密密麻麻的家當中,為了尋求舒緩和一些溫柔的指引,我讀了日本作家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暢銷書《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中文版由方智出版,2011)。在我拿起她這本書時,近藤的風潮方才席捲全美(至少也是全美的生活類記者和評論員)——這位溫和的日本整理大師多少受到神道原則的啟發,她建議讀者只要留下那些「令人怦然心動」的物件。
不過,當你從家裡清掉五十年份的沉積,「整理」一詞並不足以形容發生些什麼。當我在處理我媽的那團混亂,我才沒發現什麼東西令人怦然心動,只是勉強欣慰至少還能堅強的面對這場看似不可能的任務。結果最撫慰我的書是蘿茲.查斯特(Roz Chast)所著的《我們不能談些更愉快的話題嗎?》(Can’t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More Pleasant?)。這本 二〇一四年的插圖回憶錄,講述了她父母的衰退,以及「那般龐大、非常怪異又令人心碎的工作」──這句話完美描述了她得在兩老從舊公寓搬進輔助生活設施後,處理他們東西的經過。我不會說這本書讀起來很鼓舞人,但它讓我身處的情況,變得不那麼詭異了。
老年照護困境就跟流產一樣,只有當發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原來那比任何人告訴你的還要普遍得多。當我媽那場危機的消息傳了出去,朋友紛紛帶來自己的故事,他們提到大屋換小屋和看護照顧、財務和法律安排、痛苦的對話,也提到一些事實證明是無痛的、甚至是歡欣的長者遷移,那可是一種很少見、很難得、也很令人羨慕的經驗,那是從雜物中解放出來,而非被迫與其分離。這些朋友和我交換了個案工作者、個人整理師和垃圾清運者的名單和電話號碼。我太晚才認識到,原來有些社會服務,也許能在我媽的髒亂引發危機之前,就將她從裡面拯救出來。
不過,我還是去到哪都拖著我媽家當的重壓。當我走路或開車、工作或上健身房、坐在辦公桌或用餐,問題一個個閃過我腦海。那些問題會在夜裡吵醒我。這一切將何去何從?哪些是可以搶救的?哪些是我得拋棄的,而我又該如何把寶藏從垃圾之間分離出來呢?尤其是其中有這麼多──這麼多的雜物!──看起來都像垃圾。
***
到了某個階段,存在性的煩惱讓位給實踐性的煩惱。前進的唯一道路,就是必須先起頭。我一次次裝滿垃圾箱和回收箱,送走報章雜誌和垃圾郵件,送走沒用過的罐裝果醬和乾燥調味品。那些我繼父去世兩年後都放著沒人管的衣服,也一併送到一家在地慈善機構。至於他其餘的家當,則費時更久:他的孩子住得遠,而我不忍心扔掉他那些照片、家族文件和傳家寶,所以我只好分批寄出。這些文檔很花時間整理,但很容易發送。事實證明,要橫跨全國運送老爺鐘、管鐘和各種有的沒的,可沒那麼容易。
我不像我媽那樣,在危機闖入前拒絕一切的幫忙和好意,我才不相信我能自己應付這一切,所以我找了一位整理師來幫忙。這個人是個話少高效的女性,兼具治療師的風範和老管家的審慎。她花了好幾天翻查令人卻步的一落落紙堆,從多年份的垃圾郵件和報紙篩出重要的文件。
隨著整座紙堆森林慢慢縮小,我開始看到一條穿過所有雜物的(具體和抽象)通路隱約浮現。有些人好心地建議我甩掉這一切──直接把房子清空、賣掉就好。但是,說來容易做起來難。
這所有的東西都很久沒在市面上流通了,但至少其中有些可以再次變得有用。我緊緊抓住那個哪怕渺茫的希望,我成了一個奪命判官,非常無情的送了大批倒楣鬼上路。過程中並無歡喜可言,但清理幾十年沒人管的雜亂,倒是有種原始的愉悅感。我媽無法或不願加以處理,而我必須處理,所以我來處理。我逐廳逐室翻過整間房子。我淘汰、淘汰,再淘汰。
東西之多嚇到我了。無論我搬出多少袋垃圾和回收物,無論我跑了多少趟「好心願」,還是又有更多東西出現,拔地而起就像一支喪屍部隊。我太常開玩笑說,解決這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罐汽油和一根火柴。在那些時刻,我都很懷疑在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東西,有多少是我們真的會想念的。
垃圾清運夫法蘭克幫我度過整場淘汰賽中最慘烈的部分。法蘭克和他的組員在幾個月間多次出勤到我媽家。每次他們來,都開著一輛粉紅色卡車,這輛卡車能裝下超乎我想像多的東西。他們裝載卡車的幾何式填塞法精準到讓我想起「塞車時刻」(Rush Hour)這個遊戲,玩家必須操縱一輛汽車通過車陣,靠的是移動其他車輛來創造可以鑽過的空間。真的是寸土必爭。
法蘭克性格活潑開朗,又默默同情我,很討人喜歡。他可以是我缺少的那個兄弟。為了讓我暫時忘記丟棄東西的痛苦,法蘭克跟我講了一些故事,是關於他服務過的一些家庭,講到他們為了東西爭吵不休,哪怕他正將其搬出房子。我想,也許我很幸運,我只需要和我自己爭吵要搶救些什麼。
即使有專業人士的協助,清空我媽房子仍要花上數年時間,花上多到數不清的夜晚和週末,還有午餐時間和假期日子。要是我能從我目前的全時工作請假來做,這也會是一份全職工作。
實際上,我必須零零碎碎地做,因為那會侵蝕我可以花在我先生、我孩子和寫作上的寶貴時間。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麼艱難的事。我在大部分過程中都覺得罪惡,也很憤怒。一再而再,那感覺就像在殺掉我媽,同時也在被她消解。我無法就此質問她──失智症豁免了患者對其罹病前作為的責任──我面對一整間房子滿滿都是代表物,都是她個性和慣習的實體殘餘。
***
囤物是個很奢侈的問題,你可能很難意識到,尤其是你正淹沒在一場清理當中。在世界許多地方,人們不用跟太多的東西糾纏,而得設法憑著太少的東西求生存。當生命面臨風險,「少一點東西,多一點生活」(Less stuff, more life)這句極簡主義口號就不適用了。
當我忙於我媽生活的廢墟,歐洲正面臨一場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當我努力弄清楚我媽和她所有的東西將何去何從,那些來自中美洲的移民父母正努力讓自己和孩子來到美國避難,卻在美墨邊境被迫分離。後來,當我著手撰寫這本書,加州和澳洲的惡火吞噬了住家和社區,破壞了生態系統,毀掉了很多人幾輩子的財產。當我完成這本書,一種致命病毒正在大流行肆虐全世界。
死命逃避暴力、疾病、天災或內戰的人,都被迫面對關於東西存在性的問題。如果得逃命,你會帶上什麼?哪些物件是真正無可取代的?我媽從未回答這個問題,而是把什麼都留著。她曾計畫要辦庭院甩賣和跑「好心願」(Goodwill),卻從未實現過。在一座有地下室、閣樓和車庫的房子裡,她總能找到角落可以存放餘物。因此只要時候一到,她就會處理她的東西。
但是,時候從未到過。對這社會上的許多人來說,時候永遠都不會到。
我想了解像我媽這樣的人,是如何成為自己物事的囚徒——還有囤物是如何成為一個大到足以催生暢銷書和電視實境秀的集體問題。對答案的追尋最終帶我在時間上往回走,回到維多利亞時人和工業主義和大規模生產的開端,然後向前走,走向消費文化的興起已經引領我們到目前的處境,走向我們可以為此而做的事。但首先,我需要更加了解個人與他們物事的關係,如何能從消費主義滑落到功能障礙,甚至病態──就像我媽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