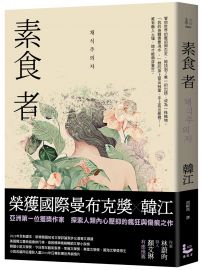妻子吃素以前,我並不覺得她是一個特別的人。老實講,初次見面時,我沒有被她吸引。不高不矮的個頭、不長不短的髮型、泛黃的皮膚上布滿了角質、單眼皮的眼睛和稍稍突起的顴骨,一身生怕惹人注目的暗色系衣服。她踩著款式極簡的黑皮鞋,以速度和力度適中的步伐朝我所在的餐桌走了過來。
我之所以會跟這樣的女人結婚,是因為她沒有什麼特別的魅力,同時也找不出什麼特別的缺點。在她平凡的性格裡,根本看不到令人眼前一亮,或是善於察言觀色和成熟穩重的一面。正因為這樣,我才覺得舒坦。如此一來,我就沒有必要為了博取她的芳心而假裝博學多識,也無需因為約會遲到而手忙腳亂,更不用自討沒趣地拿自己跟時尚雜誌裡的男人做比較了。我那二十五歲之後隆起的小腹和再怎麼努力也長不出肌肉的纖細四肢,以及總是令我感到自卑的短小陰莖。這些對她來講都是無關緊要的事。
我向來不喜歡浮誇的東西。小時候,年長的我會帶領比我小兩三歲的小傢伙們玩耍,是玩伴中的孩子王;長大後,考進了能領取豐厚獎學金的大學;畢業後,進了一間珍視我微不足道能力的小公司,並為能夠定期領取微薄的薪水而感到心滿意足。正因為這樣,跟世上最平凡的女子結婚便成了順理成章的選擇。從一開始,那些用漂亮、聰慧、嬌豔和富家千金來形容的女子,只會讓我感到不自在。
正如我期待的那樣,她輕而易舉地勝任了平凡妻子的角色。她每天早上六點起床,為我準備一桌有湯、有飯、有魚的早餐,而且她從婚前一直做的副業也或多或少地貼補了家計。妻子曾在電腦繪圖培訓班做過一年的助教,副業會接一些出版社的漫畫稿,主要的工作是給對話方塊嵌入臺詞。
妻子少言寡語,很少開口向我提什麼要求。即使我下班回來晚了,她也不會抱怨。有時難得週末兩個人都在家,她也不會提議出門走走。整個下午,我拿著遙控器在客廳打滾的時候,她都會待在房間裡閉門不出。我猜她是在工作或是看書。說到她的興趣愛好,似乎只有看書而已,而且看的都是那些我連碰都不想碰的、枯燥乏味的書。到了吃飯時間,她才會走出房間,一聲不響地準備飯菜。坦白講,跟這樣的女人生活一點意思也沒有。但看到那些為了確認丈夫行蹤,每天會打數通電話給丈夫的同事或好友,或是定期發牢騷、找碴吵架的女人們,我對這樣的妻子簡直感激不盡。
妻子只有一點跟其他人不同,那就是她不喜歡穿胸罩。在短暫且毫無激情的戀愛時期,有一次,我無意間把手放在了她的後背上,當我發現隔著毛衣竟然摸不到胸罩的帶子時,莫名地稍稍興奮了起來。難道說她是在向我暗示什麼嗎?想到這,我不禁對她另眼相看。但觀察結果顯示,她根本沒有想要暗示什麼。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難道只是因為她懶得穿,或是根本不在乎穿不穿胸罩這件事?與其這樣,還不如在胸罩裡加一片厚實點的胸墊。這樣一來,跟朋友見面時,我也好顯得有點面子。
婚後,妻子在家裡乾脆就不穿胸罩了。夏天外出時,為了遮掩圓而凸起的乳頭,她才會勉強穿上胸罩。但不到一分鐘,她就把胸罩後面的背勾解開了。如果是穿淺色的上衣或稍微貼身的衣服時,一眼就能看出來,但她卻毫不在意。面對我的指責,她寧可在三伏天多套一件背心來取代胸罩。她的辯解是,自己難以忍受胸罩緊勒著乳房。我沒有穿過胸罩,自然無從得知那有多難以忍受。但看到其他女人都沒有像她這樣討厭穿胸罩,所以我才會對她的這種過激反應感到很詫異。
除此之外,一切都很順利。今年,我們已步入結婚的第五年,因為從一開始就沒有熱戀期,所以也不會迎來什麼特別的倦怠期。直到去年秋天貸款買下這間房子以前,我們一直推遲了懷孕的計畫,但我想現在是時候要個孩子了。直到二月的某天凌晨,發現妻子穿著睡衣站在廚房以前,我從未想過這樣的生活會出現任何改變。
***
「妳站在那裡做什麼?」
我原本要打開浴室燈的手懸在了半空。當時凌晨四點多,由於昨晚聚餐時喝了半瓶燒酒,所以我在感受到尿意和口渴後醒了過來。
「嗯?我問妳在做什麼?」
我忍受著陣陣寒意,望著妻子所在的方向。頓時,睡意和醉意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妻子一動也不動地看著冰箱。黑暗中,雖然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卻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恐懼。她披著一頭蓬鬆且從未染過色的黑髮,穿著一條垂到腳踝
的白色睡裙,群擺還微微地往上捲起。廚房比臥室冷很多。如果是平時,怕冷的妻子肯定會找一件開衫披在身上,
然後再拿出絨毛拖鞋穿上。但不知她從何時開始光著腳,穿著春秋款的單薄睡衣,像聽不見我講話似的楞楞地站在那裡。彷彿冰箱那裡站著一個我看不見的人,又或者是鬼。
怎麼回事?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夢遊症?妻子像石像一樣佇立在原地,我走到她身邊。
「妳怎麼了?在做什麼……」當我把手放在她肩膀上時,她居然一點也不驚訝。她不是沒有意識,她知道我走出臥室,向她發問,並且靠近她。她只是無視我的存在罷了。就像有時,她沉浸在深夜的電視劇裡,即使聽到我走進家門的聲音也會當作看不見我一樣。但眼下是在凌晨四點漆黑一片的廚房,面對四百公升冰箱泛白的冰箱門,到底有什麼能讓她如此出神呢?
「老婆!」我看到黑暗中她的側臉,她緊閉著雙唇,眼中閃爍著我從未見過的冷光。「……我做了一個夢。」
她的聲音清晰。
「夢?妳在說什麼?看看現在都幾點了?」她轉過身來,緩慢地朝敞著門的臥室走去。她跨過門檻的同時,伸手輕輕地
帶上了門。我獨自留在黑暗的廚房裡,望著那扇吞噬了她白色背影的房門。我打開燈,走進了浴室。連日來氣溫一直處在零下十幾度,幾個小時前我剛洗過澡,所以濺了水的拖鞋還很冰冷潮濕。我從浴缸上方黑黝黝的換氣口、地面和牆壁上的白瓷磚,感受到了一種殘酷季節的寂寞感。當我回到臥室時,妻子一聲不響地蜷縮在床上,彷彿房間裡只有我一個人似的。當然,這不過是我的錯覺。屏住呼吸側耳傾聽,便會聽到非常微弱的呼吸聲,但這一點都不像熟睡的人發出的呼吸聲。只要我伸手就能觸碰到妻子溫暖的肉體,但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想碰她。甚至連一句話也不想跟她講。
***
我蜷在被子裡悵然若失,迷茫地望著冬日晨光透過灰色的窗簾照進房間裡。我抬頭看了一眼掛鐘,慌忙爬起來,奪門而出。妻子站在廚房的冰箱前。
「妳瘋了嗎?怎麼不叫醒我?現在都幾點了……」我踩到了什麼軟綿綿的東西,低頭一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妻子穿著昨晚那條睡裙,披著蓬鬆的頭髮蹲坐在地上。以她的身體為中心,
整個廚房的地面上擺滿了黑、白色的塑膠袋和密封容器,連一處落腳的地方都沒有。吃火鍋用的牛肉、五花豬肉、兩塊碩大的牛腱、裝在保鮮袋裡的魷魚、前陣子住在鄉下的岳母寄來的處理好的鰻魚、用黃繩捆成串的黃花魚、未拆封的冷凍水餃和一堆根本不知道裝著什麼的袋子。妻子正在把這些東西一個接一個的倒進大容量的垃圾袋。
「妳到底在做什麼?」我最終失去了理智,大喊了起來。但她仍跟昨晚一樣,依然無視我的存在,只顧忙著把那些牛肉、豬肉、切成塊的雞肉和少說也值二十萬元的鰻魚倒進垃圾袋。
「妳瘋了嗎?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都扔掉?」
我扒開塑膠袋一把抓住妻子的手腕。她的腕力大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使出渾身力氣才逼她放下了袋子。妻子用左手揉著被我掐紅的右手腕,用一如既往沉穩的語氣說:
「我做了一個夢。」又是那句話。妻子面不改色地看著我。這時,我的手機響了。
「媽的!」我慌忙地抓起昨晚丟在客廳沙發上的外套,在內側口袋裡摸到了正在發出刺
耳鈴聲的手機。「對不起,家裡出了點急事……真是對不起。我會盡快趕到的。不,我馬上就到。只要一會兒……不,您別這樣,請再給我一點時間。真是對不起。是,我無話可說……」
我掛掉電話,立刻衝進浴室。由於一時手忙腳亂,刮鬍子時劃出了兩道傷口。「有沒有熨好的襯衫?」妻子沒有回答。我一邊破口大罵,一邊在浴室門口的髒衣服桶裡翻出了昨天穿過的襯衫。還好沒有太多折痕。就在我把領帶像圍巾一樣掛在脖子上、穿上襪子、裝好筆記本和錢包的時候,妻子仍待在廚房沒有出來。這是結婚五年來,我第一次在沒有妻子的照料和送別下出門上班。
「她這是瘋了,徹底瘋了。」
我穿上不久前新買的皮鞋。新皮鞋穿起來特別緊,我費了好大力氣才把腳塞了進去。等我衝出玄關,看到電梯還停在頂樓時,只好無奈地從三樓跑樓梯下樓。當我衝進即將關上車門的地鐵後,這才看到陰暗的車窗上映照出自己的臉。我理順頭髮,繫好領帶,用手掌抹平襯衫上的皺褶。做完這些後,我腦海中浮現出了妻子那張令人毛骨悚然的、面無表情的臉,以及僵硬的語氣。
我做了一個夢。同樣的話,妻子說了兩遍。透過飛馳的車窗,我看到妻子的臉在黑暗的隧道裡一閃而過。那張臉是如此陌生,就跟初次見面的人一樣。然而,我必須在三十分鐘內想好該如何向客戶解釋遲到的原因,以及修改好今天要介紹的方案。因此,我根本無暇去思考妻子異常的舉動。我心中暗忖:今天無論如何都要早點下班回家,自從換了部門之後,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在十二點前下過班了。
***
「那是一片黑暗的森林。四下無人。我一邊扒開長著細尖葉子的樹枝,一邊往前走去。我的臉和手臂都被劃破了。我記得明明是跟同伴在一起的,可是現在卻一個人在這裡迷了路。恐懼與寒冷包圍著我,我穿過凍結的溪谷,發現了一處亮著燈、像是一座倉庫的建築物。我走上前,扒開草簾一樣的門走進去的瞬間,只見數百塊碩大的、紅彤彤的肉塊吊在長長的竹竿上。有的肉塊還在滴著血。我扒開眼前數不盡的肉塊向前走去卻怎麼也找不到對面的出口。身上的白衣服早已被鮮血浸濕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從那裡逃出來的。我逆著溪流而上,跑了好一陣子。忽然間,森林變得一片明亮,春日的樹木鬱鬱蔥蔥。孩子成群結隊,一股食物的香氣撲鼻而來。我眼前出現了難以形容的燦爛光景,流淌著溪水的岸邊,很多出來野餐的家庭圍坐在地上,有的人吃著紫菜飯捲,有的人在一旁烤肉。歌聲和歡笑聲不絕於耳。
但我卻感到很害怕,因為我渾身是血。趁沒有人看到,我趕緊躲到了一棵樹的後面。我的雙手和嘴裡都是血,因為剛剛在倉庫的時候,我撿起一塊掉在地上的肉,放入口中,咀嚼著那塊軟乎乎的肉,嚥下肉汁與血水。那時,我看到倉庫地面的血坑裡映照了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
我無法忘記用牙齒咀嚼生肉時的口感,還有我那張臉和眼神。猶如初識的臉孔,但那的確是我的臉。不,應該反過來講,那是我見過無數次的臉。然而,那不是我。我無法解釋這種似曾相識又倍感陌生的……既清晰又怪異又恐怖的感覺。」
***
妻子準備的晚餐只有生菜、大醬、泡菜和沒有放牛肉或是蛤蜊的海帶湯。
「搞什麼?因為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就把肉都扔了?妳知道那些肉值多少錢嗎?」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打開冰箱冷凍庫的門。果真都被清空了,裡面只有多穀茶粉、辣椒粉、冷凍青椒和一袋蒜泥。
「至少幫我煎個雞蛋吧。我今天累壞了,連午飯都沒好好吃。」「雞蛋也扔了。」
「什麼?」
「牛奶也不會送來了。」「真是荒唐無稽。妳的意思是連我也不能吃肉了嗎?」「那些東西不能放在冰箱裡,我受不了。」她也太以自我為中心了吧。我盯著妻子的臉,她垂著眼皮,表情比平時還要平靜。一切出乎我的意料,她竟有如此自私、任性的一面。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她會是一個這麼不理智的女人。
「妳的意思是,從今以後家裡都不吃肉了?」
「反正你只在家吃早餐,中午和晚上都能吃到肉……一頓不吃肉死不了人的。」
妻子應對得有條不紊,似乎認為自己的決定很理性,很妥當。「好吧。就算我不吃,那妳呢?從今天開始,妳再也不吃肉了嗎?」她點了點頭。
「哦?那到什麼時候?」
「……永遠不吃。」
我啞口無言。我知道最近流行吃素,人們為了健康長壽、改善過敏體質,或是為了保護環境而成為素食者。當然,還有遁入空門的僧人是為了遵守不殺生的戒律。但妻子又不是青春期的少女,她既不是為了減肥,也不是為了改善體質,更不可能是撞了邪。只不過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就要改變飲食習慣?而且她還徹底無視我的勸阻,固執得不可理喻!如果一開始她就討厭吃肉的話,我還可以理解,但結婚前她的食性就很好。
這也是我特別滿意的一點。妻子烤肉的技術非常嫻熟,她一手拿著鉗子,一手拿著大剪刀,剪排骨肉的架勢相當穩重。婚後每逢週日,她都會大顯身手做一桌美味佳餚,油炸用生薑末和糖漿醃製過的五花肉,香甜可口極了。她的獨門絕技是在涮火鍋用的牛肉上塗抹好胡椒、竹鹽和芝麻油,然後再裹上一層糯米粉,最後煎烤。她還會在碎牛肉和泡過水的白米裡加入芝麻油,然後在上面鋪一層豆芽,煮一鍋香噴噴的豆芽拌飯。加入大塊馬鈴薯的辣雞肉湯也好吃得不得了,滑嫩的雞肉裡飽吸了辣汁湯頭,十分入味,我一頓飯就能吃下三大盤。
可是現在妻子準備的這桌飯菜都是些什麼啊!她斜坐在椅子上,往嘴裡送著令人食欲全無的海帶湯。我把米飯和大醬包在生菜裡,不滿地咀嚼著,突然意識到,自己竟然對眼前這個女人一無所知。
「你不吃了?」她心不在焉地問道,口氣跟撫養著四個小孩的中年女人一樣。我怒瞪著她,可她卻毫不在意,嘎吱嘎吱地嚼了半天嘴巴裡的泡菜。
***
直到春天,妻子也沒有任何改變。雖然每天早上只吃蔬菜,但我已經不再抱怨了。如果一個人徹頭徹尾地改變了,那麼另一個人也只能隨之改變。
妻子日漸消瘦,原本就突出的顴骨顯得更加高聳了。如果不化妝,皮膚就跟病患一樣蒼白憔悴。如果大家都能像她這樣戒掉肉的話,那世上就沒有人為減肥苦惱了。但我知道,妻子消瘦的原因不是吃素,而是因為她做的夢。事實上,她幾乎不睡覺了。
妻子並不是一個勤快的人。之前我深夜回到家,很多時候她都上床入睡了。但現在,就算我凌晨到家洗漱上床後,她也不會進臥房。她沒有看書,也不會上網跟人聊天,更不要說看電視了,那份為漫畫加對白的工作也不可能佔用這麼多的時間。
直到凌晨五點左右,她才會上床睡覺,但也只是似睡非睡地躺一個小時,然後很快地在短促的呻吟聲中起床。每天早晨,她都是一副皮膚粗糙、披頭散髮、瞪著充血的眼睛的模樣為我準備早餐,然而她自己卻連筷子也不動一下。
更讓我傷腦筋的是,她再也不肯跟我做愛了。從前,妻子總是二話不說地滿足我,有時還會主動撫摸我的身體。但現在,只要我的手碰到她的肩膀,她就會悄悄躲閃。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了她理由:
「到底怎麼了?」
「我很累。」「所以我才說要妳吃肉啊。不吃肉哪有力氣,以前妳可不這樣。」「其實……」
「什麼?」
「……其實是因為有股味道。」
「味道?」
「肉味——你身上有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