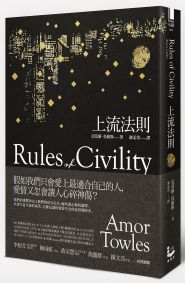前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晚上,當時都已經步入中年後段的我和法爾,去了現代藝術博物館,參加「蒙召者眾」攝影展開幕晚會。這是沃克.艾文斯(Walker Evans)首次展出這批作品,三○年代晚期在紐約地鐵上用隱藏式相機拍的人像。
社會專欄作家會稱之為「一流盛事」。男人都打了黑領結,呼應那些照片的色調;女人穿著豔燦燦的禮服,裙襬有長有短,長的至腳踝,短的至大腿上段。香檳放在小圓托盤上面,端盤子的是失業年輕演員,個個生著一副完美無瑕的俊臉,以及特技演員般優雅的體態。那些照片根本沒人看,賓客都忙著尋歡作樂。
不知怎的,不到八點就在正式場合醉醺醺,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事,甚至成了流行。
話說回來,也不是那麼難以理解。五○年代,美國把全世界從腳跟提起來甩,已經把人家口袋裡的零錢都甩了出來。歐洲成了窮親戚,牆上是掛滿了紋章徽飾,桌上卻沒有餐具;而非洲、亞洲、南美洲那些個教人分不清楚的國家,正要開始爬過我們學校教室的牆,像太陽下不怕火的蠑螈。沒錯,有共產黨,在某個地方,但是麥卡錫已經進了棺材,沒有人上過月球,現下俄國人神出鬼沒還只是在間諜小說裡。
所以我們或多或少全都醉了。我們把自己發射到這個夜晚,像是衛星,繞著離地二哩高的城市轉,崩潰的外幣和精濾的烈酒為這座城供應電力。我們隔著餐桌喊叫,帶著彼此的配偶溜進空房間,痛快暢飲、隨意喧鬧,像希臘神祇那樣不知節制。到了早上,我們準時在六點三十分醒來,神智清明,樂天開朗,準備好回到工作崗位,在不鏽鋼辦公桌後面掌著全世界的舵。
那晚的聚光燈並不是打在攝影家身上。
大家的目光焦點都不是艾文斯,大家都看著一個頂上稀疏的年輕作家,這人剛剛寫了自己母親外遇的情史,大為轟動。他讓他的編輯和公關一左一右護著,接受一群書迷讚美奉承,像個狡黠的新生兒。
法爾好奇地看著那群馬屁精。他爾靠著推動瑞士連鎖百貨與美國飛彈製造商的合併案,一天就可以賺進一萬元,卻完全無法理解一個長舌夫怎麼能引起這麼大的騷動。
那位公關時時留心著周遭,正好與我四目交接,便招手要我過去。我速速揮了揮手,就攬住我丈夫的手臂。
——來吧老公,我說。我們去看那些照片。
我們走到沒那麼擁擠的第二間展覽室,開始沿著牆慢條斯理逛了起來。幾乎所有照片都是橫幅構圖,拍攝坐在攝影者正前方的一兩位地鐵乘客。
這裡是一個嚴肅的哈林區青年,頭上圓頂禮帽歪得很大膽,蓄著兩撇八字鬍。
這裡是一個四十歲眼鏡男,穿戴毛領大衣和寬邊帽,一看就是幫派會計師的模樣。
這裡有兩個單身女子,梅西百貨香水櫃員,著實有三十多歲,自知金色年華已逝而臉色微慍,眉毛一路拔到布朗克斯區那麼遠。
這裡一個他;那裡一個她。
這裡年輕;那裡老。
這裡光鮮亮麗;那裡單調灰暗。
這些照片雖然拍了不只二十五年了,卻從來沒有公開展覽過,艾文斯顯然顧慮著影中人的隱私。這聽起來可能很奇怪(甚至有點自以為是),想想看,照片是在這麼公開的場合拍的嘛。可是看著他們的臉排列在牆上,你就會理解艾文斯的為難,因為照片事實上捕捉了赤裸裸的人性。許多人戴著無名通勤者的面具發呆,渾然不察有具相機直直對著自己,不知不覺中暴露了自己的內在。
一天搭兩次地鐵上下班求溫飽的人,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上車的時候,你戴著面對同事舊識的面具;那副面具你已經一路戴著通過旋轉閘門、穿過車廂滑門,讓同車的乘客看得出你是什麼樣的人——趾高氣昂或是小心謹慎,春心蕩漾或是冷淡漠然,荷包滿滿或是靠人救濟。可是你找到位子坐了下來,列車開動,停過一站又一站,乘客來了又去了,在列車搖籃似的晃動之下,你那副仔細雕琢的面具開始滑脫,思緒漫無目標地飄過你的憂慮和你的夢想,你的超我隨之慢慢溶解。更棒的是,思緒飄進一團包圍著你的催眠狀態,連憂慮和夢想都退去了,宇宙的祥和寧靜充滿其間。
在不知情的人眼裡,這場攝影調查一定教他們很滿意吧,那些年輕律師和新進銀行主管和神采奕奕的交際花,他們逛過一間間展覽室,一定是看著照片心裡想:真是精彩巨作,多麼高的藝術成就呀,我們終於看到人性的面貌!
但是攝影當時正年輕的我們,如今見到這些影中人,卻像見到鬼魂。
一九三○年代……
多折磨人的十年啊。
經濟大蕭條開始的時候,我十六歲,年紀正好夠了,夠讓我所有的美夢與期望都被二○年代唾手可得的繁華給騙了。當時彷彿經濟大蕭條是美國刻意推出的政策,就只是為了給曼哈頓一個教訓。
股市崩盤結束以後,你不會再聽見人體撞擊人行道的聲音,但大家好像一起喘了一口大氣,接著寂靜就降臨整座城,像雪一樣漫天蓋地。燈光一明一滅,樂隊放下他們的樂器,觀眾安靜地朝門外走去。
接著風向變了,西風轉成東風,把奧克拉荷馬打工仔的沙塵一路吹回四十二街。風吹沙滾滾翻騰而來,落在書報攤和公園長椅上,覆蓋了蒙福的人和被詛咒的人,像是埋住龐貝的火山灰。
是呀,一九三八年到四一年間沃克.艾文斯用隱藏式相機拍的肖像,是呈現了人性沒錯,不過是某一種特別的人性,向磨難低頭的那種。
我們前面幾步有個年輕女子正在欣賞展品,她頂多二十二歲,每張照片好像都是驚喜,好像她身處城堡中的肖像畫廊,裡頭的臉孔全都莊嚴而陌生。她的皮膚泛起紅暈,散發出不自覺的美麗,教我滿心嫉妒。
我不覺得那些臉孔陌生。那些疲憊的表情,得不到回報的凝視,都太熟悉不過。就好像你有過的那種經驗,你走進另一個城市的旅館大廳,看見其他客人的衣著舉止跟你如此相像,你一定會撞見某個不想撞見的人。
說起來,那天正是如此。
——是錫哥.古瑞欸,我說。法爾正走向下一張照片。
他走回我身邊,再看了一眼。照片中的二十八歲男子鬍子沒刮乾淨,穿著破舊大衣。
看起來體重不到標準,少了二十磅,兩頰的紅潤也幾乎不見,臉上看得出來很髒。但他的眼睛炯炯有神,靈敏機警,而且直盯著前方,嘴角一抹極不顯眼的微笑,彷彿正在觀察攝影者;跨過三十年的凝視,跨過無數的邂逅,像是前來探訪,而且每一寸都像他自己。
——錫哥.古瑞。法爾複述一遍,印象模糊的樣子。我弟弟好像認識一個叫錫哥的,在銀行業……
——對,我說。就是他。
這次法爾更仔細研究照片,對受困逆境的點頭之交展現出禮貌上該有的興趣。不過他一定要冒出一兩個疑問來的,他會好奇我認識這男人多深。
——真是奇了。法爾只說了這句,並且非常不明顯地皺了下眉頭。
我和法爾開始約會的那個夏天,兩人都還只有三十多歲,錯過彼此的成人歲月頂多十年。但是十年夠長了,足夠每個人去過活度日、去誤入歧途;夠長了,像詩人說的,足夠時間去謀殺,去創新,或至少保證有疑問掉進你的盤子裡。
但是法爾不太覺得向後看是什麼美德,關於我過去的祕密,關於其他好多事,他都以紳士作風為優先。
儘管如此,我讓步了。
——我也認識他,我說,有一段時間在同一個朋友圈裡,不過戰前我就沒聽過他的消息了。
法爾的眉頭舒展開來。
或許這些小小事實表面上的單純安撫了他,他更仔細研究照片,還搖了搖頭。短暫的搖頭動作既給了這次巧遇該有的反應,也是鄭重表示大蕭條有多不公平的意思。
——真是奇了。他又說一次,這次多了點同情味道。他挽住我的手臂,輕輕地拉我前進。
我們在下一張照片前面站了該有的一分鐘,然後下一張,再下一張。但那些臉像是反向電扶梯上的陌生臉孔,一張一張過去,我幾乎沒看進心裡。
看見錫哥的笑容……
過了這麼些年,我全無準備,感覺猝不及防。
或許只是我自滿——一個曼哈頓中年有錢人毫無根據的欣然自滿——但是穿過博物館裡一扇又一扇門的我,甚至願意發誓作證,我的人生已經達到平靜;我的人生是兩個人心性的結合,兩個都市靈魂的結合,緩慢而無可避免地向未來傾轉,就像向日葵轉向太陽。
然而,我發現自己的思緒探向了過去,轉身背對現時千錘百煉而來的圓滿,反而去搜尋已逝的一年間甜美的無常,搜尋那一年所有的邂逅——那些邂逅在當時看起來如此偶然無序,如此生氣蓬勃,隨著時間過去,卻變得有些命中註定的味道。
是呀,我的思緒飄向了錫哥,飄向了伊芙,但是也飄向了華勒斯.渥卡特和迪奇.范德淮,還有安妮.戈藍登。我也想起了那些萬花筒轉呀轉呀,給了我的一九三八年形形與色色。
我站在丈夫身旁,發現自己忙著把那一年的回憶留在自己心裡。
並不是那些回憶太可恥不堪,會嚇著法爾,或威脅到我們婚姻的和諧。正好相反,要是我和法爾分享,我說不定會更喜愛他。但是我不想分享,因為我不想稀釋了那些回憶。
最重要的是,我想要獨處。我想要踏出照在身上炫目的光圈,我想要去飯店酒吧喝一杯。不如搭計程車去一趟再也沒去過的格村吧,都多少年了……
是呀,照片裡的錫哥看起來很窮。他看起來貧窮,飢餓,前途無望。但是他同樣看起來年輕,活躍,而且奇怪地充滿生氣。
突然間,牆上那些臉孔彷彿在看我。地鐵上那些鬼魂,疲憊孤單的他們,在觀察我的臉,留意我臉上妥協的痕跡,那些痕跡給人類老化的五官抹上特有的悲涼感。
然後法爾嚇了我一跳。
——我們走吧,他說。
我抬起眼,他笑了。
——走嘛,等哪天早上沒這麼多人再回來看。
——好。
展覽室中央很擁擠,我們於是靠著牆邊走,走過那些照片。一張張臉孔快閃而過,像在最高戒備牢房裡的囚犯,一個一個從門上的小方窗往外望。他們的眼神緊跟著我,彷彿說著:你以為你逃得了?而後就在我們走到出口之前,其中一張臉擋下了我的腳步。
我的臉上浮現苦笑。
——怎麼了?法爾問。
——又是他欸。
牆上兩幅年長女性的肖像中間,夾著錫哥的第二張照片。錫哥穿著喀什米爾羊毛大衣,沒留半點鬍碴,領帶打了個俐落的溫莎結,搭在訂製襯衫的領子上頭。
法爾拉著我的手往前站,只離照片一呎。
——你是說跟剛才那張同一個人?
——對。
——不可能吧。
法爾走回第一幅肖像。我望向展覽室那一頭,能看到他仔細地研究那張髒兮兮的臉,尋找特徵。
他走回來,站回原來的位置,距離穿著喀什米爾大衣的男子一呎。
——不可置信,他說,就是同一個人!
——請往後退離開藝術品,保全人員說。
我們往後退。
——不知道的人,會以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是呀,我說,你說得沒錯。
——嗯,他顯然是東山再起了!
——不是,我說,這幅比較早。
——什麼?
——另一幅比這幅晚,另一幅是一九三九年拍的。
我指向說明牌。
——這一幅是一九三八。
不能怪法爾弄錯會假定這一幅比較晚,是很自然的事,不只是因為展品排序在後的關係。
一九三八這一幅的錫哥看起來不只是日子比較好過了,年紀也好像比較大,臉比較圓,有一絲務實的厭倦俗世的味道,彷彿一連串的成功裡頭夾帶了一兩樁醜陋的真相。一年後拍攝的照片看起來比較像承平時期的二十歲男子,生氣蓬勃,無所畏懼,天真爛漫。
法爾為錫哥感到難為情。
——哦,他說,真是遺憾。
他又挽住我的手,為錫哥搖了搖頭,也為我們大家。
——鳳凰變麻雀,他輕聲說。
——不對,我說,不見得。
紐約市,一九六九年
1友誼萬歲
一九三七年的最後一夜。
沒有更好的計畫,沒有新年新希望,室友伊芙拖著我去了「新潮俱樂部」,一家取了個一廂情願的店名、深入格林威治村地下四呎的夜總會。
伊芙是那種來自中西部令人驚豔的美女。
人在紐約,你很容易假定城裡最有魅力的女人都來自巴黎或米蘭,其實她們只是少數,更大一群來自字母I開頭幾個身強體健的州,像是愛荷華、印第安納、伊利諾。這些原始金髮美女的生長環境有適量的新鮮空氣,適量的打打鬧鬧,適量的無知;她們從玉米田出發,看起來就像有手有腳的耀眼星光。初春的每一天早晨都有其中一個跳下門前陽台,帶著玻璃紙包的三明治,準備向第一輛開往曼哈頓的灰狗巴士招手。曼哈頓,這座城歡迎所有美麗的事物,打量一番之後,就算不立刻納為己有,至少也會試試合不合身。
伊芙來自印第安納財富階級的上層。她父親有公司車載去上班,她早餐吃的是黑人莎蒂在食品室切的軟烤餅。她上過兩年淑女學校,在瑞士待過一個夏天假裝學法文。但是如果你走進一間酒吧初次見到她,你會無法分辨,她是玉米餵大的女孩來釣金龜婿呢,還是富家千金出門狂歡;你能確定的只有一件事:她是道道地地的美女。因此,要跟她熟起來,可以少了很多複雜的工夫。
伊芙有一點值得稱讚,她在紐約是老老實實靠自己努力。一九三六年她到了這裡,帶著父親的錢,足夠在馬汀革太太寄宿公寓租一間單人房;還帶了足夠的父蔭,在潘布洛克出版社找到了行銷助理工作,促銷那些學生時代避之唯恐不及的書。寄宿公寓的第二晚,她在餐桌邊坐下時不小心翻倒盤子,她的義大利麵正中我的大腿。馬汀革太太說除漬最佳良方就是用白酒浸泡,所以從廚房拿來一瓶夏布利白酒,讓我倆都到浴室去。我們在我的裙子上灑了一些白酒,剩下的全坐在地板上背靠著門喝光。
伊芙一拿到第一張薪水支票,就搬出單人房,也不再從父親的帳戶開支。伊芙自食其力幾個月後,爸爸寄來一個信封,裡頭裝著五十張十元鈔,還有一張溫馨小紙條,說他有多麼以她為榮。她把錢寄回去了,好像上面沾了結核桿菌一樣。
——要我躺在什麼下面都可以,她說,只要不是別人管東管西的大拇指就行。
所以我們一起省吃儉用。我們把寄宿公寓供的早餐吃得一粒不剩,中午就餓肚子;我們跟其他同一層樓的女孩交換衣服穿,幫彼此剪頭髮。週五夜晚我們讓不想吻的男孩請我們喝酒,吻幾個不想再吻一次的男孩換來一頓晚餐。偶爾在下雨的星期三,班德爾精品百貨擠滿了有錢人家的太太,伊芙會穿上最好的襯衫和外套,搭電扶梯到二樓,把一雙雙絲襪塞進自己的襯褲裡。我們遲交房租的時候,她也盡了力:她站在馬汀革太太的房門口,流下五大湖不帶鹹味的淚水。
‧‧‧
那個除夕,我們打定主意只靠三塊錢儘可能拉長那一夜。我們懶得跟男孩混了,一九三七年我們已經給了不少人機會,最後幾個小時不打算浪費在遲到的人身上。我們準備待在這間店租便宜的酒吧裡,這裡的音樂算是值得認真聽,所以兩個漂亮女孩不會受到打擾;琴酒算是便宜,所以我們可以每個小時點一杯馬丁尼。我們打算多抽幾根菸,稍微超過文明社會允許的分量。一等什麼慶祝活動都沒有地過了午夜,我們就要去第二大道上的一家烏克蘭小館,那裡的深夜特餐有咖啡、有蛋、有烤土司,只要你五十分錢。
但是才過九點半不久,我們就喝掉了十一點的琴酒;到了十點我們把蛋和烤土司也喝掉了,兩人身上只剩四個五分鎳幣,什麼都還沒吃。是時候開始即興演出了。
他就是在這個時候踏進俱樂部。
伊芙先看到他的。她原本向著舞台,為了議論幾句,把視線轉了回來,因此越過我的肩膀看到了他。她踢踢我的小腿,朝他的方向點了點頭。我把椅子轉了個方向。
他長得十分好看,挺拔的五呎十吋,打了條黑領帶,大衣披在手臂上;褐色頭髮深藍色眼睛,臉頰中央泛著星狀的紅暈。你可以想像他的祖先站在「五月花號」的舵柄旁,發亮的眼睛盯著地平線,鹹鹹海風吹得頭髮微捲。
——我要了,伊芙說。
他站在門口好位置,先讓眼睛適應陰暗,再掃視店裡的客人。顯然他來這兒找人的,一發現人不在,臉上便微微浮現失望的表情。他在我們隔壁桌子坐下,再看了一遍整間屋子,接著,他向女侍示意,又把大衣披在椅背上,動作一氣呵成。
他點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語氣極為親切禮貌,展現的敬意稍稍多過女侍應得的分。然後他靠到椅背上,開始觀察環境。但是他的視線從吧台移到樂隊的時候,瞥見了伊芙,她還盯著大衣看。他紅了臉,他剛才太專心環視室內、向女侍示意,竟然沒發現拿來披大衣的椅子是我們這邊的。
——真抱歉,他說,我太沒禮貌了。
他站起來伸手要拿。
——不會不會,一點都不會,我們說,這裡沒人坐,沒關係。
他停下動作。
——確定嗎?
——千真萬確,伊芙說。
女侍帶著威士忌出現,轉身要走的時候,他請她留步,然後提議各請我們一杯——舊年最後一次做好事,他這樣說。
我們已經看出來這人高貴,優雅,乾淨,像他的大衣一樣。他的言行舉止帶著那種特殊的自信,對周遭環境一視同仁的興趣,還有那種含蓄的假設,假設別人都會親切友善;這些只有在生長環境富而好禮的青年身上,才看得到。這種人沒想過自己在新環境不見得受歡迎,因此,他們很少不受歡迎。
一個男人沒人作伴,請了兩個漂亮女孩喝酒,這種情形下,你會認為不論他在等誰,應該都會想要搭訕聊一聊。但是我們這位大善人沒有,他舉杯向我們友好地點頭致意後,就開始啜飲威士忌,注意力放到了樂隊上。
兩首曲子過後,伊芙開始坐立不安。她一直瞄他,希望他能說說話,什麼都好。有一次他們四目交接,他禮貌地笑了一下。我看得出來,等這首曲子結束,伊芙就要主動找話說了,就算得把手上的琴酒翻倒在他大腿上,也在所不惜。但是她沒等到機會。
曲子結束,一個鐘頭以來薩克斯風手第一次開口說話。他用當牧師也不為過的低沉嗓音,長篇大論講起下一首曲目。這首曲子是新作品,獻給一位人稱「銀牙霍金」的鋼琴手;他在音樂家聚集的錫鍋巷打天下,三十二歲英年早逝。這首曲子講的是非洲什麼的,曲名叫〈食錫魔〉。
他綁緊了鞋套的雙腳踏出一段節奏,鼓手在小鼓上複習一遍,接著低音提琴和鋼琴加入。薩克斯風手聽著同伴的樂聲,跟著節奏點頭。他用一小段活潑的旋律融入樂聲,像是馬兒在拍子的畜欄裡小跑步。接著他開始粗聲喧嚷,好像馬兒受了驚嚇,瞬間跳出圍欄。
我們的鄰桌客人看起來好像觀光客在向憲兵問路。他正好對上我的目光,特地為我做了個困惑的表情。我笑了出來,他也對我笑。
——那裡頭有旋律嗎?他問。
我把椅子靠過去一些,假裝聽不清楚。
——什麼?
——我不知道那裡頭有沒有旋律。
——旋律出去抽菸了,很快就回來。不過我以為你不是為了音樂來的。
——這麼明顯?他靦腆地笑問。其實我是來找我家兄弟的,他是爵士迷。
從桌子這一頭我都可以聽見那頭伊芙的睫毛在拍動。喀什米爾羊毛大衣,加上兄弟組新年約會,女孩兒還需要多問嗎?
——等他的時候,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坐?她問。
——哦,我不想叨擾二位。
(出現了,我們平常不會聽到的詞彙。)
——你怎麼可能叨擾,伊芙責備他。
我們挪了個位置給他,他把椅子拉過來。
——錫奧多.古瑞。
——錫奧多!伊芙大呼小叫地喊著,連羅斯福都要人家叫他泰迪了。
錫奧多笑了。
——我的朋友都叫我錫哥。
這不是很好猜嗎?那些上流社會新教徒就愛用普通人的行業給孩子取小名,錫哥啦,箍伯啦,鐵男啦。或許是為了回首聆聽他們十七世紀在新英格蘭一步一步踩出的靴帶聲——那些手工業把他們打造成堅定謙遜的人,他們的上帝眼中善良貞潔的子民。或者,也可能只是一種出於禮貌的輕描淡寫,刻意不突顯他們天生的好命。
——我是伊芙琳.羅思。伊碧說,帶她的本名出來兜了兜風。這位是愷蒂.康騰。
——愷蒂.康騰!哇,所以你現在滿意嗎?[註]
——才不,再乾一杯看看有沒有機會吧。
[註]:愷蒂的姓是Kontent,發音同字義為「滿意」的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