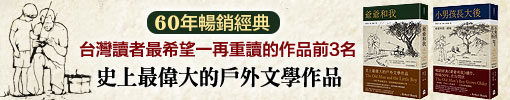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這個世界還年輕
◎楊富閔(作家)
閱讀C.S.路易斯的經典之作《納尼亞傳奇》,我的腦袋始終浮現燈野地的畫面。那一陰錯陽差來到納尼亞的鐵桿,植栽深根於納尼亞的沃土,最後竟長成了一座起引與照明的燈座。燈座在小說中具有接駁故事的符號意義,它是廣袤地圖上一個不容忽視的亮點,而你看燈野兩字多麼立體,視線像被拉得既深且遠,但它的暖光令人安心,同時也引領作為讀者的我,彷彿一同走入納尼亞的世界,或許森林深處、瀑布岩壁,就要與阿斯蘭不期而遇。
然而除了燈座,留在納尼亞世界的物件至少還有四件大衣,以及愛德蒙的手電筒等,我始終在想它們最後去了哪裡,是否也會擁有自己的獨特生命,長出了自己的故事。這看似小說家的千里伏筆,卻也是閱讀納尼亞傳奇最有趣的地方。讀者始終得以同步參與故事的行進,我們宛如跟著說書人一同觀看世界在你眼前發生,看著露西走進了魔衣櫥,看著大浪沖出畫框,跟著尤斯塔斯驚慌失措,看著小說家為我們架設起了一座又一座目眩神迷的嶄新世界,並讓「世界」述說它自己的故事。讀者聆聽納尼亞的傳奇故事,與不同主人翁一同陷入兩難,一同領受驚喜,一同看見阿斯蘭。
換言之,納尼亞系列得以分而讀之,彼此之間卻又交綰呼應,如此動態的結構設計,與小說家在空間與時間的匠心擘劃密不可分。文本處處盡是進入納尼亞故事的入口,小說家卻始終留下一個席次要給作為讀者的你我,如《最後一戰》寫著:「他們在納尼亞的所有冒險,都只是封面與書名頁而已。現在,他們終於開始了『偉大的故事』的第一章,而這一章是世上不曾有人讀過的。它將永遠持續下去,且一章比一章精彩。」《納尼亞傳奇》這部在全球創下無數傲人成績的曠世巨作,儼然形成了一套獨屬於納尼亞的閱讀模式,作為讀者的你我經由小說家的引路,也在納尼亞的世界且看且讀,那些純真與勇敢的冒險故事、關於背叛與信任的反覆辯證。我們從納尼亞世界獲得的,留在內心世界的,必然也會長出什麼吧。
比如化身而龍的尤斯塔斯,以龍爪所寫的字,卻屢屢被拍打上來的潮水沖毀,他的日記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又比如可尼斯博士告訴凱斯賓國王的話:「你必須非常勇敢。你必須獨自啟程,立刻就走。」每個讀者幾乎得以蒐羅整編而出一本納尼亞語錄。而那意外到訪人類世界的女王,脫口而出的那句「你們的世界比較年輕」,在我按著次序的閱讀過程,同樣不停來回盤旋在我的腦海。「世界」作為納尼亞傳奇的關鍵字,珠玉般散落在七本小說的字裡行間。而作為問世於二十世紀五○年代的《納尼亞傳奇》,令人想到「世界」意義在當今此刻,是否業已存在更多解讀意涵了呢?這個世界還年輕,我相信,於是我聽見阿斯蘭的嘶吼,而燈野之地持續放出光芒。
■我讀《納尼亞傳奇》
◎安石榴(童話作家)
第一次讀這套書時我相當年輕,但很可惜那時我不是孩子了,這是我很遺憾的地方,如果能有一個重來的人生,我盼望在十歲以前讀過它,好讓我在往後的生命裡拓印下納尼亞曾有的光輝與危機,它的創生與它的結束。
我很好奇,十歲以前的我會怎麼讀它。如同王爾德童話深深影響我(我十歲以前的故事書),納尼亞傳奇會對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會長成什麼樣的成人?會是那個從小就想長大,長大後想永遠停留在某個階段的蘇珊(她最後忘了納尼亞),還是那個爽快、孩子氣的露西?但我實在不敢也不願相信愛上納尼亞的孩子最終會長成蘇珊一樣的成人;除非,讀的時候就認為它是個傻氣的冒險故事而且沒有什麼寓意,但我想這樣的人應是非常少的。
我初讀它的時候,發現書頁裡充滿了意義,覺得自己快被壓垮了,所以我從沒把它當冒險故事看;也因此我真好奇,小時候的我會怎麼看它,如果王爾德童話用華麗的形式揭示給我生命的苦難與苦難的昇華,那麼納尼亞傳奇會揭示我什麼。可惜,這個問題永遠得不到答案了,因為我初讀它的時候已接受過基督教的洗禮,所以我自然的一讀就知道「阿斯蘭的九個名字」其中一個便是耶穌。即便如此,《獅子•女巫•魔衣櫥》裡阿斯蘭代替背叛的愛德蒙受死,接著死而復活,納尼亞那個世界發生了與我存在的世界曾經發生過的類似的事件,讀到此,心中仍激動不已,甚至更激動,因為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而且不是重述耶穌的受難,而是栩栩如生的以阿斯蘭之名、以獅子的形象而非人的形象、因不相同的情況,阿斯蘭自願赴死,以免了愛德蒙的債。
但我內心也知道耶穌只是阿斯蘭的其中一個名字,耶穌並不完全等同阿斯蘭,耶穌在我們的世界,阿斯蘭在納尼亞,納尼亞不是我們這個世界。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因此海外大帝不是上帝,愛德蒙不是出賣耶穌的猶太,能言鼠銳脾氣不是使徒彼得,甚至,黎明踏浪號的遠航不是水手辛巴達的航海冒險也不是奧德賽的重述;《魔法師的外甥》裡善良的馬車伕的歌聲引起阿斯蘭的回應導致納尼亞的創生,也與聖經《創世紀》記載這個世界的誕生大不相同,納尼亞結束的方式也與《啟示錄》描述的末日不同。因此,C.S.路易斯並不是用象徵性的寫法把這個世界代換成納尼亞,不是這樣的,他其實是發現了另一個世界;如同他自己曾說過的,他先是看到情景,「先有形象才有文字」。或許我們可以說,劉易斯瞥見了那個世界的某些情景,他努力的看清那些情景,寫下它們,就像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哥倫布繪製了新大陸的地圖,到過的地方精確,沒到過的地方模糊;然而路易斯是文學家,他以他的筆與奇異的思想,從瞥見的幾些場景裡仔細的推敲、構思出一個有始有終的、精確的世界。
這個精確的納尼亞,不禁讓我沉思:當個理智的現代人是多沒意思啊,是不是現代人類的理智與現實主義,把樹精、水精、獨角獸、飛馬、會說話的動物等等擠壓到別的世界去了。我們內心真的相信只有我們存在的這個世界嗎?我們有把握在另一個時空的地球還是圓的?那裡的星星不是「成分」而已,而是某種生靈?如同最終部《最後一戰》──那些陸續到過納尼亞的七個孩子(有幾個已經長大或是成了老人)死於火車車禍後立即去到了阿斯蘭的世界──我們內心真的相信只有現在活著的生命,死後沒有另一個生命?如果路易斯瞥見的是某種真實呢?而文學不僅僅只是舞文弄墨的文學呢?藉著作家的筆所描繪出來的世界與精神,有沒有可能比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更加真實(或是一樣真實),還是皆為某個真實世界的複製或者倒影?
對我來說,納尼亞傳奇轟頂而來的都是不得不讓人在有生之年需要深思的問題,這些問題關乎一個人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活過此生,最終面對無可迴避的死亡。也許對理智的成人來說,他會自覺年紀大到不好意思再讀童話故事了,可是我總覺得成人並非那麼純粹的成人,他的內在總有些部分還是個孩子,也會在某個年紀之後漸漸轉回孩子(這是幸福的),那麼他就會像路易斯所寫的:「總有一天,你會長大到一個重新開始閱讀童話的年紀。那時,你可以將這本書從書架上拿下來撢去灰塵……」然後任思緒在書頁間漫遊,禁錮我們頭腦的思維習慣便會開始逐一鬆脫,讓意識更流動,也能探索別的層面,我們可以變得深愛我們的世界而非緊抓不放,然後,我們或許能嘗到一丁點自由自在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