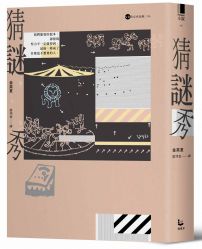我又想起智媛,可是那一瞬間,我的腦海裡突然浮起一個好主意,只要登入我和她見面的聊天網站,就可以確認其他會員的簡介。就算查不到地址和電話號碼,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會公開自己的電子郵件資訊。我立即起身打開筆電。我為什麼到現在為止都沒想過這個方法?只是這樣發呆,躺著等電話,為什麼不若無其事的寫封電子郵件給她……?那天平安到家了嗎?我也平安到家了;我非常愉快,妳呢?有空的時候打通電話給我;如果妳使用MSN,請告訴我妳的ID之類的。寄出這樣的電子郵件,她應該不至於把我視為可悲的懦夫吧?
電腦啟動後,我立刻打開瀏覽器,連結到聊天網站。找出她的ID並不困難,簡介出現後,她的電子郵件信箱也隨之出現。不只電子郵件,還可以發送站內訊息,但如果對方沒有同時登入聊天網站,訊息也無法送出。我決定要寄電子郵件給她,複製了她的信箱地址之後,打開郵件程式。程式一打開,過去沒有確認的信件一一堆積在「收件匣」裡。我習慣性按下「收件匣」的信件,結果大吃一驚,急忙把頭緊貼在螢幕前面。在幾封垃圾郵件中間,寄信人為「牆裡的妖精」的郵件夾雜在裡頭。因為我全然沒想到她會寄電子郵件給我,心裡反而有種不祥的預感。
為什麼知道我手機號碼的人會寄電子郵件給我?滑鼠游標雖然已經抵在郵件主旨上,我卻猶豫不決,無法按下。但最終我還是按下了滑鼠,不一會,電子郵件的內容就出現在畫面上。
你好!
嚇了一跳吧?我不是騷擾者,只是無意中按下你的簡介,上面有電子郵件信箱,不經意點了一下,Outlook就彈了出來。嗯,我覺得這個方法也很好,所以就寫信給你了。讀小學的時候,我曾經在學校前面的文具店買了幼稚的粉紅色信紙,在上面寫了各種不像話的內容到處寄送。可是現在在電子郵件上寫信都覺得很不自然了。我覺得電子郵件也像當年的粉紅色信紙一樣,已經變成極其久遠的媒介了。首先要寫得很長,還要依循某種形式,一開始還要提到天氣如何如何。
可是我為什麼選擇寫信?我也突然好奇起來,是不是女人的心裡永遠都存在如此的欲望?想要給誰寫長信的那種欲望。
你知道一個叫伊迪絲.華頓的美國女性作家嗎?哈哈,我好像已經看到你為了尋找答案而動著腦筋的樣子。對,就是那個寫下《純真年代》的人,她的小說裡有這樣的句子:
「女人這種存在就好像是滿是房間的宅邸,裡面有著供人們穿梭的走道,也有著接待客人的會客室,還有家人共度的客廳。可是走過這些房間以後,另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房間。誰都沒有摸過門把,甚至不知道有這些房間存在,就算知道,也不知道如何進去。這些房間當中最深邃的房間裡,在那個最神聖的地方,靈魂在此獨坐,等候永遠不會到來的某些腳步。那正是女人的本性。」
我非常喜歡這段文字,我也不太清楚我內心最深的角落有著什麼樣的房間?即便如此,我似乎在那裡面等待著某人。可是當那個人真的出現的時候,我是不是能認出他?也許我會坐在永遠不為人知的深邃房間裡思考這個問題。
你一定會認為我很愚蠢吧?是的,我好像有點愚蠢,我現在終於知道了我寫這封電子郵件的理由。正是因為我的愚蠢,正是因為見面的時候我不能說出如此愚蠢的話所致。見面的時候,彼此要微笑,要聽音樂,還要喝啤酒。於是,有些事情變得理所當然,最後一切也都變得沉悶了。
我害怕我會讓你失望,我害怕有一天環視四周時,卻突然發現認識我的人、我為之敞開心扉的朋友全部離我而去。如果是這樣的話,請你現在就告訴我。我雖然喜歡你,但也熱愛現在平穩的生活,因為好久沒有這種安定的感覺了,我不希望毫無準備就為之動搖。
手機每天都有新機型上市,可供交流的機器及其速度也快速發展,為何邀請某人進入我內心最深邃的那個房間是如此困難?為何人與人之間彼此理解、接受,向對方敞開心扉仍是如此吃力?
啊!我真的不知道。期待你明智而愉快的回信。
(期待能破繭而出的)牆裡的(醜陋)妖精
看完她的電子郵件,我第一個想法是,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這會不會是巧妙的拒絕?或者溫柔的告別儀式?但是讀了幾次之後,我認為她是在小心翼翼地邀請我進入她的世界。如果真是這樣,就我而言,實屬幸運,但以邀請而言,又似乎有哪裡顯得陰暗未明。正如她引用的伊迪絲.華頓的文句一樣,我腦海裡浮起她坐在大宅邸的某個深邃的房間裡等待著我的形象,但卻又不是讓人十分愉快的畫面。那就是女性嗎?抑或是女性特有的某種自我陶醉的幻想?為了走近她們,是否一定要穿越那像似迷宮的走道和徘徊在無數的房間之間才有可能?我突然愚蠢地想起《簡愛》裡的羅徹斯特夫人,那個患有精神病的奇怪女人,因為嫉妒丈夫和家庭教師的愛情,放火燒了家裡,丈夫羅徹斯特伯爵因而失明。其實我也不明白究竟為何突然想起這個情節。
讀了太多的書,經常都會思考一些無用的東西,那就是大哥你的問題所在。光娜經常這麼說。
18
智媛的電子郵件非但沒能讓我安心,反而讓我愈發緊張。她向我提議進行一場比賽,她發的球進到我的場中,此刻該輪到我接球了,比數仍然是0:0!
這個暫且不表,到底「明智而愉快的回信」應該怎麼寫啊?我的頭皮發麻,真是奇怪,為什麼女人要將男人弄得慌亂不已之後,再從中感到喜悅?就打電話約好見面,然後喝一杯冰涼的啤酒不行嗎?
我站起來,想在房間裡走走,但房間太窄,根本沒有辦法邁開腳步。這是我在煩悶或想不出好主意的時候,經常會出現的習慣,但在這裡是必須放棄的。我又再次坐在椅子上,就在那時,隔著牆壁傳來細微的聲響。
大概是隔壁房間的女人回來了,我能聽到放下包包的聲音、脫下外衣的聲音、椅腳拖過地面的聲音。要不要把電子郵件的內容給她看看,問問她的意見?同樣都是女人,一定比我更能好好解釋(或翻譯)那封電子郵件吧?我認真地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決定還是不要這樣做比較好。
我鎮定心情,坐到電腦前,這是為了開始寫「明智而愉快的回信」。可是光第一句就比我想像中花了更長的時間。我又再次輾轉於各種入口網站,迷失在各類謠言和八卦叢林之間,將寫下第一句話的時間往後拖延。當然我不能永遠推遲下去。
我終於寫下第一個句子。
智媛:
讀完妳的信後,我一直為要如何寫出「明智而愉快的回信」苦悶不已,可是無論再怎麼想,我似乎也無法寫出那樣的回信。在我放棄了那個帥氣的角色之後,終於可以開始寫下去了。
我經常憶及在小公園第一次看見妳的情景。現在想來,我那時有些魂不守舍,不,用這種程度的詞彙來形容其實是不夠的。我的意思是說,儘管妳坐在我的身邊或面前,我還是完全想不起妳的臉孔。我很驚訝地看著妳,妳哪裡也沒去,還是坐在那裡。我看清了妳的臉孔……啊!是的,就是這張臉,這個人就是徐智媛,「牆裡的妖精」。可是當我的視線再次移開,我又完全記不起妳臉孔具體的長相,就在剛才、不過幾秒以前才看過,我就已經記不得了。妳的眼睛長得怎麼樣?眼睛大嗎?抑或是長長的鳳眼?鼻梁呢?高還是低?應該說妳長得像誰呢?那一瞬間,如果有人問我這類問題,我一定回答不出來。有人說如果右腦的特定部位受到衝擊,就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說是無法精密區分或記住別人的臉孔。也許能認出卓別林的照片,卻無法認出自己的妻子,當然,我沒有這種病,以前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情,只有在那一瞬間如此。
我也很驚訝,為什麼會這樣呢?我一直在思考其原因。也許和去尋找妻子,要把她從地獄裡帶出來的奧菲斯心情一樣吧?是不是和他終究回頭看了尤麗迪斯的理由類似?是不是妳這個人即便身處這麼近的地方,我仍不敢相信?是不是感覺妳就像幻影、幽靈一般?是不是因為如果我靠近妳、撫摸妳,妳就會像煙霧一樣消失於無形,所以我大腦裡的某個部位阻擋儲存、分類妳這個人的形象?我就像個傻瓜一樣,鎮日想著這些事情。
可是妳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打,一則再平常不過的簡訊也沒發,就這樣銷聲匿跡了。這兩天,我真的像神話裡的奧菲斯一樣,迷失在我內心的地獄裡。啊!我實在是不想再提那地獄的光景了。所以說實在話,我是恨妳的,可是在恨妳的同時,我又拚命想要回想起妳的面容。為了不要讓我更恨妳,不,至少要讓我記住我恨的人的臉孔,我們一定要見一面。妳收到郵件以後,一定要打電話給我。今天、明天都沒關係。不,有關係,事實上,我迫不及待,如果超過明天,也許我會變成和現在不一樣的人也不一定。嗚嗚。希望妳認真思考我的這個威脅(?)。
十分想念妳的民秀
ps. 我也知道「人與人之間彼此理解、接受,向對方敞開心扉」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我不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任務。如果連靠近彼此靈魂的這種冒險都沒有,那我們的人生不就太沒意義了嗎?
寫到這裡以後,我才伸懶腰、看了看錶,不覺間過了兩個小時。起初只是懷著接球的輕鬆心情,但開始寫了之後,因為沉醉於感情,似乎淪為太過於感性的信件。越讀越覺陌生,這真的是我寫的嗎?我怎麼會寫出這種文章?嗯,這封信可不能寄出,我握住滑鼠,模樣猶如尖銳箭頭的滑鼠游標滑過outlook express的工具選項上方,最後停留在電子郵件視窗上端的「X」字上,如果按下,那這封令我羞愧、陌生的信件就會彷彿一開始就不存在似的,瞬間消失無蹤。滑鼠的游標就如同瞄準獵物的長槍一般,始終執著地對準符號X,可是我並沒有點擊,游標再次移向「寄出」的選項一側,但立刻又離開那裡,在畫面上四處流竄。
我的右手從滑鼠上移開,開始敲打鍵盤,修飾電子郵件的內容。將最後一句「十分想念妳的民秀」改為「因為恨妳腦子有病的民秀」,這樣看來就更輕鬆一些,也似乎中和了上面寫的比較嚴重的內容。然後我移動滑鼠,按下「寄出」。撰寫中的電子郵件視窗好像被吸入黑洞一樣,瞬間變小,最後成為一個黑點,一個小小的殘影。費盡心力寫好的文章經由數據機和纜線輕易地飛走,我竟有些不知所措。
類似「你真的要寄出郵件嗎?」或「你有信心寄出後不會後悔嗎?」的提問完全沒有出現,當然也沒有寄出之後再次修正,或取消寄出的功能。我承受著暗暗後悔的攻擊,但是已經無法挽回了。我只能以後寫電子郵件給比爾.蓋茲,建議他研發「為膽小的人準備的Windows Vista」。
19
郵件寄出去之後,我的心裡輕鬆許多。我把書桌收拾乾淨,在上面放上白紙,然後寫下過去這幾天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情。崔女士的過世、和光娜分手、搬到考試院、在便利商店打工、參加電視節目錄影,以及和智媛見面,這段時間真的發生太多的事。可是在辛苦承受這一切的同時,我覺得自己成為比以前堅強太多的人。一想到以前的我是多麼軟弱的存在,我不得不為現在的我感到自豪。雖然沒有家人,獨自居住,但不覺間已經慢慢習慣。我也生出只要有屋頂,在哪裡都可以生活的自信感。而我進入猜謎秀的決賽,可以說向世人證明我不是傻瓜。最重要的是,我現在擁有一個可以向她敞開心扉的女朋友。這些事情都是在這個比宅配箱子大不了多少的考試院裡成就的。
現在只要賺錢就行了。
我的心裡突然煩悶起來。大學畢業時,我就像其他朋友一樣,為了就業,曾經將履歷表寄到各個公司,並且參加面試,但沒有獲得任何一家公司的合格通知。即便我的成績不低、英語實力也不差、個性也沒有問題,但每次都是如此。在第五次面試時,我終於得知真實原因。面試官在翻閲我提交的申請文件後,詢問我的家庭關係。
「我和外婆住在一起。」
「你的父母親呢?去世了嗎?」
「母親在我小時候就過世了,父親則不太清楚。」
我看到面試官們面面相覷,露出隱約的微笑。「正直是最好的對策」這句格言,至少在就業時是沒有任何助益的。
「不太清楚是什麼意思?」
其中一個面試官問道。
「就像我說的一樣,我不太清楚。」
坐在提問的面試官旁邊的人,戳了戳他的腰際,發出不要再問了的信號,他們好像對我失去了興趣。之後,他們只針對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申請者提出多樣的問題。
「好的,大家辛苦了,你們可以出去了。」
比我接受更多提問的另外兩名競爭者,表情明朗地走出房間,我原本也想跟在他們後面走出房間,但停下了腳步,再次轉身走回面試官前面。我將雙手交錯在身前,用最恭敬的態度向剛才問我問題的面試官詢問道:
「我有不明白的事想請問您,如果我想在這麼好的公司工作,應該改善哪些方面呢?」
坐在最右邊的男人燦然而笑問道:
「我們還沒決定是否聘用,為什麼一副好像好像已經落選似的呢?」
我換了一個問題。
「那麼,如果我無法順利進入這間公司,我應該改變自己哪些地方呢?請務必告訴我。」
他們悄悄地交換著視線,外表看起來好像很難堪,但內心似乎非常享受,即便如此,他們仍遲遲不答。坐在中間的男人乾脆連看都不看我,開始在他面前的白紙上寫下什麼,最後是剛才問我問題的男人回了話。
「原本回答這類問題是不行的,但考慮到我是你大學學長,所以才告訴你,你絕對不能說出去。嗯……怎麼說呢?你也知道,因為我們是金融公司,所以信用非常重要。換句話說,能不能信任這個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吸收的不是自己的錢,而是客戶的錢。」
他再次確認了我的名字之後,繼續說道:
「雖然講這個話有點失禮,可是李民秀先生在這個部分是很難獲得周遭支持的。畢竟新進職員的信用都差不多。」
他雖然很委婉地說出「周遭」這個詞,但我立刻就知道他說的是家人,特別是指父母的存在與否。
「關於那個部分我也無能為力,不是嗎?」
為了不讓我的問題聽起來太過挑釁,我特別留意語調,語尾下降,表情也十分恭順,但那並不是演技。我特別想知道這個社會是怎麼看待我這種人的。
「問題就在這裡,個人無可奈何的部分當然存在,可是那永遠是最重要的。你回家去好好想想我的話,社會就是如此:因為是女性所以受排擠;因為年紀大被炒魷魚;因為貧窮沒辦法上大學;因為是韓國人,所以受到差別待遇,諸如此類的現實。只有接受這些現實,你才能看到自己的路。背景也是能力的一部分。」
這面試官一副好像就算捅他一刀也不會流出一滴血的模樣,大發慈悲般說道。
「謝謝,我會銘記在心。」
我低頭恭敬地行了禮。坐在中間那名五十多歲男人未發一語,只是在白紙上畫圖,此時抬頭說道:
「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欣賞你的霸氣。任何人都有缺陷,只要你用這種精神生活的話,一定可以克服的。最後我再給你一個忠告。我雖然不敢肯定,但李民秀先生與其從事金融業,倒不如往銷售、業務等方面發展會更適合你,祝你順利。」
那時如果乖乖跟著其他兩名競爭對手走出面試間的話,大概一整天的心情都會很憂鬱,可是至少我問了問題,所以沒有被破壞自我的自卑感所困擾,也沒有虐待自己。不,應該說我反而產生了自信吧?雖然可能只是我自己的誤會,那一瞬間,雖然這一瞬間極其短暫,但那些面試官和我之間,似乎產生了雄性之間的友情或關聯。這應該說是求取忠告的年幼雄性,和對此產生憐惜的狡猾雄性之間,發生非常傳統的交易嗎?我感覺好像看到了這個層面。肉鬆麵包爺爺雖然也說過「這個世界不會喜歡提問的年輕人」,但那只不過是那個老傢伙的想法,我還是認為提出問題才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學習、適應社會的重要方式。
反正那之後,我就轉換跑道考上碩士班。我的人生似乎存在某種迂迴道路。這是神只為我預備的道路,是不用受到父母親信用影響的生命,那種不用受「個人無能為力的部分」所左右的生命。直到現在為止,我都還在尋找那條路究竟是什麼,可是它始終沒有出現。
現在我也沒有悠閒考慮這些問題的時間。我連和智媛見面,請她喝一杯啤酒的錢都沒有,而且還得交下個月考試院的房租。我翻遍了口袋,計算了各銀行事實上處於休眠狀態的帳戶裡剩下的錢,可是加在一起也不到五萬元。我真是鬱悶啊!真希望有誰,就像算命仙一樣的人能告訴我,「你的人生就是這樣,所以順著這條路走」就好了。
韓潔以前曾經說過:
「我們是檀君以來讀最多書、最聰明的世代,不是嗎?能說流利的外語、操控尖端電子製品也像樂高積木一樣得心應手,幾乎所有人都是大學畢業,多益分數也是世界最高水準,就算沒有字幕,也能看得懂好萊塢動作片。打字達到每分鐘三百字,平均身高也很高。至少會彈奏一種樂器,對了,你不是也會彈鋼琴嗎?閱讀量也比我們上一代多太多。我們父母那一代只要精通我剛才說的其中一樣,不,只要跟我們差不多,就可以一輩子不愁吃穿。可是為什麼現在我們都是無業遊民?為什麼大家都變成失業者啊?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們沒做錯什麼。」
我也附和著。事實上,長輩對我們這一代的印象就是不讀書、沒能力、只會玩電腦遊戲,但這完全是錯覺。真正不讀書、沒能力、外語不行、甚至沒有愛好的人,就是那天坐在面試場裡俯視著我的面試官,而不是我們。我們出生在八○年代,在彩色電視和職棒的陪伴下成長,並且在富裕的九○年代上學。讀大學的時候,去外國學過外語,也當過背包客;二○○二年世界盃足球賽時,目睹了韓國進入前四強的場面。我們這一代是看到外國人不會退縮、外國的廣告看板中能看到我國演員臉孔的第一代。我們受到的教育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更多樣,文化上更先進,生而為優秀的世界公民。
我們經歷從DOS到Windows,從寶石字形到HWP;從以Unix為基礎的數據通訊發展為網際網路,我們對於大部分的操作系統程式都能操控自如。以前只有專業攝影師才能拍出來的照片,我們也能用幾十萬元的照相機照出來,過去只有電視台才能拍攝、編輯的視頻,我們也能輕易地完成。一言以蔽之,我們和上一代的人完全生活在不同的國度,和以前的世代相比,我們幾乎可說是超人。我們在落後國家出生,成長為開發中國家的年輕人,然後在先進國家上大學,可是現在的我們沒有工作,這像話嗎?
韓潔也同意我的話,他口沫橫飛地說道:
「我們從小學到現在,每天從早到晚只是坐在書桌前面讀書,乖乖做著父母或老師叫我們做的事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世界上充滿性能卓越的東西和必需品,為什麼我們的口袋裡沒有可以購買的錢?不是說每個人的國民所得是兩萬美元,這些錢都去了哪裡?你知道我們為什麼這樣活著?我覺得我們太順從了,那些老傢伙根本不怕我們嘛!你想想看,三八六世代手裡不都拿著汽油彈?那些怕死的老傢伙心裡有多害怕啊?他們得畏懼我們,才會為我們創造就業機會,才會給我們提高薪資。這些該死的大企業根本就不招聘,只是在大學裡蓋了各種建築而已,誰需要建築物啊?」
留下這些話以後,韓潔去了瑞士的酒店學校留學,大概幾年後,不管是成為廚師還是調酒師,他一定會獲得實際的工作,然後回到首爾來。無論如何,現在我得處理延宕了許久的作業了,總不能永遠拖下去吧?我拿起鉛筆,在白紙上寫下:
我需要錢。
寫下來之後,也沒有別人會看到,可是我總覺得「錢」這個字看起來太俗氣,於是把它擦掉,在下面寫著「職場」二字。我又覺得似乎不太合適,於是又把它擦掉,寫下「工作」,因為沒有職場也無所謂,但一定要有工作才行。
我看了月曆,到了下個星期,我就在考試院住滿一個月了。怎麼辦?至少這裡有天花板,四方也有牆壁遮擋,不是嗎?如果離開這裡,我能去哪裡?我雖然絞盡腦汁,但也想不出妥善的方法來。這世界泛濫成災的金錢究竟都去了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