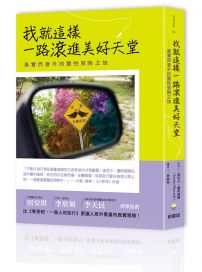1. 天空中的臉 1992年5月
「奎度!」我哀聲大叫,「我綁的綠頭毛鉤看起來活像一隻吸血螞蟥!」
「綠頭毛鉤不就綠頭毛鉤唄。」他喃喃地說,掛斷電話。
奎度‧藍哈特‧拉爾三世是我的釣魚教練,我那氣死人不要錢、派頭十足、要求甚嚴、穿高筒釣靴的「黑武士」飛蠅釣教練。要不是他長相酷似布萊德彼特,我才不甘忍受他的虐待。我們是在一九九O年夏天第一次參加外蒙古釣魚遠征隊時認識的。奎度和我一樣來自北美西,他代表《國家地理雜誌》去考察,我則是受《君子雜誌》委託隨行採訪。我為雜誌撰寫採訪稿已經將近十年時間,編輯老爺們總算答應讓我——一個女生!——撰寫跨國冒險故事。
我愛冒險故事。我愛冒險行動和冒險帶來的驚喜、鮮活的人物、遙遠的背景、明確的內容、把事情做到位,以及十九世紀探險家的幹勁,這一切都符合我對田野採訪報導近乎病態的喜愛。就個人而言,我寧捨描寫現代人際關係的抒情小說,選擇白芮兒‧馬克罕的飛行散文《夜航西飛》:「我的飛機從奈洛比機場起飛,這大概是我第一千次的飛行了,」她在書中這樣寫著,「每當機輪從地面開始滑行一直到飛上天空,我沒有一次不感受到宛如第一次冒險般的興奮與刺激。」和馬克罕一樣,我也想親眼見證,看它、聽它、嘗它、聞它、加入它,並且在難得的情況下——好比打高爾夫球或用假音唱瑞士約德爾調民歌——嘗試把它做到最好(假如有個地洞,我想我總有一天會唱出約德爾調)。
因此,當奎度答應教我如何在蒙古蔚藍的天空下用毛鉤釣魚時,我雀躍萬分。回國後,每隔幾個月,我會離開位於西雅圖西部外海瓦遜島上的小木屋,驅車南下到奎度居住的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然後我們會找一條美麗的溪流,他為我上了兩分鐘的釣魚課後,便會扔下我,獨自找地方釣魚。這也是為什麼我老是學不好拋釣技術的緣故。現在他又要我學會自己綁毛鉤。
看奎度綁毛鉤彷彿看一場魔術表演,但是在我手上,它就像整理蒲公英的絨毛一樣,還沒來得及把絨毛綁在釣鉤上,它們就飛走了。而且我還經常把自己的手指跟鉗子綁在一起。一陣初春的微風從窗口吹進來,又把雞毛吹散了一地。
「可惡!」我說。
電話鈴聲又響了。
「奎度,我不會!……喔,是潔娜!嗨!」
我想道歉,但繼母的聲音聽起來十分沙啞。
「你父親住院了,」她打斷我的話,「醫生說這次很危險,親愛的,你最好過來一趟。」
我知道我這樣說也許很不敬,但這個消息讓我覺得很煩。我的父親是個老煙槍,日復一日受到肺氣腫的折磨,過去八年已經不知進出醫院多少次,每次都說「很危險」,但他依舊活到現在,而且還在繼續抽煙。我快煩死了。
我收拾好毛鉤的材料,把它們塞進那口老舊的漁具箱,書房窗外的天空和蒙古的天空一樣藍得發亮。我只想把飛蠅釣(又稱毛鉤釣)學好,然後接下到世界各地去採訪釣魚活動的任務。但是在那之前,我得先學好拋線技巧,同時,我也必須先學會如何綁出漂亮的毛鉤,這兩樣我都沒學好,現在我的老爸又生病了。
「我不去,」我大聲說。我的忠實的短腿柯基犬阿弟瞪大眼睛看著我。
「別瞪我,我不去!」
我踩著重重的步伐進入浴室,用力脫下衣服,站在蓮蓬頭底下,然後,我聽到「那個聲音」了。
「這次是真的,去吧。」
我站那裡發楞,不知如何是好。然後我開始發抖,眼淚和著蓮蓬頭的水沖下來,我知道這是真的,我的父親快死了。
我抓起一條浴巾,衝出去打電話。下一班飛往洛杉磯的航班還剩一個座位。我打電話給正在上班的丈夫,體貼但一如往常不易動情的他,贊同我應該去,同時和往常一樣,他也沒有主動說要陪我去。我已經很多年沒有結婚的感覺了。
我的妹妹瓦樂莉到機場接我,她的丈夫和兒子坐在他們的休旅車中在路肩等候。瓦樂莉、史考特、還有我心愛的五歲外甥傑西,他們是我的家人,一切都很正常。
「他有多嚴重?」
「很嚴重。」瓦樂莉說著就哭了。
傑西給我看他新買的爬蟲類圖書。他是我天真無邪的小哥兒們。
事情的進展看似緩慢,卻又讓人感覺十分快速,一刻又一刻延續下去,相互堆疊在一起,從我聽到電話中潔娜的聲音到抵達父親的病榻,彷彿才一眨眼的功夫,等我在病床邊站定時,我的呼吸比他更急促了。
「潔西卡,」父親說,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心溫熱,看起來很健康,一張紅褐色的臉,雙頰紅潤,他真的快死了嗎?
父親調整一下鼻孔上的氧氣管,說起話來像剛抵達終點的馬拉松選手。
「我很……高興……你……來了。」
「我也是。」我說,拍拍他的手。
護士進來整理他的被單,他的一雙腿!那雙腿已經沒剩多少肉了,看起來像名非洲難民。
這麼說,這是真的。我凝視父親的雙眼。他害怕嗎?
「爹地,我帶了……」
「史考特,醫生來看你了。」
另一位護士把我們趕出隔簾外。傑西說他肚子餓了。
「我們還是走吧,」瓦樂莉說。潔娜點頭說她留下來。她和父親結褵二十五年了,而父親和我母親脆弱的婚姻只維持四年。瓦樂莉告訴潔娜我們明天早上會再過來。她又點頭。她看起來很糟,那是一定的,因為這次是真的了。
接下來兩天我們又去探望父親若干次。我很想找幾個只有他才能回答的問題問他,一些以後我再也無法從他口中得到答案的問題。
「你母親真的是在夏威夷的電車上認識你父親的嗎?還是在巴士上?」
好瞎的問題。
我想不出任何重要的問題,所以我沒問,和大多數面臨這種情況的人一樣,我只是告訴他我愛他。
我想為他朗讀我的朋友黛勃拉˙賴爾送我的一本小書《主說:快跑!》。不知道為什麼,老是有人想挑動我對靈性的興趣。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完全陌生的人。來,看看這個!有個印度大師要來——想不想去?你一定要去看這部新拍的轉世輪迴的電影。真奇怪,我只對世間的事有興趣,我是一個志在冒險的作家呢,拜託!
我喜歡的這本小書。《主說:快跑!》非關佛教,也無關基督教或印度教;它推崇所有的信仰,而且它很幽默。「靈性」一族的人最困擾我的地方是,他們都太嚴肅。耶穌不是復活了嗎?佛陀不是找到去除人類痛苦的方法了嗎?涅槃不就是極樂嗎?快樂不是終極目標嗎?那為什麼重視靈性的人都這麼嚴峻?但這本書不一樣,它甚至引述物理學家的話。我認為,人人都應該閱讀過去這一百年來的物理發展史。想得到啟發嗎?讀一讀量子物理吧!
我把這本書帶在身上,因為我擔心父親會害怕,怕死,怕離開我們,怕他死後可能——或不可能——發生的事。我想讓他安心,覺得物理學家大衛˙波姆(David Bohm)也許能幫上忙,至少他在科學界享有盛名。
最後那幾天我一直沒有機會和父親獨處。潔娜當然隨時守在病床邊,要不就是瓦樂莉,或瓦樂莉和傑西,或瓦樂莉、傑西和史考特,或史考特和傑西,或瓦樂莉和史考特。如果他們都不在,那就是護士和醫生。我覺得自己彷彿一個陰謀家,也許我不應該為父親朗讀這些東西?
他以前似乎很重視靈性,儘管都是死背他英籍宗教狂母親的一些陳腔濫調——她做了很不符合基督教的行為,把獨子扔在孤兒院,自己跑去南非服事上帝。同樣的偽善,使我母親在十歲那年拒絕回德州東部教養她的法國天主教會,因為她的妹妹凱蒂背不出教義問答而遭到修女責打。這些人是怎樣的基督徒啊。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決反對宗教的原因,特別是反對基督教。但我的父親此刻躺在臨終病床上,他的雙眼緊閉,他的頭在枕上來回晃動,在微弱的呼吸中低吟:「耶穌受難是為了去除……我們的罪,耶穌受難是為了……拯救我們。」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些呻吟。終於,在父親臨終前的最後一天,我發現我有機會和他單獨在一起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機會,我也不知道當時其他人都在哪裡,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爹地,」我說,「我想為你朗讀一點東西。」
他點頭,理一理他的被單。我覺得自己有點傻。
「好,嗯,這是物理學家大衛‧波姆所說有關……呃……本質的問題。哎,我直接唸給你聽好了,好嗎?好:
「『我說過,人類的意識是一體、不可分割的。當你在經驗人、地、事物時,不管它多麼神奇美妙,你只是在用自己能夠了解的形式和語言,去與同一個心識(Mind)溝通……然後你讓這個物質轉回到它原來的神性,享受我們都是一體,以及最高形式的精神世界!』」
父親的眼睛倏然張開,用食指指著天上。
「那就是祂!」他說,聲音聽起來很正常。
我嚇了一跳。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也明白了,」他回答,「這就是真理,潔西卡,我們都是一個偉大整體的……一部分,我們……都是。就是祂。」
我們談到固體物質的幻象,以及物理學家如何證明所有物體——醫院的病床、窗戶、我們的肉體——事實上都是充滿流動能量的空間。我們又談到萬物被這奇妙而有智慧的能量連結在一起。我們還談到神,但我們沒有提耶穌。
「這麼說,你不怕?」最後我說。
「不怕,」父親回答,調整一下他的氧氣管,「只是……不太舒服。」
我們倆都笑了。
這時候潔娜走進來,父親握住她的手。
「潔西卡和我剛……聊到……但願我們二十年前能有這樣的交談!」他說。
「不,不!」我抗議,「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談了!」
父親微笑。
次日傍晚,父親的肉體像一台舊機器一樣停擺了。我搭機返家。接下來兩天一片渾噩。我沒有哀慟,也許是太震驚的緣故。我好像什麼事也不能做,心不在焉。到了第三天早上,我異乎尋常地早早醒來,格外清醒且精神奕奕。由於父親剛剛過世,這種狀況似乎有點說不過去。我的精神好到讓我不知如何是好,於是我把已經取消去阿拉斯加釣鮭魚的委託任務又重新接回來。一切都恢復正常。同樣的,我要的下一班飛往阿拉斯加的班機又只剩最後一個座位。我立刻整理行裝,絲毫沒有往常最後一刻的手忙腳亂,中午十二點半離開家,準備搭十二點五十分的渡輪。
那是五月下旬一個晴朗的春日,我在清朗無雲的藍天下開車。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忽然抬頭往上看,就這麼一抬頭,我看見父親的臉出現在我頭上的天空。那張臉大到塞滿整個藍天,彷彿電影院中的投影,而且是彩色的全像攝影圖,半透明,色彩非常鮮明。它是由各種顏色的光聚合而成,彷彿從彩虹雕刻出來似的。父親臉上的表情散發出非凡的喜悅,它不是我所認識的父親——人世間的父親始終是焦慮的,他從來不是一個快樂的玩家。
我驚詫地望著它。他的臉在快速變化,我注視著它,看見它的色彩逐漸加深。然後我恍然大悟,這個彩像充分證實了我們最後的談話——我是真的在「用自己能夠了解的形式和語言,去與同一個心識溝通」:也就是我父親的臉!我當下恍然大悟,父親——或某個人,或某個東西——正從死亡的喪鐘下展現一個連科學家都承認為事實的證據:一個凝結之光致福的展現。大衛˙波姆是對的!儘管肉體死了,人的意識是不滅的,因為我的父親,或父親的一部份,就在那裡,此刻正出現在我眼前。
許多人宣稱看到已逝親人的靈魂——也許在夢中,也許在門口向他招手。然而,或許除了伍迪艾倫之外,我們很少人會有這種戲劇性的陰陽接觸,看到父母親的面容出現在天空中。但父親這種復活不是惡作劇,它是一種來自天上的禮物,明確的告訴我,父親和他的去世這兩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有活著的人才有死亡的痛苦。當然,我不會把這個已經驗證的智慧說給別人聽,否則,人們會怎麼想!
但就在當天晚上,我的妹妹瓦樂莉打電話到阿拉斯加找我。
「今天是我這一生最不可思議的一天!」她激動地說,「我在一個異象中看到爹地了。」
「什麼!」我說,盡可能保持冷靜,「你是在天空中看到他的臉嗎?」
她大吃一驚。果然不錯,當天下午三點三十分,就在我看到它的三個鐘頭以後,我的妹妹也在天空中看到父親的臉。她當時剛幼兒園把傑西接回家後準備再回辦公室,和我一樣,她也是自己一個人開車,抬頭忽然看到父親的臉在這個南加州濱海小鎮的天空中閃耀。那個小鎮是我們從小成長的地方,瓦樂莉一直住在那裡。
「他好快樂!」她告訴我,「他在發光,而且他的臉佈滿我頭上的天空。它有點半透明,但輪廓比它的四周更清楚——那些色彩好美!他好歡喜!我忍不住把車掉頭,揮手說:『再見,爹地!再見!』車子掉頭後,他還在天上!無論我往哪一邊看,他無所不在,彷彿他在天上,同時又在我四周。」
我們一致同意,我們共享了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奇蹟。我們知道,這個奇蹟有助於我們未來處理失去父親——或任何其他我們所愛的人——所帶來的的傷痛。我沒想到的是,這次的經驗竟然讓我進入一個全新而奇特的靈性世界,這個世界具有如此絕妙的創意與力量,連那些有第一手經驗的人也難信服。
2. 聖養豬人 1994年 11月
電話鈴聲有如寺院的鐘聲劃破天空。事實上,我正想著寺院,因為我想找一位佛教僧侶到我任教的華盛頓大學寫作班演講。這是今年的最後一堂課,我想請一位能帶來啟發性的貴賓到班上演講。
我不久前才看過一部電影《小活佛》,敘述一名住在西雅圖的男孩被認為可能是一位西藏大喇嘛的轉世。電影中,男孩的父親向一位西藏僧人提問有關轉世的概念。僧侶為男孩的父親奉上一杯茶後,便打破自己的茶杯,茶湯四濺。僧侶解釋茶杯如同人的肉體,而茶湯就如同人的意識,當肉體消亡時,意識仍繼續存在,只不過換了一種形式——相當於愛因斯坦的能量不滅定理,當然也符合看見死去親人的面容出現在天空的概念。我很想找個人為我的學生闡述這種概念,使他們能建立無我的寫作觀,摒棄有限的茶杯象徵的自我意識和先入為主的觀念,使無拘無束的靈感能源源不絕湧入。
但我的計畫進行得不大順利。
到目前為止,我只和西雅圖市區一座藏傳佛教寺院內一位不會說英語的僧人通過電話,另外一位是朋友口中所謂的「白雞佛教徒」,我第二次再打電話去這座寺院時她接的電話。她告訴我,院內的僧侶絕不可能去大學課堂上演講。不過她給我一個在亞洲研究學系任教的美國教授的電話。
「他是西藏人嗎?」
他不是。他是另一個想成佛的白人。更糟的是,他用惹人厭的做作語調說話,一會兒是不自然的高亢音調,彷彿在誦經,一會兒又降到極低,根本聽不清他在說什麼,更別說要聽懂。我盡可能解讀的結果,發現那竟然是對立的言論。首先,他提到拋棄自我有助於寫作的概念,「許多成功的作家都十分自我……(聲音越來越小)」。我回答,我通常不會先告訴我的學生我要怎麼做,然後再「出其不意灌輸他們新的概念」。他說,他覺得「灌輸」是個「非常暴力」的字眼,「會造成……(聲音越來越小)」。
我的一位德州表親常說,沒有人喜歡白癡,但佛教白癡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我禮貌地告訴這位「比你更懂佛教的先生」談話到此結束。那時候已經是星期一了,我的課排在星期三。就在我幾乎放棄這個尋找啟發靈感演說者的點子時,電話鈴響了。
「還沒找到你要的佛教僧侶……?」電話那頭說道。
那是我的哥兒們吉姆‧史都華,「星巴克」早期的經營者「西雅圖極品咖啡」的創辦人。吉姆的烘焙工廠那時候設在瓦遜島,他曾經應邀為我班上的學生示範如何品嚐咖啡,讓他們練習如何用文字來描述味覺與嗅覺。
「你是何方神聖,是那個咖啡瘋子嗎?」我問,然後我告訴他,「我找不到人!」
「我的領導力老師自告奮勇去你班上演講。」
他的領導力老師?
「領導力老師是什麼東東?」我問他。
原來吉姆曾經向他這位顧問提到我這個班級——我如何以茶和點心、精油、鮮花及音樂寵愛我的學生,因為我發現多寵愛他們一點,他們就會多用功一點,這是現代教育比較弱的一環。他們戲稱我這個班是「成人的幼稚園」。想不到,吉姆的顧問竟自告奮勇要來當我的客座講師,他對我這個冒險女孩產生好奇心。我反正已經沒了主意就答應了,不過心裡還是有點忐忑不安,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傢伙打算說什麼。
但是當羅利˙米塞爾(Lory Misel)走進我的教室時,一股神聖的電流也隨著他一起進入。
我指的不是他的外表——他是一個長相普通的人,有點鄉紳派頭,身材高大,年紀大約在五、六十歲,微微發福,戴眼鏡,穿著一件手肘貼皮的羊毛外套。但他身上會發光,一種純善的光芒從他身上散發出來,而且他有一股乾淨的毛巾味。羅利顯然不是常態性的顧問,我很快便發現,他是一個養豬農,在西雅圖東南部的雷尼爾山腳下有一座農場。他雖然堅稱他真的是「一個以家庭心理輔導為業的養豬農」,但他同時也是一位高水準的靈性導師——不自大,不自吹自擂,沒有鼓吹他人「簽名加入我的教會」的宗教狂熱,而且(謝天謝地)也沒有高調古怪的假道學激情。羅利甚至不收演講費。他的嗓音彷彿具有魔力,能使人平靜下來,又具有傳導力,當下便能吸引人全神貫注,隨他而轉,彷彿一張能把人帶到寧靜祥和之地的聲音魔毯。
那天晚上他講了一些前所未聞的事,說我的學生「很早以前便與神訂下契約」,今天才會在我的課堂上聚在一起(說他們過去是一群出類拔萃的人)。他說神會引導他們邁向正確的寫作之路,他們在智力上與情感上都不能低估他們在神眼中的真正價值。他說,事實上,他們是「神的聖子」,他們出生是為了「庇祐這個世界」。
三個小時之後,全班二十五位學生絕大部分都聽得如癡如醉,許多人流下感動的淚水,都很高興能在學期結束前意外得到這種啟發——其中只有一位持無神論的學生例外,她很不滿意我請來一位靈性講師……「不過,我原諒你,我的孩子。」她說,然後誇張的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
我非常激動,全身每個細胞都在高速悸動。這個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
第二天上午我打電話給羅利問個清楚。
我激動地再度感謝他到我班上演講。
「喔,十年前就有人告訴我,我會遇見你。」他不假思索說。
我大吃一驚。
「有人『告訴』你,你會遇見我?」
「是的,」他說,「那個人說我會遇到一位紅髮作家,然後我們會一起合作,寫出非常重要的靈性著作。」
前兩天我就聽說羅利宣稱他曾得到某種異世界的指示。
「可是我……我,」我結結巴巴說,「我是個冒險作家哩!你確定我是……他們說的那個人嗎?」(管「他們」是誰,我心想。)
「啊,是的,」羅利回答,「吉姆提起你和你的班級時,我就知道那個人是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