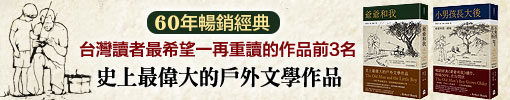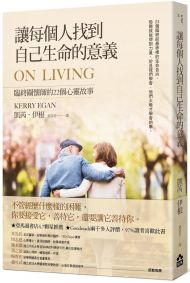【想像力與苦難】
亞伯特總是坐在同樣的位置:坐在床頭的一張椅子上,位於愛妲和窗戶之間。他輪流重複著同樣的動作:看著愛妲的眼睛,把一湯匙融化的冰淇淋送進她嘴裡,輕拍她凹陷的雙頰,然後望著窗外。我總是坐在亞伯特的對面,床的另一側,我們兩人之間,夾著他依然貌美的妻子。
我見到愛妲的時候,她已經完全無法說話,肌肉收縮的程度嚴重到手指整個蜷曲、戳進掌心的肉裡,非常疼痛。她已經有好幾年沒辦法移動,只是不斷愈縮愈緊,縮成像一顆球。所以,其實真正和我交流的人是她的丈夫亞伯特。
每次我去拜訪時,亞伯特都會說同一個故事,說了好幾十遍,每一次的內容都一模一樣,用字遣詞一模一樣,說話的姿勢也一樣。
「他好愛那些火雞爪。喔,他覺得那些火雞爪很好玩。他假裝自己是火雞,我們全都笑了。他假裝拿火雞爪來搔我癢,結果是他自己被搔到。」
亞伯特每次講這個故事時,都會把雙手舉到面前做出雞爪的樣子,手掌用力張開,手指半彎,就像他兒子拿著玩的火雞爪。小男孩拿著火雞爪在廚房裡,追著父親跑了一圈又一圈,就在感恩節前夕,也是他死於腦膜炎的前夕。
他才四歲。我閉上眼就能看到亞伯特在我面前,一遍又一遍做出同樣的動作。
「他發燒得好厲害,我們甚至來不及發現。醫生救不了他。全都是因為我們讓他玩那隻火雞。他好愛那些火雞,總是笑啊笑個不停。」
亞伯特凝視著空無一物的前方,張大嘴一臉呆愣,然後搖了搖頭,一如他每次結束這個故事時的動作。
亞伯特堅信,兒子生病是因為被火雞爪抓到,不管醫生護士怎麼說,都沒辦法改變他的看法。他知道兒子的死因是腦膜炎,但他也知道是因為火雞爪。
他自己養的火雞,他太太清理乾淨的火雞,他們允許兒子玩的那隻火雞,只因為他笑得如此開心。
亞伯特責怪自己,他早該想到會有這種後果。
「你能怎麼辦?你能怎麼辦?你能怎麼辦?」他一面輕拍妻子的臉頰一面反覆質疑,每次都是這樣結束。
✳✳
當故事從不改變時──當某個人一遍又一遍用同樣的方式訴說同樣的故事時──總是讓身為靈性關懷師的我很緊張。我提出的問題無法引出新的回答,我的禱告似乎無法帶來安慰,說話者對於看到、學到、想到、體驗到的其他事物,始終無法產生新的連結;對於發生的事沒有任何感想,甚至似乎不知道我在場,只是一遍又一遍說著同一個故事,每次說的內容都一模一樣,絲毫不差──這表示這個故事卡住了,說話者承受的苦痛凝固了,而且這苦痛是沒有意義的。倘若這苦痛是人生中的一大重要事件,便可能意謂著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傷痛是有生命的,乍聽之下可能有點難以接受,但這是真的。傷痛會成長演變,像生物一樣。有時候,變化來得又急又快又驚人,空虛的悲哀可能在一夜之間轉變為熊熊燃燒的怒火,堅毅的忍耐可能在瞬間瓦解爆發。有時候,改變的速度很慢,慢到幾乎無法察覺,要等到二、三十年後回顧時才會發現。
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希望有變化。傷痛成長演變時,位於其核心的苦難也會跟著改變,變得沒那麼劇烈,沒那麼熱辣辣,也沒那麼怵目驚心。我不確定這痛苦會不會縮減,但我知道它會在回憶中擴散,隨著環繞痛苦核心的回憶四散,痛苦似乎變得沒那麼集中,因而比較能夠忍受。
然而,有些痛苦似乎凍結於時空中,就像愛妲,手指永遠蜷曲如爪,戳進掌心;就像亞伯特,手指蜷曲如爪,戳進空氣裡。
✳✳
「大家都討厭改變。」在我遇見亞伯特和愛妲許多年後,另一個病人蘿絲這樣宣告:「沒人喜歡改變。但是我要告訴妳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改變是來自上帝的禮物。我們應該每天跪下來感謝上帝,謝謝祂讓所有事物隨時隨地在改變。這就是我的看法。」
我才剛告訴蘿絲我沒辦法再來看她了,因為我要搬去南卡羅萊納州。要離開家、離開我的朋友和工作讓我很難過,而她的這種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每個人都只想到好的事情變了,這就是問題所在。」蘿絲繼續往下說:「但是如果好事不會變,那麼壞事也不會變。感謝上帝,壞事是會改變的。不管是多壞的事都會改變。要是什麼都不會變,我們八成會發瘋。」
那個躺在醫院的男孩,那個因為球鞋搶劫中彈而脖子以下癱瘓的男孩──我從他的痛苦中逃開,無法逼自己回頭──他的苦難讓我無法承受,就是因為當我看著他,看著他的未來,卻看不到任何改變,我只看到永無止盡的不變。他會一直癱瘓下去。他重複了一遍又一遍的那些話,那些不變的話語,更突顯出這一點。
但真正心靈癱瘓的人其實是我。我只看見他的身體狀況,沒有想到他的精神和感情並沒有隨著身體一起癱瘓。我沒有去想像,即使手腳不能動,還是有無限方法可以過著快樂而充滿意義的人生。我沒有去想像,我可以如何創造出一塊神聖的空間,讓他能在其中哀悼他的痛,讓他的心和靈魂能夠跨越眼前的苦難,向前邁進。
我的想像力辜負了他。
蘿絲說的話確實千真萬確。世上所有的事終究會改變,只不過有時候,當我們正身處苦難之中時,無法想像事情能改變。
✳✳
當某人訴說自己受苦的故事時,很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依然身處痛苦之中。其他人沒辦法代替他們決定這苦難的意義,或這其中到底有沒有意義存在。我們當然也不應該說一些類似「上帝絕不會給任何人他們無法承受的苦難」,或是「上帝自有其旨意」這樣的話,我們不可能光靠丟下一句「苦難有某些深遠的意義」,就憑空斬斷某人的痛苦。只有當事人才能決定事情是不是這樣。我們能做的,只有坐下來傾聽他們的故事,如果他們願意說出來的話。
若是他們不願意說,那麼我們可以靜靜坐在那兒陪伴他們。
當人們翻來覆去、一遍又一遍講述他們的故事時,是在試著找出或是製造意義。這個意義必須由他們自己發現,儘管過程可能痛苦萬分,但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旁觀者不管是絞盡腦汁幫忙思考,或是提供最老套的陳腔濫調,最後還是必須由他們自己面對。而他們所找出來的意義和你所能想到的幾乎絕不相同,總是更有深度,更細緻入微,更出人意表。
✳✳
我曾經遇過一個病人,是一個白血病末期的四十多歲女性。她告訴我,她是多麼努力祈禱,長時間拚命祈禱,想要康復,想要能夠再次好好當她孩子的母親。她當然不想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目睹她的痛苦。她祈禱再祈禱,但是病情卻愈來愈嚴重,疼痛愈來愈加劇,不管用了多少嗎啡都無法壓抑。現在死亡迫近,只剩幾個星期的時間,她就要死了,無論她多麼努力祈禱都不可能改變。這讓她鬱鬱寡歡。
但是在某一次我去探訪時,她語帶驚奇地告訴我,她領悟到上帝其實終究有回應她的祈禱,她說:「一切消散以後,我終於懂了,死亡就是答案。」
我通常十分擅長在病人面前維持鎮靜的姿態,但是這一次,我可以感覺到震驚掠過自己的臉龐。她微微一笑。
「妳不懂嗎?死亡將會帶走我的痛苦。這是終結痛苦的唯一辦法,也是我的孩子不會再看見我受苦的唯一辦法。妳懂我的意思嗎?終結痛苦的唯一辦法就是我死掉。我可以教我的孩子如何不帶恐懼地死去。他們將會從我身上學到這件事。這就是身為母親的我能為他們做的事。」她停了下來,或許是在等我的回應。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又說:「事情總會有辦法解決的,現在我懂了。只不過一開始的時候我不懂。這不是我想要的解決辦法。但是事情總會解決的。只不過不是我原本想的那樣。」
她要教她的孩子怎麼死。這是她在生病和死亡中找到的意義和目標。
有時候,我會對我那情感豐沛的女兒這樣說:「事情總會有辦法解決的,親愛的。妳只是還沒想出來而已。」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說這話,因為這話從來沒有安慰到她。
她會回答:「妳總是這樣說,但是這種情況根本沒有辦法解決!」我猜想,我是希望這種想法能深深滲入她的潛意識,等到哪一天,她遇見真正可怕的事情,當她的世界天崩地裂時,她會在心底某處想起來:總會有解決的辦法,苦難不會持續到永遠,即使在最悲慘的情境中,人也能找到某種意義。
我也能理解她的反應,猶如膝反射一般直覺抗拒這樣的概念。身在苦難當中時,本來就很難接受這樣的想法,甚至連想都沒辦法去想。苦難的本質就是這樣,不論你是受苦受難的人,還是旁觀者,都很難去想像改變。
然而,所有事物一定會改變。
我不是在試圖美化死亡,真的不是。我只是在重述我的病人希望我分享出去的那些故事,盡我所能分享他們的想法,以及他們所獲得的啟示。這些故事和啟示的內容並不是我決定的,其中有些乍聽之下可能顯得奇異而獨特,讓人不舒服,或甚至只想敬而遠之。但是身為靈性關懷師的我,有幸得以聆聽將死之人的真知灼見,我可以告訴各位,有時候這些內容是如此具有啟發性,能徹底解放你的想法。病人們在我想都想像不到的地方找到意義,而且這些意義遠比我所想到的東西更讓人嘆為觀止。這就是為什麼你必須讓人們自己去找出意義,因為他們得到的成果絕對會遠遠超越你。
✳✳
但是有時候,有時候呢,就是找不出意義,再怎麼努力也製造不出意義。
有時候,在這世上有一種痛苦是如此龐大,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帶著這痛苦,用一個永遠不改變的故事帶著它一輩子。有時候,就是會有那些荒誕無稽的火雞爪,永遠搔抓著空氣。
遇到這種情況時,除了靜靜傾聽別無他法。有時候,當我疲累不堪時,或是剛從另一個病人那兒聽到讓人難過的故事,又或者,只是那一天剛好某根心弦被觸動,縱使我已經對這個故事熟到不能再熟,我還是會忍不住跟著亞伯特落淚,為了他走得太早的兒子而哭,為了他活得太久的妻子而哭。
我會悄悄抹去淚水,提醒自己,他為之哭泣的那個小男孩不是我的孩子;提醒自己,亞伯特不是我的爺爺。我通常能掩飾自己落了淚,因為他是如此沉浸於悲傷之中。但是有一次,他看到我在哭。
「喔,天啊,我害妳哭了。」他的聲音破碎粗啞。
「沒事,沒事,沒什麼。」我回答。
「謝謝妳為我的兒子哭。再也沒有人會為他哭,除了我。等到我死了,就再也不會有人為他哭了。」
他停頓了一下,重重地嘆了口氣,把肺裡的空氣全部嘆了出來,說道:「說不定這是件好事。因為到時候,我們終於可以團聚在一起,我再也不需要哭了。」
【「死」只不過是個動詞】(節錄)
即將死去的人不會莫名其妙變得特別有智慧,或有神奇的魔力;同樣的,照顧他們的人也是如此。
大體而言,照顧病人的人並不比我們其他人更有同情心、更堅強、更有耐心或愛心。他們並不特別,而且不管別人怎麼說,他們並不覺得擔起這種責任是神的賜福,至少我從來沒聽過有人自己這樣說過。很多人覺得孤立無援,大部分的人根本不想要承擔這份責任──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照顧自己的配偶、父母或兒女,而是因為他們壓根兒不希望自己的配偶、父母或兒女得到不治之症。
一般人會主張,那些照顧垂死者的人都是聖人再世,這種想法和「垂死者與你我不同」的看法互為表裡,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我有個多發性硬化症臥床超過十年的病患,她丈夫告訴我,有時候他會在雜貨店和教堂遇到他太太以前的女性朋友,她們會誠摯地緊握他的手,希望他知道她們在為她祈禱。
這個丈夫怒氣沖天地說:「她不需要那些天殺的禱告!她需要你們來看她!別因為不想來就拿禱告當成他媽的藉口!」
照顧垂死者的工作使人心力交瘁,身體、情緒、心理和精神都很累。照顧者的人生,因為家人被診斷為末期病人而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承擔起照顧病患的工作同時,他們並沒有因此變得更有力量或活力,還是和以前有著同樣的需求和弱點。若是假裝他們擁有超人的力量,往往代表我們放著他們孤軍奮戰,這不僅使他們無法得到所需的幫助,也讓垂死病人無法得到所需的安慰與陪伴,更讓我們失去了每個人都應該要有的認知:沒有任何事物──包括死亡──能夠輕易抹去我們的缺點,或是能像變魔術一般,讓我們變成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有人曾經問過我,我認為人們應不應該事先想好臨終遺言。簡短版的回答是:不用。無論你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很有可能,你在說的那個當下,根本不會察覺到這是你人生中說的最後一句話。那種好萊塢電影式的死法,在斷氣前輕聲吐出祕密或是深富哲理的話,並不會發生在現實世界當中。大部分的人要不是在死前好幾天就陷入昏迷狀態,就是死得太突然,什麼都來不及說。
也有一些人是太虛弱或神智不清,所以語不成句,或者有些人最後說的話只是一聲感嘆,像是「看!」或「天哪!」。
比較長的答覆版本是: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如果你有事要告訴心愛的人,而且這件事重要到你願意花時間去構思準備,那麼,為什麼不能現在就說?現在立刻馬上說?
如果你想要道歉,那就現在立刻道歉。如果你想告訴某個人你以他為榮,現在馬上就說。如果你想要表達愛意,趕快打電話過去說「我愛你」。如果你想要求原諒,這一秒就做,趁著還有時間,才能走完達到和解的必經過程:釋出善意、考慮、接受、原諒。別遲疑,現在就做。
這些事情或許很困難,甚至很嚇人,但是死亡不會讓你變得勇敢,不會讓你變成另一個人。如果你沒辦法在吃飯、走路,或是用吸塵器吸客廳地板時,找到做這件事的勇氣,你憑什麼認為,自己會在做一件從來沒做過的事情時找到勇氣?
倒不是說在人生的最後幾個月、幾個星期或甚至幾天內,不會發生巨大的改變和成長。確實是會發生的,我見過。
但我也同時見到為了促成這種改變所付出的努力。人在健康時,在沒有學習如何從事一項全新的活動時,同樣也需要為了改變而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