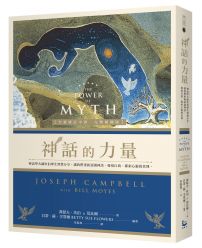英雄的歷險
莫:為什麼在神話故事中,有這麼多的英雄?
坎伯:因為那是值得大書特書之事。甚至在流行小說中,主要的角色也都是個英雄或英雌。他們或發現,或完成一些超越正常範圍內的成就與經驗。英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比他偉大事物的人。
莫:文化不同,英雄穿的外衣也不同,他們行為的內涵又是什麼呢?
坎伯:有兩種不同的行為。第一種是肢體的行為。英雄在戰場上勇敢作為或解救生命。另一種是精神層面的行為,英雄經驗超常態的人類精神生活,然後回到現世傳播訊息。
會展開英雄歷險的人,經常是自己有所失,或是覺得其他社會成員有所匱乏。接著這個人便開始一連串的歷險,不是去找回他失去的事物,就是去找尋某種滋養生命的萬靈丹。歷險通常是個循環,有去有回。
這個歷險的結構以及相關精神意義,在一些早期部落社會的成人禮或啟蒙儀式中,便預期得到。透過這些儀式,孩子被迫放棄他的兒童期, 而真正長大成男人。死去的可說是幼稚的人格與心靈,重新回來的則是一個負責任的成人。這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一個基本心理轉化。未成年前,我們有十四到二十一年的時間依賴於他人的保護與監督。如果你要攻讀博士學位,依賴期可能會持續到三十五歲。因此你絕不是一個能自我負責、自由行動的人,而是一個服從命令的依賴者,隨時等待別人的發落, 或接受懲罰與獎賞。要從這種心理上不成熟的「地位」,脫胎換骨擁有自我負責、自我擔當的勇氣,就必須要死一次然後再活回來。那就是所有英雄歷險的基本母題——出離某種境界並發現生命的來源,以將自己帶入另一個更多采多姿而成熟的境界。
莫: 所以,即使我們不是拯救社會的大英雄,我們在心理上、精神上都必須要經歷這樣的「旅程」。
每個人出生時都是個英雄
坎伯:正是如此。蘭克在他那本重要的小書《英雄誕生的神話》中宣稱,每個人在出生時都已經是個英雄了,出生的過程就是一個兼具心理與生理的極大轉化,每個新生兒都從一個充滿羊水環境的小水生動物,變身成一個呼吸空氣的哺乳動物,最後還會站立起來。那是個巨大的轉化。假如這是個有意識的過程,那一定是一種英雄行為。而母親那一方也是種英雄行為,因為這一切都是她帶來的。
莫:那麼英雄不全是男性了?
坎伯:喔,不是的。男性通常會是個較顯著的角色,那是因為生命的條件使然。他在外頭的世界,女人則待在家中。但以阿茲特克人為例,他們會依據人死亡的狀況把靈魂分配到許多不同的天堂,而死於戰場的戰士和因分娩而死的母親,所歸屬的天堂是同一個。生產確實是一種英雄行為,在那個過程裡,分娩者把自己交付給另一個生命。
莫: 英雄的試煉、考驗與折磨有何意義?
坎伯: 從主觀意願上來講,試煉是用來驗證有「成英雄」意圖的人,是否真能成為一個英雄?他是否真能匹配這個任務?他可以克服危險嗎?他有勇氣、知識和能力服務他人嗎?
莫: 在這個簡易速成的宗教文化中,我們似乎忘記了三大宗教的教導:英雄旅程的試煉是人生重要的一環,沒有捨棄,不付出代價,就不會有收穫。《古蘭經》說:
「你認為你可以不經歷和在你之前死去人們一樣的試煉,便能進入充滿極樂的伊甸園嗎?」耶穌在《馬太福音》中說:「通往生命的門是偉大的,路是窄小的,極少人能發現它。」猶太教傳統的諸位英雄在達到他們的救贖之前,也都經歷過大考驗的。
坎伯: 假如你能夠體悟真正的問題所在--放下自己,把自己交付給更高的目的或他人,你就能體悟這才是終極的試煉。當我們的思考不再以我們自己或我們的自我維護為主時,我們便在意識上經歷一場真正的英雄式轉化。
所有的神話都必須處理某種意識上的轉化。你一直以某種方式思考,現在你必須以另一種方式來思考。
莫: 意識如何轉化呢?
坎伯: 要不通過試煉本身,要不通過啟示。試煉與啟示就是轉化的全部了。
莫: 我們常聽人說:「和你自己接觸。」你認為這句話如何解釋?
坎伯: 由於深受周遭他人的理念和命令影響,你對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可能成為什麼?根本一無所知。我認為,在極端嚴格、威權的社會情境中成長的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了解自己。
莫: 因為你總是聽命於人。
坎伯: 每次都有人確切告訴你要做什麼, 每分每秒。你是在軍隊裡啊。這就是這個社會的做法。從小在學校,總是有人告訴你該做什麼,所以你才會算日子等待放假日,因為那是你做自己的時候。
莫: 如何與另一個自己、真正的自己接觸,這點神話怎麼說?
坎伯: 首先要遵循神話本身,以及宗教導師的提示,他們應該知道的。這就像運動員找教練一樣。教練告訴他如何把自己得能量好好在比賽中發揮出來。一個好的教練不會告訴跑者如何提起手臂之類的事。他會看著他跑,然後幫助他調整他自己天生的模式。一個好的老師守護年輕人、辨識他的可能性,然後再給建議,而不是命令。命令會是:「這是我的方式,所以你必須這麼做。」某些藝術家是以這種方式教導學生沒錯。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作為老師的都應該好好跟學生談,給他們一些線索。假如沒有人這麼守護你,你必須自己絞盡腦汁、從無生有,就好像重新改造輪子一樣。
我知道有一種好方法:你有什麼困擾,就去找一本在處理相關問題的書,一定會給你一些線索的。我自己就從閱讀湯瑪斯.曼和喬伊斯的書中受益良多,他們兩人都是把基本的神話主題,用來詮釋當代社會年輕人的各種問題、疑問、體悟和關心的事。你可以透過了解這些事的優秀小說家作品, 找到你專屬的「神話引導」母題。
莫: 那是讓我感興趣的地方。假如我們夠幸運的話,假如神和繆思都在微笑的話,大約每一世代都會有啟發我們想像力的人出現,讓我們踏上自己的旅程。在你的年代是喬伊斯和湯瑪斯.曼。在我們的時代,大概就是電影吧。電影是否創造了英雄神話呢?你認為像《星際大戰》那樣的電影,是否有滿足「創立英雄典範」的部分需求呢?
坎伯: 我曾聽到年輕人使用喬治.盧卡斯的某些用語如「原力」和「黑暗面」等。所以它一定有某種影響力。我認為,它是個很好的教學素材。
莫: 我想那某種程度地解釋了《星際大戰》的成功。它並不只是一部製作精良、值得一看的佳片,它推出的時機也正好符合人們以「熟悉的意象觀賞善惡交戰」的需求。他們需要理想主義來給自己提個醒,想要觀賞基於無我而非自私的羅曼史。
坎伯:「邪惡力量不等同於任何特定國家」,這個事實意味著它是一種抽象的力量,它代表一種原則,而不是特定的歷史情境。這個故事講的是原則的運作,而非國與國的交戰。電影裡頭演員戴的野獸面具,代表當今這個世界的真正野獸勢力。達斯維達面具下面是個未成形的人,一個尚未發展成為人類個體的人,是一張奇怪、可憐、未分化的臉。
莫: 它的意義是什麼?
坎伯: 達斯維達尚未發展出他自己的人性。他是一個機械人。他是一個官僚,活著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一套外加的系統。這是對我們生活的威脅,是我們今日共同面臨的課題。系統將打敗你、否定你的人性呢,還是你能運用這個系統來造就人性化的目的呢?你要和這個系統保持怎樣的關係,你才不至於被迫受制於它?意圖改變它以符合你的思考系統是沒有用的。它背後的歷史動能太強大,因此要從個人行動衍生出真正有意義之改變的機會太過渺小了。你要做的是去學會活得像個人。這和改變大環境完全不同一回事,而它是可以做到的。
莫: 怎麼做呢?
坎伯: 堅持你對自己的理想,就像天行者路克一樣,拒絕系統強加在你身上的非人性要求。
莫: 我帶我兩個兒子去看《星際大戰》,故事來到最後激戰的最高潮,肯諾比的聲音對天行者說「關掉電腦、關掉機器、自己來做、遵循你的感覺、相信你的感覺」。路克這麼做了,他成功了,我的兩個兒子和所有觀眾一起大聲鼓掌。
坎伯: 你看,這部電影確實有在跟年輕人溝通。它是以年輕人的語言來和年輕人交談,這點很重要。這部電影要問的是:「你要做一個有良心、有人性的人,因為那是從『心』而來的生命之所在,還是要依照所謂的『意志力量』所要求的去做呢?」肯諾比說的「願原力與你同在」, 指的是生命的力量與能量,不是設定好的政治意志。
莫: 我對原力的定義感到好奇。肯諾比說:「原力是所有生命產生的能量場。它環繞著我們,它穿透我們,它把宇宙銀河結合在一起。」《千面英雄》中也針對世界臍心、神聖處所、創世剎那的力量有類似的描述。
坎伯: 是的。當然,原力從內部移動而出。但是帝國的原力卻是立基於征服並統治的不良意圖上。《星際大戰》不是一齣簡單的道德劇,它講的是生命的各種力量;透過人的行動,這些力量或得以實現、或被打破和壓抑。
莫: 我小時候讀的《圓桌騎士》就激起我的「英雄夢」。我想要出征屠龍,我要到黑森林中斬殺邪魔。神話讓奧克拉荷馬農夫之子「肖想」成英雄,這點你有什麼看法?
坎伯: 神話啟發你的覺察能力,你知道自己的完美、力量的圓滿,以及把陽光帶入世界的可能性。斬殺龍怪便是斬殺闇黑事物。神話從內心某處抓住了你。小時候,你能做的有限,像我就只是埋頭讀我的印地安人的故事。後來,神話可以教給你的愈來愈多。我想任何曾經認真鑽研宗教或神話概念的人,會告訴你,我們從小便在某個層次上認識了神話,但是之後會有更多層次被揭「密」出來。神話的啟示是無限的。
莫: 我如何斬殺我內在那隻龍怪呢?什麼樣的旅程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去經歷的?是你所謂的「靈魂的最高歷險」嗎?
坎伯: 我給學生的總原則是「遵循你內心直覺的喜悅」。找出它,然後勇敢去遵循。
莫: 它是我的工作還是我的人生嗎?
坎伯: 假如你做的工作,是因為喜歡而選擇的工作,那就是了。但是假如你想:「喔,不!我不能那樣做!」那就是你內在的龍怪鎖住了你。「不,不,我不能成為一個作家」,「不,不,我做不了某某人做的事」。
莫: 就這點而言,和普羅米修斯或耶穌這些世紀英雄不同的是,我們不是走在解救世界的旅程上,而是要解救自己。
坎伯: 但那樣做的同時,你救了這個世界。生氣蓬勃的人就會帶來充滿活力的影響,這點是毫無疑問的。沒有靈性的世界是一片荒原。人們總是認為,改變事情、改變規則、換一個當家做主的人……才能解救世界。不,不!任何有生氣的世界都是「正確」的世界。要緊的是帶入生命。而唯一的方法,便是根據你自己的情況,找出你的生命所在,並活出自己的生命力來。
莫: 當我上路去斬殺龍怪時,我只能靠自己嗎?
坎伯: 假如有人可以幫你,那很好。但是最終一擊還是得靠自己完成才行。就心理意義而言,龍怪是自己對自我的一種執著。我們被拘囚在自己的龍穴中。精神科醫生要解決的問題是「瓦解」那隻龍,把牠剖開,好讓你有更廣闊的人際關係。究竟之龍就在你心裡,是你的自我把你壓制住了。
莫: 自我是什麼?
坎伯: 你認為你想要的、你願意相信的、你覺得自己負擔得起的、你決定去愛的對象、你認為你應該執著的。它也許毫不起眼,但它可以把你釘死。假如你只是照周遭人所說的去做,你就一定會處處動彈不得。那些人便是從你的內在反射出來的龍怪。
莫: 我喜歡你在提到西修斯和阿麗亞德妮這則古老神話時說的話。西修斯對阿麗亞德妮說:「假如妳能指引我一條出迷宮的路,我將永遠愛妳。」所以她給他一個絲線纏繞成的球,他進入迷宮時也一邊打開,最後只要按照原路出來就好了。你說:「他所有的只是那絲線。這是你需要的全部。」
坎伯: 那是你需要的全部——阿麗亞德妮的絲線。
莫: 有的時候我們會期待有巨大的財富或強大的力量來拯救我們,或是偉大的觀念來救我們,然而我們所需的只是那條絲線。
坎伯: 要找到並不容易啊。但有人給你線索,是件美事。那是老師的工作,幫助你找到你的阿麗亞德妮絲線。
莫: 像所有的英雄一樣,佛陀並沒有告訴你什麼是真理本身,他告訴你通往真理的道路。
坎伯: 但是,那必須是你自己的路,而不是他的路。例如,佛陀無法告訴你如何去除掉你自己特有的恐懼。不同的老師會有不同的建議,但它對你很可能不見得有效。老師所能做的只是建議。他像一座燈塔般指出:「那裡有岩石,離開它。外頭那裡有條航道。」
任何年輕人生活中會面臨的大問題, 就是在找出能夠啟發自己未來可能性的模式。尼采說:「人是病態的動物。」人是不知道怎樣處理自己的動物。心識有許多可能性,但我們一生只能活一次。我們該怎樣「處置」自己?一個「活」神話就能帶出多個當代的生活模式。
莫: 今天,我們擁有無窮可能的各種模式。許多人最終試了一堆模式,還是一點都不清楚自己是誰。
坎伯: 當你選擇職業時, 你實際是選擇了一個適合你的模式, 至少可以撐好幾年。例如, 一個人過了中年以後, 別人就很容易分辨出他的職業為何。不論我走到那兒,別人都知道我是教授。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做了什麼,或是看起來的樣子,但是我也看得出教授與工程師、商人的不同。你是被你的生活所塑型。
莫:《亞瑟王》的故事中有個很棒的意象。當時圓桌騎士正要進入黑森林中尋找聖杯的下落,說故事的人說:「他們認為成群結隊走進去是降格之舉。」所以每個人都分別選了自己的入林點。你的詮釋為:這個故事表現出「強調個人生活之獨特現象」的西方觀點,每個人都要獨自面對黑暗的挑戰。
坎伯: 當我閱讀十三世紀《聖杯的追尋》一書時,讓我有所啟發的是,它概括了一個西方特有的精神目標與理想,那就是,只有你可能把你內在的潛力表現在生活中,其他人都不可能。
我相信這是偉大的西方真理: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生命,假如我們要獻給這個世界禮物,它一定是出自我們自己的體驗,出自自我潛能的實現,不是任何其他人。另一方面,在傳統的東方,以及所有強調傳統的社會裡,個人就像用模具製造出來的餅乾一樣。他的責任絕對而精確地加在他身上,不可能打破。當你找上宗教導師尋求精神指引時,他只知道一些老套的做法:依據傳統,你現在在哪個階段、下一步該去哪裡、你該怎麼做才能達到目的等等。他會讓你有樣學樣、看起來像他一樣。那可不是西方認可的教學方式。我們必須讓學生依照自己的樣子發展,老師則在這個基礎上給他們指導。一個人在生命裡必須尋求的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必須是從他自己獨特的經驗潛能所產生的東西,是他自己獨一無二且空前絕後的經驗。
莫: 那是哈姆雷特問的問題:「你面對了你的命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