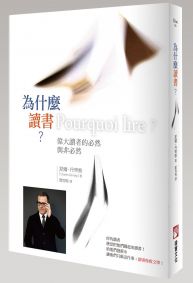【只因愛而讀書】
On ne lit que par amour
如果要在本書結束之前說出來——其實我既反對宣稱終結一切的結論,也反對自以為證明了一切、其實引起懷疑的引言——歸根結底,假如我們博覽群書,我們定是因為喜愛才那麼做。我們由喜歡人物開始;接下來是喜歡作者;最後則是喜歡文學。文學這位女王正是我們的永恆追求,我們伸長脖子、張著貪婪的嘴,朝著那個純淨而炫目的新鮮感匍匐前行,我們曾在早期閱讀時體會到那種新鮮感,現在卻再也感知不到,即使我們感知到了,也有可能是錯誤地感知到了憂傷。我們失去了童稚,但同時也不再無知。如果什麼都未讀過,那麼有著最微不足道丁點才華的人在我們眼中都成了帕華洛帝。我想,當探險者剛剛走進原始叢林時,他會對自己遇見的第一隻千足蟲驚歎不已;可是,當他在森林裡跋涉數月之後,在他到達林中空地,看到仙女們在那裡隨著琴鳥的吟唱翩翩起舞時,他不會失去感覺而無動於衷。即使我們讀了很多書,閱讀的數量也不會使其品質有所折損。
童心未泯的讀者常常是文學魅力的締造者。很多讀者都童心未泯。正是這樣的讀者把小說變為暢銷書。那些內心依然是少女、依然夢想愛情的婦女為純純蠢蠢的言情小說帶來了三十萬冊的銷售量,小說醫治了她們的痛苦——由於嫁了一個胳膊肘撐在桌上吃飯言行舉止粗俗不堪的丈夫而產生的痛苦。而那些思想仍留駐於少年時代的男人們則放棄法國電視一台轉播的足球賽,去讀一些鼓吹世界末日論的笨蛋炮製出的幻想小說。
有時候,乾巴巴的知識給溫柔的(溫柔的:優點)愛套上了雙重的挽具,於是從愛這匹雪白駿馬的玻璃鼻孔裡噴出的白氣(啊~這種寫得糟糕卻自欺欺人地認為寫得好的邪惡樂趣)使我們喪失了質樸純真。而這就是為什麼那些聲名卓著的讀者變得越來越吹毛求疵的原因,他們在尋覓某種稀有的滋味,那種滋味十分強烈,能讓他們在讀過的書越來越多感覺卻越來越少之後重新感受到某種東西。他們就是一些身處沙漠之中、口乾舌燥得即使有整船整船的涼水也無法解渴的人。要喝水!要喝水!他們邊喊邊用力扔掉1868年的狄金森酒杯和1350年的薄伽丘香檳酒瓶。
【為了憎恨而讀書】
Lire pour la haine
某些人是出於憎恨而讀書。這是一些嫉妒同行的作家和嫉妒所有人的批評家。前者反覆說:「我們不讀自己寫的書,我們這是相互監督。」高尚的慷慨。我想他們看不起馬樂侯1:有一天,有人把一位年輕作者剛剛寄到伽利瑪出版社的手稿轉給他,他邊讀手稿邊拍著大腿說:「啊,這個小夥伴!啊,這個小夥伴!」(這是貝爾勒2講述的逸事。)那位年輕作者有可能寫得如皮埃爾∙德里厄∙拉羅薛爾3一般糟糕,但這是另一碼事。馬樂侯有可能喜歡他的某種文風,德里厄式的文風,況且德里厄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作家,而這類作家出現時會顯得很現代。馬樂侯曾寫過《蔑視的時代》,將人分為兩類,喜歡蔑視他人從而產生苦澀滿足感的人和甚至連想都未曾想過那種蔑視的人。後一類人瀕臨滅絕。我們也可以把人分成憎恨和不憎恨馬樂侯的兩類。對馬樂侯的憎恨,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一直代表著某一類人。然後那個時期過去了。正如卡繆。在1955年,不喜歡卡繆可能意味著(法西斯主義或極權式的)無人性;在2010年,卡繆曾表明過立場的那些政治論戰早已偃旗息鼓,不復存在,除了存在於某些人的思想意識中,這些人經歷過那段歷史並且緊緊抓住不放,因為他們無法想像有反對卡繆的文學論據。或者可以說,有一些八十五歲的老人仍然耳聰目明。
作家,根本是群敗類!一個充斥著欲望的大染缸。我相信自己寧願成為劇作家,他們不那麼互相厭惡,如果我們信賴《潛在的異性戀者》(The Latent Heterosexual,1968)的作者帕迪·查耶夫斯基4的話,我要讀一讀他的這部作品。安東妮亞·富萊澤5在《你一定得走嗎?》(Must You Go?,2010)中談到了查耶夫斯基的這部作品。《你一定得走嗎?》是一部關於她與哈洛德·品特(Harold Pinter)婚姻生活的日記,很有趣,很好看,可能有點過火。其中兩頁或許可以成為對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現的「魚子醬左派」6這個西方小幫派未來的總結:英語系師生戰戰兢兢地接待一位後來成為當地小國元首的南美革命者——尼加拉瓜的丹尼爾·奧蒂嘉7。這些人的純真並不令人厭惡,因為它出自把事情做得令人滿意的良好願望,而他們一貫反對社會進步的言行有時是源於輕蔑的想法。
由於想找出一個嫉妒的批評家作為例證,又沒有太多這樣的人,我花了數天時間閱讀某雜誌登載的文章,我告訴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這樣的評論家。我找到了,可是並不因此感到高興。這就好像翻過垃圾箱一樣。我發現了一個十分擅長評論他人文風的女批評家,她的文章如同一觸即怒的女中學生的作文,而且由於她用語粗俗地寫些平淡無奇的文章,因此自以為有透徹的洞察力。她喜歡攻擊作家。那些攻擊我們的人並非都那麼有才華。正因如此,他們常常只剩下庸俗了。為了彌補自己欠缺的理性思考,她用「我們」這個人稱寫作。「我們」,她供稿的那本雜誌的「文化」版面,強迫那些分外難以忍受此類宗派作風的人接受她的欺世盜名。瞧瞧一個跳梁小丑到底如何自以為聖賢。世上就是有這樣一種既平庸又惡毒的讀物。我對那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沒有任何興趣,所以我把它們留給道學家們去研究。
【為了手淫而讀書】
Lire pour se masturber
在一本我家世代相傳的宗教書裡,我看到了地獄。廣闊,壯麗,擁擠。魔鬼坐在版畫中央的王座上,十分平靜。卻更具威懾力。靈魂在他下方的七個洞穴中受盡折磨,每個洞穴代表一宗罪,分別以烏龜、鏡子等等做為象徵標誌。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我萬分恐懼,卻不斷地反覆觀看那幅版畫。地獄富有魅惑力。這正是人們指責它的地方,因為它並不存在。生活如此無聊,恐懼或許能成為年少時期理性的有益補充。
成年之後,性的地獄也具有同樣的功用,只不過它始終比較隱秘。比如我從前就不知道國家圖書館曾用一個特殊的編碼把館藏的色情書都隱藏起來了,那就是「地獄」。其實沒這個必要。色情文學早就得到了解放。我上高一時,同學們在課桌下傳閱著薩德侯爵1的黑色封皮袖珍本小說,那些書由於被多次翻閱就像煮熟的朝鮮薊一樣大敞著口。多麼巨大的文學熱情啊!沒過多久我就明白了這位作家的真實作用,不過我覺得他的寫作方式太隱晦了。其實我錯了:他的文筆較為拙劣,居於同時代作家的中等水準,至於他的作用,則不僅僅是供人自慰而已。在那樣一個到處都是賣弄學問的教授在歇斯底里地聲稱「一切均為政治」的時期,性成為革命的一部分,它順應了時代的發展。性的愉悅被否定了,還有呢?它本質的輕,它的無拘無束。於是反對虛偽的爭鬥使用了最虛偽的手段。人們並非為了肉體享樂才想到把地獄之門打開。
但至少地獄之門被打開了,而且,根據以往的作家可能帶給我們的新用途來時常重新闡釋他們的作品並非壞事。這使他們重新煥發出生機。不只一位中規中矩的作家因為過世後出版的放蕩不羈書信而變得更親切可愛了,哪怕這令他們失去了那些因循守舊的老主顧。而這些主顧總會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作家來取代另一位,被取代者會被毫不留情地遺忘。假使我根據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我品嘗一種從未釀出的美酒」(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出版一部就其詩歌作情色闡釋的著作,那麼我會更新對那首詩老套的唯靈論詮釋。我的闡釋或許沒什麼道理,但我會重新激起公眾對狄金森的興趣。這正如劇院上演的老劇碼,它們常常令年齡各異、對該藝術感興趣或買得起票的老朽們詛咒連連。然而再赫赫有名的劇碼數十年之後都會變成民間傳統藝術博物館的展廳,重排上演則能讓這些展廳通風透氣。花邊連衣裙飛了,帶短面紗的女帽跑了,房間裡的霉味消失了!哪怕最後只留下一個光屁股蠟像,人們所做的也不僅僅是熬過了一場演出。作家們如同河流改道一樣被改變了方向。這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好事。當我想到,後世其實就如同現世,聽煩了相同的東西一直重複便更換了讀物,我打算留下幾部我希望能夠出人意料的遺著來震驚後世。我以前的讀者會對這些作品失望;未來的讀者,會高興於反駁前人的話語並有新的發現,他們可能會說:「他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只有我們理解他。」這會是不公平的,然而如果您認為後世就是公平,那麼我勸您立即自殺。
文學超出道德層面以外。這一切都是老生常談,早已聽過,令人生厭。但這也在變化中。在法國2007年的第二輪總統選舉中,我們有兩位提倡各種「價值」的總統候選人。2010年的匈牙利、荷蘭、比屬佛蘭德斯的議會選舉裡,最反動的政黨贏得了選舉。他們有著小丑般的政治綱領、選舉活動、行為舉止,甚至當他們失敗時都沒停止小丑行徑。在斯洛伐克,民族主義黨派沒有獲勝,他們的首領氣惱地公然宣稱:「同性戀和匈牙利人將統治這個國家。」這些小丑都夠嚇人的,不是嗎?在美國,共和黨創造出一個女丑,依靠某些極虔誠的、強有力的種族主義宣言,她注定要集中那些聖西門所言的民眾渣滓(此處指小資產階級渣滓)的意見。像弗蘭肯斯坦創造的怪物一般,莎拉·裴林或許會成功地脫離創造她的那些人成為美國總統,那時人們就笑不起來了。我們這些其他文明人知道小丑會置我們於死地,所以要立刻打敗他們。
然而,當它發展壯大起來後,當它變得容易顛覆,並且逕直朝著徹頭徹尾的國家革命的方向發展時,他們會為時已晚地發現任何事情在初期都不應被看做微不足道,因為蔑視它並不能阻礙它發展,時間的持續性也毫無疑問地可以使它迅速變得重要起來。
普魯塔克2,《凱撒傳》(Vie de César)
一股三十年代的風吹過整個世界3。這看起來很不妙。那些「價值」的捍衛者們能夠辨別一本書中的色情成分和文學成分嗎?此外,我們要警惕某些人所說的相似,因為相似常常由於我們希望看到它才存在;也要警惕某些人對現在和過去進行的種種類比附會,真正的危險其實就在這些附會背後,它並不完全與過去相像,並且無需採取有用的行動就會不斷發展。我不知道有用的行動是什麼,可是,在我們這個既瘋狂地禁止又摻雜著保守與齷齪的世界裡,我如同《巴馬修道院》裡的布拉奈(Blanès)神父一樣,感到某種奇特風潮的來臨。
社會有關性慾方面的態度如此虛偽,以至於有些人本來出於刺激的目的買書,卻買到了一些完全無關的書。《慾望·巴黎–凱薩琳的性愛自傳》(La Vie sexuelle de Catherine M.)是凱薩琳·米雷4嘗試根據自己交換性伴侶的經歷進行的文學創作。這本書之所以創下了數十萬冊的銷量,或許僅僅因為購買這本由信譽卓著出版社發行的圖書的讀者們是一些色情狂,他們不用兩眼瞄著背後悄悄溜進性用品商店就可以在書店買到這本書。他們對這本書所能引起的性興奮一定極為失望。
某些開始寫性的小說作者的問題,在於他們聽任自己的執念來駕馭自己的作品。那個人喜歡小姑娘,好吧,這想法侵襲了他的頭腦,但他卻沒能控制;而文學作品的目標之一——即賦予情感一種形式而非向其強加一種形式——由於一個陰險的催人興奮的目的而遭到遺忘。讀者瞭解這一點,鄙視那本具有功利性(而且可能對讀者自己也是如此)的書。
一位作家朋友在尋思為什麼無法成功地寫出一部包含色情段落的文學作品。這大概是因為色情作品屬於目的性的作品,而文學則是非目的性的作品。正是同樣的原因阻止了兩者的融合,阻止了色情文學的出現。色情有其功能,文學則是一種情狀。
語彙的繁多是導致兩者無法融合的主要因素之一。到底是怎樣的奧秘使得性成為唯一擁有眾多詞彙的人類活動,甚至性器官也是唯一擁有好幾個相關詞彙的人體部位?只有一個詞語來表示「脖子」或「耳朵」;而一談到性,我們的腦海裡馬上浮現出分屬於各個不同語級的詞彙。以「陰道」、「小穴」或「屄」三詞為例,可知其分屬醫學用語、下流話或粗話。人們似乎無法單純地談論性。我暗自思量是否可歸因於羞恥之心。
想到把國家圖書館色情書籍命名為「地獄」的那個人是誰呢?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還是信念堅定不移的人?是一個面頰鬆弛、彎腰駝背、每天晚上回到家可恥地朝借來的書手淫的人,還是一個年輕的、快活的、在一次會議上為了嘲笑某個假正經的保守者而提出如此建議的愛開玩笑的人?這能成為一本小說的主題。世界各民族的語彙便是這個世界的小說。
【為了不令逝者長眠而讀書】
Lire pour ne pas laisser les cadavres reposer en paix
讀者不像自己想像的那般被動。從傾聽獨白的角度看來,閱讀是一種對話。所謂對話,一般是指聽眾時而著迷時而耐心地傾聽的精彩獨白。在閱讀過程中,某個昏昏沉沉的思維被一個看似消極的思緒調動了起來。只是看似消極。其實它很活躍,因為那些感性與記憶機制。它會選擇那些能觸動思維的段落。讀者在其中重新發現了文學的感性特徵。文學與它那瘦弱的堂妹(即讀書)有一個相同之處,那就是引起共鳴。被書寫或閱讀的文學語句與其他領域的書面語句所不同之處,就在於這種共鳴,它源於文學的不純粹性本身。
我常常傾向於以詞語的原意而不是在使用中衍生的涵義來看待它們,可是我錯了。人們在使用過程中,為大多數詞語遮上了一片彩色濾光鏡。如果我在用詞時不特意說明自己不曾考慮到這一點,人們就會將那些詞語看作彩色的,而唯有我一人以自己所理解的意思來看待它們。我可以說,由於我常常這樣使用詞語,使用最貼近其原初成形時的涵義,這樣造出的語句會引起讀者們的些許好奇心,令他們流連於這些語句;於是他們會理解它們;他們會欣喜於自己的理解勝過旁人;這麼一來我簡直可以成立一個行家俱樂部了。這樣的俱樂部有時候可能有上百萬的會員,都像普魯斯特那樣。但只要知道俱樂部最初不過千把人就足夠了。多麼自命清高而又天真的想法。其實也沒那麼嚴重。應該說這個想法帶有某種日本式的情感特性:我們這幾個人在致力留存一個比我們更重要的微妙事物。提到「不純粹」,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混雜」,如同液體可以變得不純。文學的不純粹源於文學把說理和可笑的情感摻雜在一起。由此形成它如此特殊的形式。我是說通常情況,即文學是摻雜著情感的文字。我不相信有這種「風格」,即每一位優秀作家都有絕對屬於他的表達方式。「我」常常自以為獨一無二。然而,這些「我」分屬於不同的類型。人是神聖的,然而人的個性屬於不同的組合;當然存在某些細微差別,這些微末差異使得每個人都真正成為一個無可替代的人(這是我們反對謀殺的主因之一),然而這並不足以說:「給我一個句子,我就會辨認出那位作家。」我們可以認出那個(熱情的、暴躁的、有報復心理的……)類型,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然而為了辨認該作者是何人,還需要瞭解其思想。是啊,優秀作家都是擅於思考的作家。而這正是普魯斯特那一類文字極為稠密作家的作品可能會招引無限評論的原因。個性天差地別的讀者們都能在其中找到令自我滿足的東西。評論又再生發評論,因而形成了對創造性閱讀的神化,將其等同於猶太教法典般地信奉它。
因此我們應該小心避免書籍變成《聖經》。我們並非因信仰而讀書,作家並非神祇。我們可以熱愛書籍卻粗暴地對待它們,我想,我們甚至必須這樣做。我不贊成讓死者安眠。一位聽憑他人將自己安葬於地下的死者最終將走向永遠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