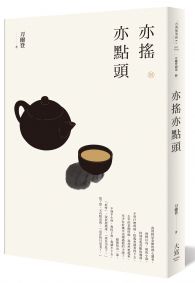誰讀完了《尤利西斯》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送給我一本《倫敦塔祕密動物園》(The tower, The zoo, And The Tortoise)。他喜歡這書,送我一本,自是希望我閱讀,然後同他討論。我隨手翻開《倫敦塔祕密動物園》,看到這樣的描寫:
「她把外套掛在衣架上,旁邊是個真人大小的充氣娃娃,嘴巴是個深紅的洞,這件物品還沒人敢認領。繞過轉角,她站在舊式維多利亞櫃檯邊,櫃檯門還是關著的……」
又翻開一頁——
「別的還有哪些呢?一隻科摩多龍,來自印尼總統。科摩多龍是世界最大的蜥蜴,可以打趴下一匹馬。它們是食肉動物,咬起來很兇猛,會往獵物身上注入毒液。所以我會留意那只動物,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鼻子裡哼了一聲,把書放在一邊了。這一「哼」的意思,不外是說,這是哄小孩兒的。在我看來,作者的描述有過多的「冗餘」細節,意在迷惑意志不那麼堅定的讀者;而我,自詡為老練、世故的讀書人,才不買帳呢——如果與情節無干,誰在乎娃娃的嘴巴是什麼顏色呢?
然後我就絕望地想,天哪,我真是老了。
這話是從何說起呢?如果是在四十年前讀到這樣的段落,我的眼睛會發亮!我會追蹤、玩味每一個細節。科摩多龍!這名字就足夠讓一個孩子的想像飛馳一會兒了,我會停下閱讀,在腦中構造「打趴下一匹馬」的畫面;這一小段話,夠我享受好幾分鐘,咯咯笑好幾次。經驗是如此排他,現在的我,頭腦塞滿辛苦積攢起來的各式法寶,從而只會「哼哼」,不會「咯咯」了。
在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第四章中,布盧姆磨蹭半天,總算要出門了:
「在門前臺階上,他伸手到後面褲袋裡摸大門鑰匙。沒有。在昨天換下來的褲子裡。得拿。馬鈴薯倒是在。衣櫥吱吱格格響。沒有必要吵她。剛才她翻身的時候就是還沒有睡醒。他很輕很輕地把門拉上,又拉緊一點,讓門下端剛夠上門檻,虛掩著。看來是關著的。反正我就回來,沒有問題。」
還記得那個「木枷,文書,和尚,我」的老笑話嗎?我現在外出,關上家門之前,總要摸一摸口袋。鑰匙永遠是放在左邊褲兜裡的,右邊則是電話,上裝右面口袋裡是錢包(現在的扒手不讀文章,對吧?),左面有香菸。「鑰匙,電話,錢包,菸。」我心裡念叨著,放心地下樓了。親愛的讀者,您也這樣嗎?如果是,那麼恭喜,您也老了,您和我一樣,對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的外部世界,丟掉了興致,您和我一樣,每天出門,實際上一直留在門內。
在我還是個小不點兒的時候,從外祖母那裡聽了好多故事。有這樣一類故事,主人公(通常是個傻氣的老三)被父親或壞心眼的兄弟趕出門,一天之內,或是遇見三件美事,或是學會了三句妙語。這些年我沒少外出旅行。而每次旅行快結束時,我都在心裡嘀咕:「人家傻小子出去轉悠一天,還學會了三句話了。我都出來一個月了……」
可別小看那類故事,它們屬於一個偉大的敘事傳統,這傳統的代表,在我國有《西遊記》、《水滸傳》,有《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等,在歐洲,則有近代小說之開端最顯赫的一批作品,《巨人傳》(Gargantua and Pantagruel)、《小癩子》(The Life Of Lazarillo De Tormes)和《唐吉訶德》(Don Quixote),有後來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痴兒西木傳》(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吉爾.布拉斯》(The Adventures of Gil Blas)、《湯姆.瓊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有美洲的《癩皮鸚鵡》(The Mangy Parakeet)、《頑童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以及《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和《奧吉.瑪琪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如果限定不那麼嚴,還得算上我從小就熟悉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以及曾很想讀卻至今沒有讀過的《克萊麗莎》(Clarissa Harlowe,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還得算上小木偶(Pinocchio)和愛麗絲。這書單子可以開得很長,這傳統可以追溯到偉大的荷馬(Homer),然後繼續上溯,直到我們祖先的祖先,那最早的一批說故事人。
最早的一批說故事人……他們說什麼呢?他們才不會說,「我今天早上,吃了兩個煎餅……」,他們的故事,應該很像《奧德賽》(Odyssey)的開頭,說的是一個人「飄遊到許多地方」,見到了許多在家中見不到的事物。是什麼令我們的祖先守著爐火,眼睛閃光,聽一個傢伙絮絮叨叨地說話呢?這人是外邦人,傳令人,還是還鄉浪子?他的故事,像拋進波瀾不驚的生活裡的石頭,激起了什麼樣的漣漪呢?這些漣漪傳到了我們這裡,減弱至什麼程度呢?
說起《奧德賽》,想起了《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的威名,是在大學裡聽到的。那會兒,歐美現代文學,剛剛擠進門縫兒,而其影響力,又絕不僅限於中文系的學生。「現代派」,對差不多所有人來說,都是有魔力的詞兒,我們像在山洞裡沉睡多年,醒來後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要趕上時代的進度。短短幾個月裡,每人都知道了一大批作品和作家的名字,急不可待地等著譯作。譯作出得很快,但無論如何,也供不及這批貪婪的學生——我們恨不得在一年之內,把所有的好東西都讀到,彷彿讀到之後,便成「現代人」,與世界齊頭並進,而甩開周圍的人幾十步了。
完整的譯本,來不及提供,便有些選段,出現在選本上,好比有口皆碑的餐廳,讓香氣飄到我們這些排著隊、伸長脖子等座兒的人前,暫且慰藉大夥兒的饑腸。這些餐廳中,門口排隊最長的,便是《尤利西斯》了。
我們從各種評介中,得知它是多麼偉大,又是多麼艱深——高越而險峻,還有什麼品質,更能吸引攀登者呢?我在選本中讀過它的一小角,說老實話,完全不知所云,這讓我更加心嚮往之。圖書館裡有《尤利西斯》的英文原版,很難借到,不過我終於借到了。我那時的英文程度,根本不配閱讀《尤利西斯》,我壓根兒也沒有那痴心妄想,把它借到手,只不過是想看看它是什麼模樣,聞聞氣味,掂掂分量,在枕頭下壓一壓(或許希冀有什麼神祕的通道,能讓書裡的內容就近往腦子裡傳一點兒?),如此而已。
我的朋友圈兒裡,碰巧有《尤利西斯》的第一位中文譯者的兒子。在他父親著手此書的譯事後,每個假期過完,他從天津回來,我們幾個人,總要打聽一番,其實他知道的也不多,而他那副慢條斯理的樣子呀,真是氣人,我又不免擔心,他父親多半也是這個慢脾氣。可不是嘛,他老人家把譯作出版,是十年後的事了。
十年……我從「文學青年」,變成了一個三十歲的、受偏頭痛折磨的、得過且過的傢伙。尤為要緊的,是我已經停止文學閱讀了,就連《尤利西斯》漢譯本的出版,也是在又兩三年後,偶然得知的。我在朋友的書架上,看到了這譯本。此時我已經想不起當時的心情,也許心跳了一下,也許沒有,多半只是禮貌地瞥了一眼,或從書架取下,握一握手,寒暄兩句,又放回去。
我能不覺得自己老了嗎?
且慢。我想起了大學裡讀過的《麥田捕手》。主人公滿腦子想的「只是離開」,然後,「我一口氣跑到大門邊,然後稍停一下,喘一喘氣。我的氣很短,我老實告訴你說。」下面一段說抽煙和肺病的破事,接著,「嗯,等我喘過氣來以後,我就奔過了第二〇四街。天冷得像在地獄裡一樣,我差點摔了一跤。」作者用好幾行字寫霍爾頓過馬路時頭腦中的念頭。最後他總算穿過了馬路,「我一到老斯賓塞家門口,就拼命按起鈴來。」
我好奇的是,如果主人公在外面漫遊了幾年而不是幾天,這書得寫多長。
《麥田捕手》是我喜歡的小說。我喜歡現代文學的許多品質,佩服當代作家對人的精神細緻入微的探究,佩服這探究所需要的勇氣和觀察力,同現代文學相比,古典文學離真實世界——哪怕是古典世界——實在是太遠了。
但是……是啊,但是,我多麼嚮往古典時代的康健之氣。我甚至想過模仿前人的筆法,編一個記行的故事,可是呀,便是編得出來,那故事怎麼看也不像是當代生活的寫照,不管我用多麼實際的細節填充它。
打個比方,我連個陌生人都想像不出來。哪裡還有什麼陌生人呢?想像能遇見的最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我差不多敢保證,從他那裡聽到的一切新鮮東西,實際並不新鮮,他的生活細節,不過在我(這裡我很想使用「我們」一詞)那個木櫥的某些小格子裡,填上新的材料,而沒有什麼,令我覺得應該為其騰出新的格子,甚至新造一隻櫥子。
是的,新的法度,新的範式(這個詞兒倒是新的,我是頭一次用),太難得了。在一切皆為一切人所知(我們自以為如此)的時代,在邊疆已被推至人類暫時的極限的時代,我們可以坐擁事物的樣本,在實際地遇見事物之前,已經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而我們的旅行,從頭到尾都是設計好的。我自己的旅行也是如此,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坐在一個陌生的門廊下,看著陌生人從眼前走來走去,就是不想搭話,因為在我的感覺中,這一切都太熟悉了。這時我便沮喪地想:「我老了。」
「真實的旅行故事已不可能了。」李維史陀(Lévi-Strauss)曾經這麼寫道。他解釋說,我們會「把真實經驗用現成的套語,既有的成見加以取代。」那麼,從來就不曾有什麼「真實的旅行故事」,在古典時期,更加沒有。但這裡的「真實」是什麼意思呢,不管它是什麼意思,誰又在乎是不是「真實」呢?我們要講故事;我們要聽故事。
又過了幾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小書店偶又見到《尤利西斯》,我買下了。我在火車上讀了一些段落,回到家中,放在一邊了。剛才我想從書架上翻出它來,沒有找到。便是找到,十年前我沒有把它讀完,現在我更讀不完了。
如前所說,我「老了」,對眼皮底下的許多事,以及對描述這些事的文字,失掉了興趣。我知道《尤利西斯》是偉大的小說,但此時此刻,那不是我需要的那種偉大。我同意,有些時候我們需要把眼睛轉向自己,我們甚至可以津津有味地談論自己,但有些時候,我還是想聽故事,粗糙的故事,外邦的故事,包含新的精神法度的故事,我們的文明在其中流動不居的故事。
《十日談》(The Decameron)的故事是這麼開始的:十個人(還有一些僕人)到山中的一所屋子裡躲避瘟疫。他們講故事……不,換一個想像,想像一群人來到某處避雨,可是,他們再也不走了,他們太喜歡這地方了,就在這裡蓋房子,交往,婚娶,種植……他們對自己說:「雨還沒停。」是啊,有些雨,確實是永遠也不會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