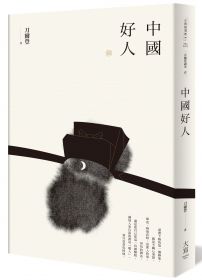【刀爾登作品集台版序】
冷靜的同情,克制的反思
文/胡又天
二○○七到一○年,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學位,每當路過書報攤的時候,就會買《南風窗》、《南方週末》、《南方人物週刊》、《三聯生活週刊》、《讀書》、《讀庫》、《財經》(後來被整管,原班人馬出走另創《財新》)這些時政與人文的雜誌。彼時雖然iPhone已經問世,但微信未出,社群APP的時代尚未全面到來,網上的精彩內容還分散在各個論壇和博客(網誌)中,實體版報章雜誌的市場還沒有萎縮得太厲害,甚且還在選題、編採、排版等各方面精益求精地進步著。應該說,一九九○年代末到二○一二年,是當代中國大陸報章雜誌最精彩的時候。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保改革開放路線不動搖,使言論環境漸漸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肅殺中回暖;江澤民時代,主要基調是經濟發展與「入世」(加入WTO),對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敏感議題,也放鬆了管制──或者應該說,發條鬆了,而體制內外大多數人,一時也還不想它再度栓緊,再加上網路開始普及,共產黨很清楚這是未來,不可遽禁,只能花時間去摸索如何管制。二○○二年換胡錦濤執政,大抵蕭規曹隨(包括可嘆的弊端及可喜的弊端),言論上也是比較被動的姿態,感覺到危險才會嚴肅的反應一下。於是,各個世代、各種思想的作者,察覺了這個空檔(或者說「過渡時期」),便紛紛大展身手,在體制容許的模糊範圍之內打「擦邊球」,藉由對過往的重述、對當下的記錄,探尋一個更好的未來,或至少是盼望著一個可以比較不一樣、不那麼「主旋律」的中國。
刀爾登便是在這個時期出名的作家之一。
刀爾登本名邱小剛,生於一九六四年,在文革的瘋狂與凋敝中度過了童年,一九八二年以河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然而他心性淡泊又帶幾分刁,並不以此為得意;一九八六年畢業,也不待在首都北京,而是回了石家莊的家,在河北社科院任職,一九九○年代末再到河北日報社旗下的《雜文報》當編輯。這些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單位,有識者或許會覺得屈才,而他既不喜爭競,一輩子或許也就這樣了。二○○一年,他和朋友被新來的領導「調離」,沒了體制內相對閒散的工作與生活;如果他下海從商,或許也能別有一番發展,但也可能就泯然眾人了。
他之所以成為了名作家,轉機在一九九九年左右開始在網上發表的文史隨筆。
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二○一○年代的最近,是翻案的時代,兩岸三地皆然:幾乎所有的一切都要被顛覆,至少也要面臨重新審視,特別是在牽涉當代政治的文史領域。其中有不少持論過激、翻案翻過頭的,雖能聳人聽聞於一時,但網路時代人人可吐槽,不久也就將引來同等的反駁,乃至流於令人厭棄的口水仗;刀爾登的文章,則沒有那樣的浮躁,講故事能自然流露出其閱讀的深度與廣度,作批評也總能細膩地引導讀者,不去執著於得出什麼正確答案或「真理」來踩人,而是讓我們能在各種殷鑑之中更加瞭解人情事理中的所以然,然後可以保育個人的自由,也讓社會能有更多同情和思考的餘裕。例如《中國好人》中的一段:
黨錮之禍,生出一批道德典範,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氣和正直,激勵過歷史中許多偉大人物。此役雖在社會生活中是大破壞,在道義上卻是一場完全的勝利;用良心或腎上腺與壞人作殊死鬥,從此成為一個模型,德昭千古。至於如何將權力鬥爭轉化為道德戰爭,不用很久也要成為拿手好戲,連續上演。
這可以說是從「得理不饒人」這句俗話,反過來切中了傳統史學和唯物史學都未能充分解釋的要害:傳統史觀格於士大夫的立場,天然地和學運站在一起(在台灣年紀稍大一點,讀國編本歷史教科書長大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當年課本是怎麼惺惺相惜地描述黨人的);唯物史觀則只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論述皇權、世家、豪強、寒門的利益矛盾與階級固化問題,將道德上的爭執貶抑為遮蔽真正癥結的煙幕,然而這種自傲於掌握了真理的姿態,往往便將經濟理性的今人和「蒙昧」的古人割裂了開來,喪失了歷史本應能讓我們培養的同情、共感(或曰「神入」)的能力。《中國好人》與《舊山河》這一集中的文章,便能通過作者潛心達致的共感,檢討中國史上這許多盛名累累的「好人」,是為什麼會將事情辦壞掉,乃至讓大局不可收拾,遺禍千年的。
刀爾登檢討國故,沒有五四運動以來急切揚棄傳統、盲目仰望西方的弊病(現在有一些為反中、反共而活動的論者仍只停留在這裡),也不走到一味擁護傳統、標榜傳統的另一個極端──這種人雖不顯眼,但也不太少,可嘆的是其中還沒幾人真有好好通讀過古書。刀爾登是真正讀過的,在二十來歲時自己大量閱讀經典和文集,打了底子,《亦搖亦點頭》便記述了他接觸中外文學的歷程與心得,書名一方面意謂豎排、橫排都看,一方面也是保持著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再一方面,也是體現他們一代人在世道幾度變更中的迷茫與恍惚。例如談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典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群己權界論》)時,他筆鋒一轉:
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秋天,在一個山坡上,與一個同學皺著眉頭討論:「……會不會變天呢?」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呢!是的,我們這一代人,本來是標準件,出自政治工廠。我們不知讀過及聽過多少正統的書籍、報紙、廣播,每天浸泡在其中,生長在其中,在小學時便寫批判稿,寫學習體會,訂閱《朝霞》、《學習與批判》,「關心國家大事」……如今我好奇的是,那一代人,是如何衝出這包圍的呢?
「好像沒費什麼勁。」我同一位老友談到這個問題,他這麼說。是的,好像沒有經歷過什麼嚴重的思想轉變,沒有經歷過可用「崩潰」、「重建」之類的詞來形容的過程,瓦解是安安靜靜地發生的,等想起來時,它已經完成了。(〈「密爾」路碑〉)
生為文革一代,刀爾登的文集不能不帶有對文革與專制的反思,事實上他的反思是深入到文化傳統根柢的,並且他謹慎地不貿然站到另外的極端立場去,只是綜合這半生的體驗,來為古老的問題吐納出自己的一番心得。《不必讀書目》這部談中國古代經典和文集的書,書名便首先對應了國學領域裡頗讓人難為情的「書單」老問題。
近百年來有不少學者開過國學書目,談論說為什麼必讀、應該怎麼讀,然後這個人說你這最低限度的書單還是太繁太多,那個人說你的讀法還是夾帶了太多執見,鬧得很沒趣。然而老一輩學者多少還真的讀過那些古書,過了兩代人,我們大多是修課時選個幾篇意思一下便罷,連參與這個話題的資格也沒有了,因而經常不能不自慚於底蘊不足,轉頭又吐槽別人不讀書或沒把書讀通,反正通常不會錯,就這樣用散發焦慮的方式來處理焦慮。
刀爾登的處理方式,卻是從「必」字著眼,針對了這種焦慮來作解說:確實讀過這麼多書的他,不跟你擺譜說你們這些小朋友快來拜師,也不去迎合某些人的便辟心理,說這些書不讀也罷(甚至「不讀更好」),而是點出他在諸子百家、歷代文苑之中所看到的執迷,讓我們可以不像前人一樣地失陷進去。並且,其中如批崇古非今、道德掛帥等等痼疾,感覺起來雖可能有些老生常談,但別人批判舊中國的崇古情結,多是站在發展主義、追求國富民強的立場上面;刀爾登的關懷,則總在於我們個性的解放,以及情志的舒展。例如:
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許自己處在愚昧中。假如我們同意,對廣袤世界最少經驗的古人,擁有最好的解釋,那麼,我們也就同意了,理性的目的是迷信,知識的目的是混沌,不可積累的高於可積累的,無可驗證的優於可驗證的,而且,我們還同意了,文明的方向從一開始就前後顛倒,是從終點駛向起點,其意義至多是保持人類的壽命,使其有時間達到古人已經達到的境界—愚昧。(〈不讀《周易》〉)
這既是針對後世玄學家將易經與儒術發展成的迷信,也是針對有史以來,思想怠惰使人們相互要脅著自欺欺人,乃至造成道德的禁錮,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是「在同溫層裡取暖」的情形,一如《中國好人》中的片段:
習慣於依賴愚昧,並從愚昧中發現出力量,體驗到快樂。田間地頭學哲學,工人階級上講臺,在這種「遊戲」裡,受傷害的絕不是知識傳統的本身,而是我們。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唸過書的人拿起什麼事來都敢胡說,我懷疑他們和我一樣,也是「批判」著過來的。(〈被小學生批判過的〉)
梁簡文帝曾說,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後人反是。自唐以後,聖道沒見到弘揚多少,國祚沒見到延壽多少,而文章倒成功地弄得無趣了。喜歡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詩,又逃詩入詞,逃詞入曲,又逃到小說,最後小說裡也全是大道,這時人們方心滿意足,吮大拇指而發呆矣。(〈庾信文章豈老成〉)
《不必讀書目》各篇標題以「不讀」開頭,其實當然不是不讀,而是不像教科書那般總要「主義掛帥」,牽強附會地將屈原說成愛國主義、李白說成浪漫主義、杜甫說成現實主義詩人,談《儒林外史》、《紅樓夢》則必云其如何揭露封建社會之醜惡云云(大陸教科書至今仍多如此,但台灣人請勿嘲笑,不少政論家在帶風向的時候,一樣是用這種強行說教的工具思維來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文學藝術)。刀爾登則脫去了教條,而能以個人的角度,帶領我們關注這些舊書真正值得細品的地方,就是「人」的處境:
偉大的《儒林外史》,講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證明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說服力是不夠的,但小說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活下去,怎樣把幻想維持下去,其中那慘澹的信心,是除了《紅樓夢》的讀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別人身上。(〈不讀《儒林外史》〉)
我們總是需要希望,即便只是一種「慘澹的信心」。這是冷靜克制的刀爾登並未放棄的溫情,他的反思不會走到徹底的絕望和否定,淪為「小人窮斯濫矣」、「破罐子破摔」的灰心喪氣,我相信這是他從文學裡得到的滋養,也是他想傳遞給我們的慧命。
二○一二年以後,以社群平台和營銷公眾號為中心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中共的網路管制趨於齊備,群眾在國勢日蒸的背景之下,亦多擁護中央以經濟發展為綱、民族主義為大棒──異議不是沒有,但已動搖不了境內的主流。仁人志士打了十幾年擦邊球,結果是中共劃出一條不得跨越的紅線了,報刊再也沒有了撬動政治、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可能,也就是不再那麼能令人「興奮」了,我也就漸漸沒再買大陸的實體雜誌,即使去年在大陸工作,偶爾買一兩本,讀起來也不再有先前的滋味。刀爾登隱逸的個性與文風,在這個新時代,自然是格格不入的,近年也很少再聽到他的消息,但或許這樣也好。
承蒙大寫出版相邀,為台灣讀者介紹刀爾登作品的時空背景,我也是首度拜讀了他文章的完整結集,而更接近了這位學長所閱讀過的,厚重、複雜而又保育著慘澹信心的古代、現代中國。大家在今日或者幾年、幾十年以後的將來讀到這幾本書,興許會很有一些恍如隔世的魔幻感:眼前的中國,居然也有過這樣的年月,出過這樣的作家。或者也不該說「恍如隔世」,而是真的隔了好幾世;然而,相隔百世的古人古書,刀爾登猶能有所共感,感知到那些不一樣的、失誤而真實、可貴的生命軌跡,我們也應該要能。謹為之序。
胡又天 二○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胡又天,北京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作家、歷史學研究者,著有《玩世青春》、《寶島頌》、《金光布袋戲研究》等作品。
文明墮落的一阻力
文/繆哲
讀者眼前的,是刀爾登君近十年來文字的一選集。其中有為遣無聊而寫的,有為逞狡獪而寫的,但多數的篇目,則是謀稻粱。刀兄懸的標準高,為了混飯吃,不得不卑其筆;對平日的所作,頗不自重。得虧喜歡他文采的幾個朋友的熱心,這些散出於報刊的短文,才結作一書冊的模樣,不復侷促於明星的花邊、富賈的野史與鴻儒的闊論間。
我與刀兄是相知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們一起讀大學,一起行走於某省的「南書房」,一起編報紙;在被人威脅奪下「五斗米」時,又「掛冠」而去,一道「回家再讀書」了。刀兄的學問淵博,識見敏銳,這使他在不大的朋友圈或口碑圈裡,成了受寵的人,與被懼怕的人;蓋在刀兄的面前,我們未免顯得愚蠢。他的天資,是舊友皆歎為不及的。記得我那一年高考,刀兄奪了鄙省的魁元;惟這一經歷,成了他「平生最大的不體面事」,人說必掩耳。蓋刀兄的性格,是羞與人爭的——而高考無非爭競而已。這個性格,亦使他在今天的瓦釜之鳴裡,自毀黃鐘,不思所作。即使有思,也懸鵠太高;往往剛一開頭,就拿心裡的尺子——我每告誡他「那可是量莎士比亞或王國維的尺子呀,哥們兒」——量自己,而每量必氣餒。故他的「有作」,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了。收入這集裡的文字,不過他棋酒的餘事,或混飯的勾當而已。
即便如此,這集裡的文字,也大有可觀了。就自然的作品說,人不多見山,多涉水,是不可稱某山高,某水廣的。人的作品,也須比長量短,方知高下。刀兄寫作的當今,是漢語史上最暗淡的一頁。人們所知的詞彙,似僅可描畫人心的膚表,不足表精微,達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懨懨如冬蛇,殊無靈動態。名詞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確地描述。動詞患了偏癱,無力使轉句子。形容詞、副詞與小品詞等,則如嫫女的豔妝,雖欲掩,然適增本色的醜劣。刀兄的文字,則是出乎其時代的。他的名詞有確義,動詞能使轉,小品詞的淡妝,更彌增其顏色;至若句式,則如頑童甩的鞭子,波折而流轉。故刀兄的友人們——包括我自己,都素重其文,稱是「文明墮落的一阻力」。這或是愛屋及烏亦未可知。但人之得益於私誼者,是有時而盡的;人所主張與反對的,也有過時的日子。到了那天,人們評判文字的好壞,將不復以激情,以偏見,而僅以品質。刀兄的友人們於今天的感受,想那時必多共鳴的人。
語言與人心或文明的關係,是古來的老話題。奧利弗‧霍姆斯(Oliver Holmes)論伊莉莎白王朝的語言說:「語言腐壞了。臭氣還薰染了英國的良心。」這是以語言的腐敗,為文明腐敗的禍首。《漢書》稱「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則又以語言的腐敗,為世風腐敗的一後果。歐威爾(George Orwell)也稱語言的愚蠢,為起於思想的愚蠢。則知語言與精神的好壞,雖不知孰為表,孰為裡,然互為表裡,是可得而言的。今天漢語的污濁,亦自為精神污濁的一表徵。雖挽狂瀾於既倒,是個人力不能勝的;但刀兄於驅遣文字時所表現的「潔癖」,亦自為精神之「骨氣」的宣示或對文明之信仰的一宣示。在他的清峻的文字下,是思想的通脫。如這集裡所論的,大都為古事;然所見每與我們聽說的不同。常人論以道德、善惡者,刀兄則論以平恕。此即《紅樓夢》所稱的「人情練達,世事洞明」,——雖然刀兄對《紅樓夢》一書,是素來鄙薄的。這個思想自周氏兄弟以來,即有人提倡之不遺餘力,但今天我讀刀兄的書,仍有孤明先發之感,由此也知我們思想的不長進了。
二十多年來,我與刀兄同居一城,衡宇相望,是頗感慶幸的。因我們所居的城市,粗鄙如「頭曼」;可與語者,舉目而寥寥。魚之大幸,固是相忘於江海,但陸處於涸轍,也不得不欣喜有相濡以沫者。但我遺憾的是,刀兄不自惜其才,「市也婆娑」,精力多耗於遊耍了。言畢不免「當奈公何」之感。
二○○八年末,於石家莊「數他人之寶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