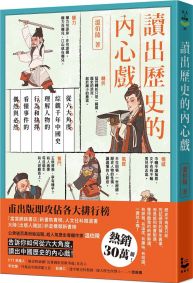安史之亂:大唐盛世的一顆毒瘤
大唐天寶三載,天下太平無事。李白被唐玄宗取消關注,落寞地離開長安,然後在洛陽巧遇杜甫。兩雙溫暖的大手緊緊握在一起,碰撞出一段佳話。他們一起在河南求仙訪道,秋天又遇到了高適,三個人每天除了喝酒閒逛,就剩下作詩了。
為大唐工作五十年的賀知章,也騎著小毛驢回浙江老家了。此時,離生命的最後時刻不過半年。
大明宮中住著李隆基,太真觀裡有楊玉環。一年後,他們將走完世界上最遙遠的旅程,向天下宣佈他們的愛情。楊玉環的哥哥楊國忠仍然默默無聞,但後來他踩上了一條光彩大道,走向了自己也不清楚的未來。
右相李林甫在朝堂隻手遮天,每次發朋友圈都能收穫上萬點贊,然而,他都懶得看一眼。幽州的安祿山春風得意,他剛剛接替裴寬擔任范陽節度使,再加上已有的平盧節度使、河北採訪使等職,大唐東北王即將加冕。
日後攪動風雲的人物都已各就各位,只是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將要面臨的是什麼。
大唐天寶三載,天下太平無事,所有人都在揮灑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們堅信,如日中天的大唐將永遠存在下去。然而,長安地下早已埋下了無數伏火雷,只等一絲火星。
天寶元年,長安城外的廣運潭熱鬧非凡。從渭河而來的三百多艘船在廣運潭一字排開,首尾連接數十裡,每艘船上都寫著大唐州郡的名稱,還有各地的土特產。
乍一看,彷彿是來長安趕集的。
唐玄宗在觀禮臺上就座後,三百多艘船依次從台前經過,接受皇帝的檢閱。潭中心有一艘船突然鑼鼓喧天,陝縣縣尉崔成甫扯開八十分貝的嗓門,唱著唐玄宗親自寫的《得寶歌》: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
潭裡船車鬧,揚州銅器多。
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
看看這詞,多感人,多喜慶,一股「啊,五環,你比四環多一環」的畫風,猝不及防地撲面而來。李隆基確實很開心,因為終於能吃飽飯了。
堂堂大唐皇帝不應該用金鋤頭種地嗎?怎麼會吃不飽飯?我跟你說,這都是真的。
開國初年,朝廷愛惜民力,再加上長安城人口少,一年只需要消耗二十萬石糧食。可在太平歲月,人們總是嚮往首都生活,當年在長安找機會的人,和如今的北漂沒什麼區別。
人口多,糧食需求就大。而造福秦漢的水利灌溉系統早已殘破,曾經接受灌溉的四.五萬頃田,被縮減到只有六千頃。唐朝的關中,早已不是經濟重心。
知道為什麼唐高宗、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嗎?人家不是去搞團建,也不是去旅遊,只是單純為了吃大米、烙餅、燴麵、胡辣湯……沒辦法,長安實在是沒糧食吃啊。
就在天寶元年,廣運潭把之前修建的運河連通起來,江南的大米可以直抵長安,並且當年就運來四百萬石糧食,李隆基能不高興嗎?
長安城解決了溫飽,可大唐依然是爛攤子。《舊唐書.玄宗紀》說:「天寶十三載,戶九八一萬,三八八萬不課,五三○萬課。口五二八八萬,四五二一萬不課,七六六萬課。」
然而,這串數位已經成為歷史學界的一段公案。從字面上來看,大意是:唐朝的財政稅收方式是租庸調制,納入這套稅收系統的人口叫課口,有課口的家庭叫課戶。
大唐登記在冊的人口中,四○%是免稅的,剩餘六○%人口交的稅要用在朝廷開支、宮廷用度、洪澇旱災上面,再加上在北、西、南三個方向同時開戰,軍費需求龐大。即便如此,正常的稅收管道都不一定通暢,往往需要朝廷派轉運使之類的官員,去地方上臨時疏通、壓榨,才能把錢糧運往長安。
大唐盛世如繁花錦繡,可朝廷只有兩個字:沒錢。因為國有土地制度崩潰了。
時間回到三百年前,北魏。
「五胡十六國」時代,北方混亂了一百多年,直至草原上的拓跋鮮卑南下,他們騎駿馬、挎彎刀,很快就征服了黃河流域。雖然北方統一了,可是有個問題:北魏朝廷沒有正規的稅收管道,官員也不發工資,大部分財政收入都來自於搶劫、賄賂或高利貸。
北魏太武帝年間,有一個朝廷官員到山西、河南一帶出差,從大同出發時,只有一匹馬,返程時卻帶了一百多輛車。這種行為我們叫吃、拿、卡、要。
四八四年,執掌北魏朝廷的馮太后在開會時說:「各位,有一好一壞兩個消息要告訴你們,好消息是,朝廷以後給你們發工資了;壞消息是,有工資以後,你們就不能隨便搶劫了。」大臣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那麼問題來了,朝廷也是靠搶劫為生的,倉庫中沒有餘糧,拿什麼給全體官員發工資?
不要急,有辦法。從西晉的「八王之亂」開始,北方的戰爭就沒有停止過。為了躲避戰爭,父老鄉親不得已到處流竄,這就有很多無主荒地和失業農民。馮太后把無主荒地全部收歸國有,按照一定比例分給失業農民,他們每年向朝廷交稅。這就是隋唐「均田制」的起源。
在這套系統下,門閥和貴族是免稅戶,只有接受國有土地分配的農民,才是國家的固定稅基。那麼,怎麼才能管理好國有土地和農民呢?
四八六年,馮太后的「男朋友」李沖建議:「可以在農村建立基層組織,一竿子捅到底。」於是,「三長制」華麗出爐。朝廷分五戶為一鄰,二十五戶為一里,一百二十五戶為一黨,分別設立了鄰長、裡長、黨長。這一套改革,歷史書上叫「太和改制」。
馮太后以國有土地為基礎,安頓了流離失所的農民,國家有了穩定的稅收,並且加強了基層組織的管理,在亂世中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秩序。
五十年後,北魏早已分裂為東魏、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建立了配套的「府兵制」,讓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員和軍隊。均田制、三長制、府兵制,就是接下來的隋唐帝國強盛的密碼。
這套制度有一個核心問題:朝廷必須持有大量土地用來分配。
我們且用初唐農民老王來舉例。當老王年滿十八歲時,就會有一百畝土地分配給他,其中二十畝是永業田,可以世代傳承;八十畝是口分田,去世後要還給國家。接受這塊土地,老王就是國家的納稅人了。
他一年四季勤懇勞作,然後按照「租庸調」的方式向國家納稅。每年交公糧兩石,給官府幹活二十天,還需要上交三丈布。這就是老王每年需要繳納的全部賦稅。
冬天到了,他也不能窩在炕頭上喝燒酒、看雪花,而是必須去指定的軍府參加集訓,以防將來可能上戰場。閒時為農,戰時為兵,兵農合一。
過了幾年,朝廷突然傳來命令:「聖人要和突厥開戰啦,你們跟我走。」於是,老王自備馬匹、刀槍等裝備,為國打仗。如果立功授勳,朝廷用勳田獎勵他;如果升官了,也有和級別匹配的職分田。
在這樣的體制下,老王和所有農民一樣,可以靠努力得到土地,朝廷可以用土地來調動百姓的積極性。
可在老王去世後土地要還給官府,能傳給兒子的只有二十畝永業田,相當於下一代重新開始。拼命一輩子,卻什麼都攢不下來,憑什麼?
對土地的渴望和人心的私欲,讓老王藏匿土地、註銷戶口、私下買賣……總而言之,有太多方法讓他從國家納稅人變成套現之後的黑戶。再加上皇室、貴族、官僚繼續兼併土地,建立莊園別墅,所以有一天朝廷驀然發現——帳本上的土地不夠用了,於是,問題出現了。
新生人口沒有足夠的土地可以分配,於是只能浪跡江湖或者到城市謀生。農民上戰場打仗立功了,卻沒有土地獎勵,只能用自殘來逃避兵役,但是他們的戶口落在本地,租庸調的賦稅也不會放過他。
立功不獎勵,沒田還收稅,農民會怎麼做?他們紛紛遠走他鄉,私下買一塊土地重新開始。因為只要不是國家分配的土地,就不會納入府兵和租庸調的體系中。
當時的大唐有種怪現象:農民都在辛勤勞作,但是很多都不用交稅,不用服兵役。天下富庶,朝廷卻始終缺錢花。這種現象,在李世民時代就已經出現,在武則天時代成為社會的主流,直到李隆基時代,由於國家沒有充足的土地用來分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社會秩序完全崩潰。
前面說,天寶十三年依然有六十%的人口是納稅戶,但這是帳面數字,實際上遠遠達不到。
國家沒有穩定的稅基,沒有穩定的兵員,甚至連基層組織都混亂不堪,因為農民四處流竄,管理起來難度太大。這就是盛唐的隱憂。
七一三年,李隆基改年號為開元。二十九歲的皇帝雄心勃勃,夢想建立起能和李世民媲美的功業。可現實給他澆了一盆冷水:國家稅基不足,導致財政吃緊,立功後無田獎勵,導致府兵逃亡。
與此同時,大唐的局勢也不安穩。北方的突厥一直蠢蠢欲動,圖謀恢復祖先的霸業和榮光。突厥被打壓後,又冒出回紇來騷擾。東北方有契丹在謀求地域霸權。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正值鼎盛時期,他們走下雪山,積極探索四川、新疆的新世界。
為了守護疆土,大唐必須維持龐大的常備軍。然而,崩潰的府兵早已不能為國爭光,甚至連保衛長安都做不到,於是,延續兩百年的府兵制被徹底拋棄,大唐實行募兵制。這其中就有一個問題,府兵制下,裝備需要士兵自己準備,國家是不管的,但是募兵制就不同了,國家需要準備好刀槍、馬匹、糧食來供養士兵。
然而,唐朝可憐的財政收入,根本不足以維持龐大的常備軍。怎麼辦?李隆基靈光一閃,想出一個辦法:沒有錢,我可以給政策啊!於是,他在開元、天寶年間,先後設立了十個節度使。節度使相當於軍區司令,朝廷沒有多餘的軍費,只能允許節度使在轄區內收稅。為了保障軍隊的管理權和財政權,朝廷又把地方監察權賦予節度使。軍權、財權、監察權逐漸集於一身,節度使已經是土皇帝了。
後人都說李隆基老糊塗了,其實他也沒辦法。舊秩序已經崩潰,李隆基又沒有能力建立新秩序,只能對破損的舊秩序修修補補,節度使就是一塊大補丁。
要想讓長安擺脫饑餓,就必須重新疏通水利,讓江南的糧食運到關中,而這個無底洞需要很多錢。皇帝親軍、中原駐軍雖然打仗不行,但也是一群「吞金獸」。李隆基和楊玉環長年累月的恩愛,不得要錢?再加上奢靡的宮廷、腐敗的朝堂、紙醉金迷的社會,繁花似錦的盛世中總是飄蕩著一股子黴味兒。而維持這一切的,只有日漸縮小的稅基。
為什麼李林甫能專權十九年?為什麼楊國忠可以爬到宰相這樣的高位?絕不僅僅是搞鬥爭和裙帶關係換來的,只有一個原因:他們能從老百姓身上壓榨到錢財。從這點來看,所有奸臣都是相似的。李林甫、楊國忠、嚴嵩、和珅……都是在舊秩序崩壞時能用特殊手段解決燃眉之急的人。
有時候壞人不是骨子裡壞,而是局勢讓他不得不壞。李林甫、楊國忠是如此,安祿山也是如此。
七五五年十二月,安祿山起兵造反。他的父親是西域胡人,母親是突厥巫婆,父母給他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軋犖山,意思是「戰鬥」。
一直以來,安祿山都特別能戰鬥,他在幽州軍中作戰勇猛,僅用了十年就從一個新兵升到了平盧節度使,駐紮在遼寧。此時的安祿山,是大唐成功「菜鳥」的典範。按照一般劇本,他將成為大唐所有落魄青年的楷模,但是局勢不允許他做一個好人。
大唐一直都有「出將入相」的傳統。在外領兵的將軍打了勝仗,一定會回到朝中擔任宰相,如果再有戰爭,宰相也可以披掛上陣。
作為皇帝的影子,李林甫在朝中全心全意賺錢,如果有將軍入朝為相,勢必會分走他的權力。而嚴峻的財政壓力,也讓李隆基不能破壞現有的撈錢模式,於是君臣二人發明了一項潛規則:「將軍儘量用沒文化的胡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入朝當宰相了。」
和其他將軍不同,安祿山的情商很高。他不僅作戰勇猛,還特別喜歡找碴兒。搜刮的軍費、戰利品經常送入朝中,上至皇帝、宰相,下至中層官員,基本都收過安祿山的好處。
有能力、高情商,又有政策紅利,安祿山成為「風口上的豬」。直到西元七五五年,安祿山已經是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全方位負責大唐東北方的戰爭。而大唐一共才十個節度使,也就是說,安祿山麾下有大唐三分之一的兵馬。歷史到這裡已經很明朗了。
國有土地制度崩潰,導致國家財政體系永遠不健康,兵役制度也渙散了。為了應付複雜的邊境戰爭,李隆基不得不把軍事、財政、監察權力賦予節度使,培養了一堆土皇帝。朝廷為了挽救財政危機,不得不讓李林甫、楊國忠獨掌相權,這樣才能集中力量撈錢。
李隆基的本意是讓宰相和節度使相互制衡,自己高高在上充當裁判。可這樣的模式,崩盤是遲早的事兒,因為人一旦嘗到權力的甜頭,就很難放下。
李林甫死得早,算是得了善終。楊國忠就不一樣了,他僅僅做了三年宰相,迫切需要建立功勳來證明自己,而安祿山就是塊最大的肥肉。
安祿山坐擁東北,早已培養了嫡系小弟。李林甫手腕高超、資歷深厚,足以讓他感到恐懼。可楊國忠算什麼東西,想拿我當墊腳石?做夢呢!於是,安史之亂爆發了。
安史之亂,讓那個後人只敢談復興、不敢說超越的大唐盛世永遠留在歷史的刻痕中,越來越夢幻。
千年來,楊玉環一直是替罪羊。還有人說,是因為李林甫奸詐、楊國忠誤國、李隆基昏庸、安祿山狂妄……總之,把所有帽子都扣到一個人頭上。然而,時代的巨變哪裡是一個人能決定的。
國有土地制度在北魏呱呱墜地,經過北周、北齊的發育,終於在隋唐大放光彩,然而又在天寶十四載壽終正寢。它成就了李世民,也埋葬了李隆基。
安史之亂,只是幾百年社會矛盾的總爆發,用千萬人民的血與淚,結成一朵妖豔的罌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