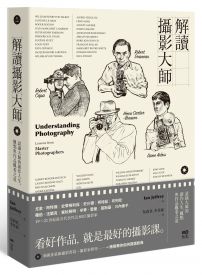亨利.卡提耶-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
他的名字可以和現代主義攝影畫上等號。卡提耶布列松對繪畫有興趣,曾在1927–28年間跟隨羅特(André Lhote)學習。大約在同一時間,他也開始拍照。他的第一趟攝影之旅,是1931年的東歐,同一年年底,他又去了象牙海岸,1932年返回法國。他在馬賽買了一台萊卡,之後就用萊卡拍照。1933年,他和童年友伴蒙狄亞克(André Pieyrede Mandiargues)連袂造訪義大利。他在西班牙拍攝的照片,有些刊登在1933年11月號的《VU》雜誌上,內容是關於當時的選舉和社會失序。1933年10月,他在紐約的李維(Julien Levy)藝廊舉辦首次展覽。他是1927年在巴黎的一場派對中結識李維,並一直和他保持聯絡。
超現實主義者欣賞歇斯底里、狂喜和夢境。1928年的《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以一篇專文讓人注意到該年是歇斯底里一詞出現五十週年。卡提耶布列松這兩張照片,都是為了呈現人物的心智狀態。馬賽那名男子所在的空間分裂成幾個部分:有些明白平坦,有些紆曲難解,一如腦部圖案。墨西哥沉睡者把頭倚放在長方形牆面和碎裂人行道之間:介於騷亂和清醒之間。心智狀態是攝影的一大挑戰,因為攝影是一種自然主義媒體。1920年代後期的現代主義攝影師喜歡拍攝一些圖解式照片,例如機器零件、鋼琴琴鍵。卡提耶布列松的創新之處在於,將這類背景與人物結合起來,暗示兩者之間具有某種意義連結。攝影師並非發現意義之人而是強加意義之人。不過這類照片正是卡提耶布列松早期作品的特色。
1932至1934年間,他分別去了義大利、西班牙和摩洛哥,旅行空檔留在法國。1934年,他啟程航向墨西哥,執行巴黎人類學博物館委託的法國地理任務。這項任務因為缺乏現金而失敗,但卡提耶布列松還是在墨西哥市停留了一年,與他同行的夥伴還包括哈林區詩人休斯(Langston Hughes)以及墨西哥畫家阿吉雷(Ignacio Aguirre)。1930年代初,人們的確期待攝師四處旅行,為新畫刊提供報導,但很少會在一個地方待上一年。不過,墨西哥市是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1934年,史川德也曾在那裡為政府工作。韋斯頓在那裡待到1927年,布拉沃更是一直住在墨西哥市。1935年3月,卡提耶布列松和布拉沃連袂在美術宮舉辦展覽。4月,與艾凡斯(Walker Evans)一同參與紐約李維藝廊的「紀實與反圖像攝影展」。李維表示,卡提耶布列松的照片「腐敗」,而他對攝影的想法「無禮而粗野」。李維指出,卡提耶布列松的藝術理論無法吸引他,因為他是個「正直謙遜」之人。
卡提耶布列松早期的照片經常上演進退兩難的情境。早在1932年,卡提耶布列松就體認到生命的起起伏伏,因為他曾在非洲得了重病。而攝影本身也極為仰賴好運,仰賴你能在正確的時間來到正確的地點。但更重要的是,1930年代初的藝術,是在哲學的環境中進行。卡提耶布列松未來將會知道,他在西班牙拍的新聞攝影,例如擁擠的場景、典型的公民,以及瞬間的風景,評價都不高。其他的非新聞照片,則像是為了彌補前者的平庸,卻成為他今日得享大名的憑藉。它們建構了一種後設敘事,或一種反思現實的詩意藝術。當時最傑出的理論家歐贊凡(Ozenfant),在1928 年出版了《藝術》(Art)一書,他認為,「科學與藝術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創造奇幻,為生活在現實中的我們提供安慰」。
他在墨西哥市住了一年,由父親提供資助。妹妹賈桂琳後來加入他,兩人於1935年搭船前往紐約。事後回顧,他在紐約李維藝廊的展出是一項成就,不過李維記得那些照片沒賣出半張,而且「攝影在那段時間是一條死路」。他還加了一句:「人們根本無法想像有誰會對攝影展有興趣,更別提買作品了。」他在紐約待了一段時間,遇到剛展開事業生涯的樂薇(Helen Levitt)。她把卡提耶布列松形容為天才,並說她1941年的墨西哥市之旅是受到他的影響。他也結識了當時介入電影製作的史川德,並可能因此受到刺激,開啟了他對電影的興趣。回到法國後,他設法讓尚.雷諾(Jean Renoir)雇用他,擔任《生活是我們的》、《鄉村一角》和《遊戲規則》等片的助手。
他曾和尚.雷諾一起在電影界工作,主要是負責對白部分。不過1937年他執導了《生活的勝利》,以西班牙內戰期間的共和軍醫院為主題。同一年,革命派超現實主義者暨作家阿拉貢(Louis Aragon)邀請他為《洞察》(Regards,前身為1932年創立的《洞察勞動世界》和《今夜》提供攝影報導。1934年起,法國一直處於紛擾的情緒狀態,那時卡提耶布列松並不在國內,到了1936年夏天,由布魯姆(Léon Blum)領導的人民陣線取得政權。人民陣線同時包含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元素,執政後嚴守改革而非革命的路線。其中的第一項改革,是在1936年1月實施集體合同、有薪假期和一週工作四十小時。布魯姆的政府只維持了一年多,隨即被法國的資金外流和一連串的罷工推翻。
1936年那張照片記錄了一個溫暖人心的事件,因為那頂雨蓬看起來像是臨時搭的,而後面那兩名釣客,則是專心做著自己的事,彷彿那是一個大家共享的空間。馬恩河畔那群貪吃客建構了一個容易引起話題的迷人畫面,不過對於關心1938年情勢的公民而言,他們看起來有些自滿。1938年夏天,人民陣線已經瓦解,罷工持續上演,而且只會越演越烈。儘管如此,卡提耶布列松還是喜歡野餐,因為野餐是研究人物的絕佳機會,而且它代表歡樂。背景中的某處會讓人回想起秀拉(Seurat),因為那是一張非常齊整的影像,帶有傳統的法國風格,卻又同時傳達出極為精準的姿勢:正在倒酒的手,以及那兩名婦人正在吃東西的手。他發展出一種獨特才能,可以在觀察日常的同時提出評論。他的觀察力從以前就有,但在早期的照片中,觀察的重要性比不上觀念。這份才能隨著人民陣線一起取得大權,並成為他在戰後拍攝的許多歐洲照片的特色—這些照片在1955年集結為《歐洲人》一書。
二次大戰期間他入伍服役並遭俘虜。1943年2月逃脫後,於1944年8月見證並拍攝了巴黎的解放。他執導紀錄片《回歸》,探討俘虜和流離失所者的遣返問題。當時他隸屬於聯盟攝影,一家具有合作社性質的通訊社,但因為行政和商業原因以失敗收場。美國人以為他已經在戰爭中喪生,正醞釀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為他舉辦一場紀念展。該場展覽最後在他的協助策畫下,於1947年登場。同一年,他和卡帕(Robert Capa)、羅傑(George Rodger)以及西蒙(David Seymour),共同成立了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1948到1950年間,足跡遠至印度、中國和印尼。1952年出版精選集,收錄1932到1950年間的作品,由巴黎的神韻出版社(Editions Verve)發行。這部備受讚譽的名作由希臘出版人泰里雅德彙整,他1930年初就結識卡提耶布列松,也是超現實主義期刊《人身牛頭怪》的藝術指導。該本攝影集的法文版名稱為「Images à la Sauvette」,意指那些照片是在奔跑中拍攝的。如果在「販售」一詞後面加上「à la sauvette」,就是非法在街上販售的意思。英文版的書名是《決定性瞬間》。1954年,當代最偉大的攝影編輯德派爾幫他出版了《轉型中的中國》,卡提耶布列松以目擊者身分敘述中國政權從國民黨轉移到共產黨的過程。他將該書形容為北京與上海1948年後的大事誌。1955年,泰里雅德出版了《決定性瞬間》的續集——《歐洲人》。
戰爭剛結束時,行旅輾轉的影像極為蓬勃。1930年代,這類照片是由旅行者拍攝,給人一種他鄉遙遠的印象。到了1945年後,這些照片則是表達了地理上的移動,有時也被用來象徵歷史的進程。面對接連上演的重大事件,備感壓力的攝影師們,開始把自己當成局外目擊者,為他們無法理解的歷史進程做見證。他們開始關注一些意外事件,這些事件既能反思他們自身的無助,也能反映參與者的無知。例如,那名盲人或許正在經歷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時刻,但在那個當下,他只能感覺到有事情正在發生。也許只是一名攝影師正在尋找素材,儘管如此,他還是得確認一下負責照管當日營收的小孩是不是還在那裡。這種局外見證者人的新概念,正是以卡提耶布列松為代表,並將繼續發展下去。
黛安.阿勃絲
DIANE ARBUS
1923–1971
攝影師都是觀察家,而且可能相當神祕。但阿勃絲相反,她在信件和筆記中坦承一切,或說了絕大部分。她很喜歡用格言,她在1961年1月12日寫給伊色瑞爾的信中指出:「這世界充滿虛構角色,忙著尋找他們的故事」,這句話非常適合用來形容當時她正在拍攝的怪胎系列。弔詭令她心喜:例如1960年在紐約市畸形人博物館表演秀中看到的一齣伊甸園劇碼,在這齣戲裡,無法抵擋誘惑的居然是那條蛇。她會花很多時間小心謹慎地遣辭用字,避免陳腔濫調。她寫信給先生亞倫和伊色瑞爾,而且寫得非常開心、投入。她的群眾都由親近人士組成,知道該對她抱持哪些期待,也都能呼應她的創造力。那是一種快速的口語散文,但不總是衝口而出,常常是伴隨著她的攝影而來。清單是她的另一個模式:她的筆記本裡寫滿了需要拜訪的人物清單和等待執行的計畫清單。
她踏入攝影圈的第一步是由阿博特領進門,時間是1941年的紐約。阿博特曾經花費很大心力,讓人們記住阿特傑。同一年,她也去了「美國一方」藝廊造訪史蒂格利茲。她一方面進行各式各樣的個人拍攝計畫,同時也跟隨《哈潑時尚》的藝術總監布魯多維奇研究攝影,他是當時極富影響力的名師。不過,她並沒有學到太多東西,一直要到1956年她去上了馬德爾的課程,情況才有了改變,這位偉大的維也納女攝影師,自從1938年起便定居紐約。馬德爾教她要戒除顆粒感,努力追求清晰的畫面。馬德爾對她的影響很大,她總是可以從馬德爾那裡尋求忠告。馬德爾告訴她:「你越獨特,你的獨特就會變得越普遍……」1962年,當阿勃絲開始改用中片幅的Rolleiflex 相機時,馬德爾還建議她該如何調整手法適應這款機器。1963年,她參加古根漢舉辦的競賽並贏得獎項,針對「美國的儀式、習慣和風俗進行攝影研究」。1965年第二次獲獎,計畫主題是「室內風景」。1964年紐約現代美術館開始收藏她的照片,儘管如此,終其一生,她都不曾在商業上獲得成功。
照片補充了她的書寫以及其中反映的論點。她寫得又快又凌亂,老愛走偏鋒。亂槍打鳥的她,總會打中某個東西,某個能夠含括該情境的直喻、隱喻或譬喻。她的描述多半很有戲劇感:她經常像個闖入古怪場合的天真旅人,困惑茫然,而這些地方大多就在紐約市內。她喜歡在信裡大肆渲染,渲染到事實變得比小說更古怪,不過那些照片卻經常流露出濃濃的紀念性,一如那名遊行中的男子。一邊是奔放的想像力—在阿勃絲的例子裡是多變的性情—另一邊則是除了束縛之外別無用處的身體。
1971年初,她在紐約西貝斯(Westbeth)藝術之家的公共室開了一堂攝影大師班。其中一名學生奈良原高一為這些課程錄音存檔,供日後參考,後來經過謄寫,做為《.diane arbus.》一書的前言,這本攝影集是由光圈出版社出版,與1972年紐約現代美術館舉辦的回顧展同步發行。這篇錄音稿連同其他摘選文字印行在這本書的最前面,讓人覺得這些內容就代表了攝影對她的意義。而這些文字確實也切中事實。它們甚至比影片更能傳達實情,因為影片還得依賴攝影師和錄音師。你不必得有什麼精湛技巧才能拍出偉大作品,你只要在對的時間有對的感覺就可以,但這卻是近乎不可能的條件。偉大的作品總會有一些意外,有些出乎預料的東西,尤其是出乎她自己的預料。她可以感覺到有些人去過另一個世界而且存活了下來,而這些人的肖像將能告訴你他們經歷過的某些事情。由於她本人就是另一個世界的常客,雖然不是同一個世界,但也類似,所以她對這些照片能透露的訊息非常著迷。
川內倫子
KAWAUCHI RINKO
1972-
川內的專業是平面設計與攝影,並在1990年代以商業攝影師的身份活躍。2001年LittleMore 出版社為她出版了第一部攝影集《打盹》(Utatane)。「utatane」意味著一種介於睡夢與清醒之間的狀態。川內對於日常生活的各種意象相當敏感,那些意象與其說是物體之姿,倒不如說是存在於我們的反應中。在《打盹》中,其中一張照片是少見於川內拍攝題材中的洩氣輪胎,爆胎的輪胎能讓人輕易地聯想至挫折這種隸屬心理層面的感受。這張照片與另一張有一道光芒照射的拉門照是成對作品,只是拉門照片捕捉的現象不足掛齒,無時無刻在全世界各地上演,也無須操煩該如何解決應對。川內偏好捕捉會在人類的好奇心與視而不見之間產生拉鋸的對象。目錄可以無邊無際擴展下去,但其中的一項條目能在我們不期然領略箇中奧義時,帶領我們看到這一點。
川內曾在一座大理石門廊下拍攝一張一位正在步行、身穿綠色大衣的女子照。在觀賞照片時我們通常喜歡看主角的臉,但在這張照片中,女子的臉被她的頭髮遮住─從她的大衣被吹開的樣子判斷,當天應該風很大。當然大理石建築是被動的,但照片的呈現方式卻帶領觀者歷經一場發現的歷程─直到我們豁然開朗的瞬間。
川內眼中的世界是由可觸碰也可品味的實體所構成。就連光線有時在她作品中也是可捉摸的,比方像浮游的灰塵或是汽車大燈光線外圍的黃色光暈。川內所捕捉下的對象就像是行走於沙地上,它們腳踏實地,移動時小心翼翼。為了可以更徹底地觀察,或是捕捉到存在的當下,川內會移動位置,以便清楚看見光線的亮點或是光線所造成的陰影─如此才能更接近被攝體的本質。人為了尋求安全感或是出於好奇,會自然而然想與外界連結或是伸出手實際碰觸。在收錄於《打盹》的一組照片中可見到浮現於昏暗天空中的閃電好似要霹向位於其下方的建築;而在與這張照片成對的作品中,可見在小燈的照射下,一隻手正將淺色衣物挪往縫紉機的針下方。除了光線、聲音與觸覺這種性質上含蓄克制的題材以外,進食的畫面也在她的捕捉範圍內。在《打盹》中可見到大批的鯉魚群湧至湖面爭奪魚餌的照片,好似在用牠們的嘴進行感測一般。無題.取自《天與地》系列.2012她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攝影時相當仰賴直覺,她通常是在相機的驅策下,於某個特殊、絕無僅有的場所中按下快門,而那樣的直覺近乎是幻象。
川內提到在自己還小時,一些微小的聲音或微不足道的小東西對她而言是很重要的存在。她也特別提及《天與地》(Ametsuchi)系列作品,此一系列為2009至13年間她在日本南部九州的火山區所拍攝的火燒原野(日文為「野 」)照。川內在實際造訪該地前曾在夢中夢到該處景象,而不曉得夢中之地位於何處的川內在六個月後竟不期然在電視上看到夢中的景象。該地在1300年前便持續火燒原野的傳統至今,為的是要將土地維持在良好的狀態,同時避免草原進一步生長成林。這樣的行為是人類取代大自然角色來維持土地的良好示例,而這項行為本身也似乎已內化為自然的一部分。川內提及人類天生有一種喜歡按部就班的特質,只要深入觀察就定能察覺到。而這些照片若要比川內在2001年初試啼聲時造成更大的迴響,那麼尺寸勢必也得要來得再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