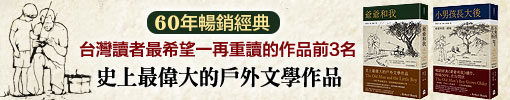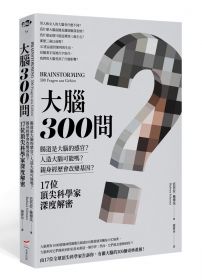Chapter 1 理論上你可以讓大腦跟身體分離,並把它存放在營養液裡。
神經心理學家彼得.布魯格(Peter Brugger)說明,為什麼大腦失去身體就會很難存活。而他為什麼把「直覺」功能定位在右腦?那些自稱能預見未來的人,腦袋又是怎麼一回事?
Q:我們為什麼有兩個腦半球?
這是科學家長久以來就爭論不休的謎團。畢竟比起兩邊得協調運作,只有一個驅動中心不是更好嗎?不過另一方面,凡事成雙總是利多於弊,尤其是萬一有部分功能停擺的話。就像人也有一對眼睛,我們需要這種雙重裝置,物體才能具有立體景深。這讓我產生一種想法,或許兩個腦半球也具有某種「產生景深」的作用,這樣我們才能在大腦深處,以兩種方式來「觀看」某個事實。
Q:如果人的某個半腦被移除,會出現怎樣的狀況?
如果是成年人,被移除的半腦所操控的那側身體會癱瘓。早期在醫學上,有時會對深受癲癇之苦的孩童進行切除半腦的手術,以使發作時的放電現象不再波及整個腦部;在手術後,這些孩童兩側的身體通常都還能活動,只有切除部位所掌管的那半身會有點障礙。
Q:有哪個腦半球較具優勢嗎?
這得看是哪方面的優勢。以右撇子為例,由於左腦較擅長處理語言,因此較具語言優勢。而右腦則相對較擅長辨識人臉。不過,語言處理本身又可區分成不同優勢(或說能力)。就像左腦負責支配涉及明確、緊密關聯性者,例如「桌子和椅子」。可是,一旦這種關聯性離得較遠,像「桌子和花」──花先插在花瓶裡,然後花瓶在桌上──我們的右腦就會活躍起來。說到河流想到水的人,運作的是左腦;而說到河流而聯想到旅行的人,運作的則是右腦。
Q:為什麼大多數的人都是右撇子?
這個問題的解答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是,不管在任何文化圈,或在人類發展史上的任何時代,大概都是右撇子占多數。早在一些史前洞穴壁畫留下的手印裡,就已經顯示當時的人是用哪隻手來支撐,又用哪隻手來作畫──他們大多使用右手。而從過去留下的器具,我們也知道早期的人大約在每十個右撇子當中,才會出現一個左撇子。
Q:我們的身體需要腦,可是腦也需要身體嗎?
理論上,你可以讓腦跟身體分離,並把它存放在一個好的營養液裡。英國兒童文學作家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的短篇小說《Kiss, Kiss》中有個非常美妙的故事,寫的就是一個住在書架上的大腦。以人工方式獲取營養的大腦,並不需要抓取食物的手或能走到某處覓食的腳,當然也不需要消化食物。在物理上,你可以想像大腦可以沒有身體而活著。然而,對習慣有身體的大腦來說,可能很難失去身體,因為這樣一來,它就再也沒有社交活動……
Q:大腦失去身體,就感覺不到身體了嗎?
其實是有的,有一種幻影式的接觸,我們還是能以幻覺的形式感覺到身體。不過,我希望是再也感覺不到疼痛,否則那將可能有如置身地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沒辦法請求別人幫我們減輕痛苦。但是,「身體的生物性功能為何」這個問題真的很有趣。身為神經學家,我會這樣說,我們身體的存在,是為了要帶著大腦到處走動,把它帶到有東西吃的地方,帶它走進社會,並走到未來的伴侶那裡。
Q:但如果這些是目的的話,我們的身體不用這麼大吧?
確實如此。但我們得有心臟血液循環系統才能跑步,也需要有消化系統才能獲取營養。而這些系統都需要空間。
Q:有時候我們會聽到這種說法:人大約只使用了百分之十的腦。
這是胡說八道,而且大多是山達基(Scientology)團體的人這樣說。我們始終使用著整個大腦,只是不會一直意識到這一點。例如開車時,我們的大腦有許多功能在運作,但其中絕大部分我們根本不會察覺到。人的大腦是如此運作的:這次是這個區域被多用一點,下次則是那個區域。而且依熟練精通程度而定,有些人腦中的特定區域,會比其他人更發達、更突出。
一個長跑健將會比不常運動的人,更常用到腦中與腿對應的區域,並因此讓它更機敏靈活。同理,經常閱讀與寫作的人,也會比幾乎不閱讀寫作的人,更常使用與此對應的腦區。此外,有種情況也會發生:某些腦區突然必須接手其他部位的任務。例如,在那些因故失明的人身上,本來一直掌管視力的大腦視覺皮質,現在會被指派其他任務。
Q:什麼任務呢?
例如觸摸印象。試想盲人如何透過指尖的敏銳觸覺,來閱讀點字。
Q:第六感是由大腦來掌控嗎?
沒錯。所謂的第六感就等同於直覺,在我的定位中,它是由我們的右腦來掌控。人的右半腦負責警惕、小心以及恐懼這類的負面情緒。我們的第六感不會說:「不要去這個或那個國家度假。」當直覺浮現時,通常是為了向我們發出「應該留意某種場合或某種人」的訊號。第六感要說的是「小心!」
Q:那些相信自己有預知能力的人,大腦是怎麼運作的?
自稱能預見未來的人,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判斷狀況。他們所陳述的那些事蹟,在別人口中通常純屬不可思議的巧合。舉例來說,他們夢到自己在比賽中贏了一輛紅色的車,不久之後真的贏了一輛紅車。其實,如果每晚都做同樣的夢,不管是誰都會相信自己天賦異稟,能預見未來;但假若夢到紅色車子的人,隔天是綠色腳踏車被偷了,就不見得會把這個夢跟失竊事件聯想在一起。除非他本身相信超自然玄學,才會認為「這絕對不可能是巧合」。比較理智務實的人,頂多會這樣想:「這是某種徵兆嗎?有意思……我夢到一輛紅色的車,然後隔天綠色腳踏車被偷了。」
Q:因為汽車和腳踏車都是代步工具嗎?
正是,而且紅色與綠色還是互補色。不過還有第三類人,而對這類人來說,一切非常清楚:這個夢絕非意外,而是一種指點,我應該把腳踏車鎖好一點才對!我們在神經心理研究院所做的實驗顯示,這些自認能預見未來的人(我稱他們為「信徒」),聯想力比一般人更豐富。我們做了這樣的測試:告知參與測試者一個字,例如「獅子」,然後請他們在聽到下一個字,如「肚子」,並覺得它與「獅子」有關時,按下一個按鈕。如果在「獅子」之後聽到是「鬃毛」,參與者會比較快按鈕,因為「鬃毛」與「獅子」明顯相關,在聽到「漫遊」時也按得比較快。
Q:或是「非洲」、「斑馬」……
……與「老虎」。能快速與廣泛地產生聯想,是具創意的人的特質。然而,這其中也存在一種危險,就是把客觀事實上不相干的事物看作相關,硬是扯在一起。例如,偏執型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會快速且廣泛地產生聯想。那些「信徒」的大腦運作機制,其實與偏執型思覺失調症患者是一樣的。
Q:有關大腦的研究由來已久,但科學上對精神疾病或慢性疼痛的治療,卻沒有多大的進展。為何會如此呢?
「我們早就開始研究大腦,但在精神疾病上的進展卻很有限」,這樣的說法很有意思。你把我們的大腦跟精神一概而論,並以此認定精神疾病就是大腦生病了。我曾研究過異肢症(Xenomelie)患者,這類人不認為某隻手或某隻腳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最極端時甚至渴望截肢,而我的研究確認了他們大腦的某些區域與對照組不同。不過,我也不想因此做出「這種截肢意願純粹出自腦神經性因素」的結論,這應該只是部分條件。
Q:那其他因素呢?
還有網路、溝通、文化及研究本身。有時候,我都覺得自己有點觸及倫理底線,在思考是不是最好停止進行這樣的研究。
Q:停止研究的話,就不會有這種病了嗎?
這正是問題所在。我們會不會在探討這種現象時,「培育」出了一種失調?一百年前在醫學臨床上並沒有「異肢症」這種病,更確切地說,那種想截肢的渴望,在過去被視為是一種性慾異常的現象,因為有一半以上的當事者認為斷肢特別具有性吸引力。一直到今天,在日本和中國都沒有人認識這種異肢症。假如你在這些國家,問人有沒有一種身體某部分不屬於自己的感覺,對方只會認為你瘋了。而且我敢說,在那些戰火肆虐、有許多人因誤觸地雷而失去手腳的國家裡,沒有任何人會想切除自己身體某個健康的部位。
Q:回到原本的問題。為什麼即使我們不斷研究大腦,在精神疾病或慢性疼痛這些領域的治療,並沒有進展呢?
因為在我們想要找出某個答案的研究過程中,總會冒出至少五個新的非常重要的根本問題,還有五百個相關的次要問題,而對此你根本完全沒有時間去研究。不過,這樣像滾雪球般有愈來愈多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代表我們對大腦的認識愈來愈精準。拜大腦研究之賜,我們現今知道了使思覺失調者出現幻覺與妄想的大腦部位,與同樣會出現這些癥狀的嗜睡症者不同。基於這些認知,我們在藥劑學上便能做出更好的藥,而這是巨大無比的進展。精神問題會一直存在,然而人們看待它的方式將有所不同。我們想問的問題會改變,但不會變得更簡單。
Q:電腦打字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快要取代了手寫了。這對我們的大腦會產生影響嗎?
肯定會。電腦打字完全不同於用手書寫,特別是當你在速記一個複雜問題的圖解時。此時,我通常會在一張紙上重點記下個別事實,或甚至把它們畫成示意圖,用箭頭把某些字連起來,也會以讓我能辨讀出來的方式劃掉某些字。手寫能力的退化,肯定會讓我們的大腦產生重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