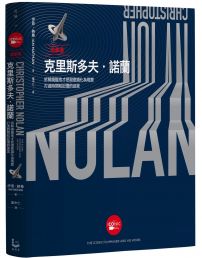「拍蝙蝠俠的基本概念是,永遠要從壞蛋的觀點來呈現他,」他說,「我總是把蝙蝠俠比成在《異形》第一集裡你剛剛瞥見的外星人。他很嚇人、充滿威脅性、而且飄忽不定。你了解他們為什麼會害怕他。」
我們第一次見到蝙蝠俠行動,就有個驚人的片段:他在高譚市迷宮般的貨櫃港一個接一個把歹徒撂倒。諾蘭曾帶著《跟蹤》參加香港電影節,被碼頭邊航運貨櫃的景象所震撼,他記住並把它當成動作戲的背景。
換到一部恐怖片裡,這些動作畫面則有著感染力。
諾蘭願意扛下各方對電影的高度期待,一個吸引他的重要原因是蝙蝠俠讓他「有機會進入一個特殊的電影類型」。不過,他絕不是要拍個更黑暗的電影。事實上正好相反。跳出了他探尋深奧哲理的習慣,諾蘭很高興有機會拍一部他小時候可能會喜歡的電影:對他而言,這是變體的《法櫃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或《007: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他把韋恩回家比擬成《基度山恩仇記》(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電影開場的呼嘯狂風,借自他所喜愛的《大戰巴墟卡》(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這部1975年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改編自吉卜林小說的傑作,由史恩.康納萊(Sean Connery)和年輕的米高.肯恩主演。
實際上,可以說他是在拍他的龐德電影——隱密身分的英雄,帶著適用各個場合的特殊裝備,破解巨奸梟雄的計畫。諾蘭想跟龐德電影一樣「走遍全球」,展現高譚之外的世界,擴展電影公司稍早之前打造的遊樂場。諾蘭是先透過電影認識這位傳奇的虛構情報員,之後才閱讀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的小說,他欣賞康納萊如何貼近這個角色的「自我陶醉」(the selfishness)。這種虛榮感,是貝爾寄託在韋恩這個角色身上的另一個特點。
「我們決定,錢就是他的超能力,」克羅利說。蝙蝠俠儘管身手矯健,但仍是凡人。很重要的是,諾蘭任何一部超級英雄電影裡都沒有所謂的超能力。理性凌駕一切。韋恩用未來色彩的裝備武裝自己,來執行超越法律的聖戰。費里曼飾演的福斯,在韋恩企業的應用科學部發明了一大堆的裝備(這是導演構想出來推動情節進展的裝置),擺明了是向龐德電影裡的「Q先生」致敬。不過這裡也帶了一些後911時代強調軍事硬體的說服力,包括「雙層克維拉」纖維護甲和微波發射器等科技含量很高的對話。反恐戰爭的概念在全片迴盪,雖然諾蘭完全否認是有意為之。
蝙蝠裝是黑夜中的一抹黑,它被設計得更有野獸風格,長手套有如刀刃的突起紋路,披風以降落傘的尼龍布裁製,透過網狀的通氣管展開它蝙蝠般的翅膀,讓貝爾得以如德古拉一樣在屋頂之間滑翔。改造更徹底的是蝙蝠車,從雪佛蘭柯維克(Corvette)改裝車,變身成了悍馬和藍寶堅尼混種的高速坦克,車身有漆黑的裝甲。被逼到無路可走時,蝙蝠俠會直接從敵人的頭上開過去。它被命名為「不倒翁」(Tumbler),由克里斯.考博德(Chris Corbould)領導的實物特效團隊一手打造。這樣一部完全可運作的蝙蝠車,也具體展現了諾蘭對實物特效投注的心力。「它成了一項真正的使命,」考博德說。
CGI(電腦生成動畫)在製作過程有如瘟疫受到排拒,導演只有在物理法則或安全出現問題時才會通融,或是用於極少數僅存於漫畫的一些遠景。諾蘭說,「我們拍這部片確實做了一些很有企圖心的東西,」這位曾和弟弟共同製作定格動畫的大男孩,自認「建造了比任何電影都還大的場景。」
@場景極盡可能的繁複
高譚市此時精純地展現蝙蝠俠精神分裂的大城市和諾蘭式的雷霆風暴。它繁複龐雜一如導演想像力的電路板,是一座城市大小的迷宮,真實的地點混雜了奇幻的場景,既龐大又封閉。他想建造像是雷利.史考特或朗.弗列茲的世界,街道同時也是譬喻的空間。「我們不異想天開,」這曾是克羅利的口頭禪,不過高譚也有其浪漫的一面;讓人聯想起《銀翼殺手》裡閃耀光芒的反烏托邦、弗列茲.朗《M就是兇手》(M)表現主義風格的柏林、《大都會》(Metropolis)深奧的未來景象,以及喬凡尼.皮拉奈奇(Giovanni Piranesi)版畫所虛構出的數不盡的監獄景象、抑或是畫家艾雪以哥德式瘋狂所呈現的數學純粹性。巨大的場景搭建在倫敦的片場。另外,貝德福郡卡丁頓一座挑高兩百英呎,過去供飛船停放的停機棚內,打造了高譚市的一整個街區——場景宛如遊樂場迷宮,極盡可能的繁複。諾蘭把它設想成「施打了類固醇的紐約」。
諾蘭處理每個場景的方式,依舊比照過去拍攝《記憶拼圖》和《針鋒相對》,這一點讓攝影瓦利.菲斯特印象深刻。「在片場裡可能有一百五十人,有超大的場景,不過當攝影機開始轉動,克里斯一樣是坐在我旁邊看著小小的螢幕監視器,演員就在我們前面。這十二英呎的區域就是他全部的世界。」
在芝加哥的下瓦克大道和洛普區(The Loop)為期三個星期的外景拍攝,提供了凡德羅設計的摩天大樓閃亮樓面和足供「不倒翁」馳騁的寬廣大道,以及充當韋恩企業總部的芝加哥期貨交易大樓。這是薛尼.盧梅(Sidney Lumet)和威廉.佛瑞金(William Friedkin)的粗獷都會風:《衝突》和《霹靂神探》裡的腐敗城區。還有曼恩的《烈火悍將》,永遠的《烈火悍將》,它以閃耀的光帶將洛杉磯帶入神話。諾蘭還記得在他頻繁旅行的童年,當飛機降落奧哈拉機場時,西爾斯大樓高聳入雲的景象。他會把蝙蝠俠安排在芝加哥最高的壁壘上,俯視著諾蘭之城——在他腦中的電動織毯。另外,他學生時期的建築也融入了城市景色,例如聖潘克拉斯車站(St. Pancras Station)、倫敦大學理事會大廈(Senate House),以及他的母校倫敦大學學院的部分建築。
在此同時,電影裡墜落的單軌電車,大霧瀰漫的狄更斯式貧民窟,以及前途難料的阿卡漢瘋人院(Arkham Asylum),代表了諾蘭對華納公司和類型電影傳統的一些讓步。有大量動作戲的最後一幕,遵循諾蘭過往電影的傳統。「製作《蝙蝠俠:開戰時刻》時,我們很明確地要讓它盡可能聲勢浩大,」他承認。這是一部夾雜了兩種不同思路的電影,或者說有雙重人格——一部諾蘭式的賣座鉅片。
《蝙蝠俠:開戰時刻》在2005年6月16日於戲院上映,強勢拉動了超級英雄必備的命運逆轉,全球三億七千四百萬美元的票房不能說是橫掃千軍,但也相當可觀。「人們很喜歡這部電影,不過還沒有我們預期的那麼成功,」他說。這個票房數字還不足以重新定義流行文化。不過,一個偶像已然在漢斯.季默配樂的陰鬱氛圍中重生(和作曲家詹姆斯.紐頓.霍華〔James Newton Howard〕的協助),電影配樂刻意迴避頌歌,代之以介於樂音和噪音攻擊之間的持續升高的音調,此外,另一段長期的創作夥伴關係也就此開啟,這部分我們稍後還會再談。
影評又鬆了一口氣,他們發現它確實是部由《記憶拼圖》的大師所拍的蝙蝠俠電影。諾蘭並沒有因加入巨頭電影公司而墮落。「出人意表的強烈且引人不安,」《Time Out》週刊如此讚揚,他們認為它是正面的訊號。「它的特效背後有一顆靈魂,」《新聞週刊》的大衛.安森(David Ansen)察覺到這一點,並對片中心理寫實的探討表示認可。的確,它向主流靠攏,不過有著明顯的企圖心。《洛杉磯時報》的肯尼斯.圖蘭(Kenneth Turan)看出諾蘭的意圖是「創造一個神話,在可能範圍內建基在一個平凡的現實上。」如導演所說的,故事裡的超級英雄「只不過是個做很多伏地挺身的傢伙。」
諾蘭拍了一部聲勢浩大、品味通俗的電影,它聯繫到一個嶄新的寫實主義,進入到蝙蝠俠故事豐富的底層深處,它就像韋恩莊園底下的洞穴系統。故事主人公既要替無理遭到殺害的父母報仇,也想追求更大的善;他在兩者之間的掙扎,具有某種普遍性、甚至是自傳性的意涵。為了打造一個更好的高譚。「蝙蝠俠受限於身為凡人,」諾蘭說,「因此在務實和理想之間始終存著張力。」
好了,回答完蝙蝠俠如何開始的問題,滿腔熱忱的英雄和意志堅決的導演接下來要做什麼?打造更好的好萊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