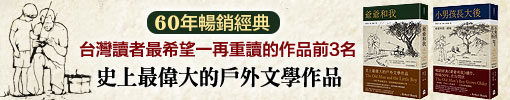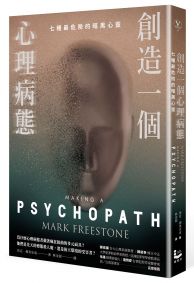第二章 殺手保羅
在大型機構裡—監獄、醫院、保釋住所—與重刑犯共事是件辛苦吃力的工
作。和你共事的人隨時有潛在的危險性,他們曾犯下重罪,對自己被監禁感到不滿,而且極度脆弱。這表示你身為專業人士的工作會非常困難:你和一群不想待在那裡的人共事,試著給他們理由做出他們無意為之的改變,同時還要避免讓他們有機會傷害你,因為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會這麼做。
除此之外,有人格疾患(例如心理病態)的犯罪人是難以矯正的。他們的精神障礙並無明確的治療方法,而且往往渴望在監獄中重新創造過去的生活,通常以使用毒品和暴力為特點。這代表,監獄本身就是一個嚴酷的所在。
早期那種較古老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監獄,因為不敵現代化必須具備廁所配管系統的健康與安全規定,如今多已消聲匿跡,目前的建築提供了便盆和監視廂房四周的清楚視野,以防有人在陰暗處逞兇,此外就只剩冰冷的混凝土建物,以毫無裝飾的塗白牆壁作為主要特色。最高安全等級的監獄或許是最糟的一種,有更高的圍牆,加上超高的金屬網圍籬和直升機網。
在我任職的機構中,沒有人像保羅那樣善於將監獄外的生活帶進監獄之中。我在一所高度戒護的監獄首次遇見了保羅,連同其他一群囚犯,他們正在和一位心理學家討論後續的治療方式。這是一項監獄實施的新服務,屬於DSPD計畫的一環,專門服務因為心理病態或其他嚴重人格疾患而被視為「無法治療的」重刑犯。當時,我的任務是觀察這類活動,試著從中瞭解和描述矯正這些個案所需創造的那種文化,以及囚犯和工作人員是如何形成關係。這些囚犯可能已經被單獨監禁多年,或從未開過這類讓他們有機會出獄的假釋會議。囚犯中的大多數人看來焦慮不安,這也許理所當然,因為他們多半被判處無期徒刑,明白這是他們離開監獄的最後機會。然而,沒有人知道所謂的「治療」是怎麼回事,除了在餐廳打架之後,有護士替他們縫合傷口的那幾針。
其中一個男人擁有單獨監禁的長期紀錄,他被獨自囚禁長達六年之久,如今就連單純坐在別人的身旁,都會猛冒冷汗。他一分鐘轉頭好幾次,緊張兮兮望著身後的空白牆壁。我猜自從他被囚禁在八乘以五英尺大小的單人牢房之後,就連此刻這個狹小無窗、只有八張椅子和一個檔案櫃的監獄會議室,也讓他感到難以想像的空曠和暴露。
另一個同樣在冒汗的男人戴著一副所謂「強姦犯眼鏡」,我後來才知道:這種眼鏡的光反應鏡片會在明亮的光線下變暗,用以保護眼睛;而許多性犯罪者似乎難以理解地被這種眼鏡給深深吸引。我說難以理解,是因為其他囚犯和工作人員似乎都知道,戴著這種眼鏡,差不多就等於擁有「強姦犯俱樂部」的會員卡,所以沒有人願意戴上這種眼鏡,因為如此一來,想找強姦犯開刀的暴力犯,就很清楚要從哪些人下手了。
在這群三教九流的人中,我第一次看見保羅。他猛然坐了下來,近乎水平地岔開著雙腿坐著。他撇嘴露出一個古怪陰鬱的表情,看起來好像蔑視周遭的一切,又好像勉為其難的加以掩飾不屑的態度。
「我想知道大家對於今天的期待?」一位女性心理學家問道。她遵循著眾所皆知的蘇格拉底詰問法,禮貌地表現出對每個人的答案感興趣的樣子。「離開這他媽的鬼地方。」保羅出言譏諷。強姦犯眼鏡男緊張地吃吃笑了起來;而單獨監禁男驚懼的雙眼,就像正緊盯住想像中一輛直直朝他頭上輾來的十八輪大卡車。
「嗯,我想這是個目標。」心理學家不動聲色的說。
「這他媽的傢伙是誰?」保羅問道,約略地指著我。突然間,我發現了強姦犯眼鏡對我也有莫大的吸引力。我很快發覺,在這座監獄裡,沒有人比保羅更自在,包括工作人員在內,當然。在監獄裡開會往往是件相當緊張和困難的事,工作人員和囚犯的訴求會產生嚴重的衝突,但無論會議氣氛多麼緊繃,保羅從頭到尾都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模樣,雙臂交疊,臉上露出嘻笑的表情。只有在少數片刻,當他感覺有人擺出妥協的姿態,他的面孔會因為義憤而扭曲,就像來自美國中西部的電視福音傳道人那樣,他會讓對方切確知道他們欠他東西。上帝為證,現在該是他收債的時候。
還在監牢外的保羅,大概是我最常被問到的那種身份之一—殺手。我很想寫成「刺客」,但「刺客」擁有各種迷人的意義,而保羅做的事可一點兒也不迷人。當某些人欠他錢或欠他老大錢,他會找到這些人,將他們綁起來好好折磨一番,或是吩咐他那些沒有骨氣但同樣殘忍的手下替他動手。這些人一來受到恐懼的驅使,二來自己也想當上「大咖」。保羅的恐怖統治範圍橫跨了英國好幾個郡,在他的團伙支持下,拼命向意志力薄弱的男男女女推銷毒品。他們差不多全都對古柯鹼上癮,這點讓保羅得以近乎絕對地掌握他們的生死。
不料一天事情做的太過火,某樁毒品買賣出現了對手,威脅到保羅的生意。保羅糾集了幾個年輕的幫兇—其中有個男孩年幼到必須上少年法庭受審—他們聯手突襲毒品販子,用衝鋒槍將他打成蜂窩。出庭時,保羅指示律師團隊將一切罪責推給那個年幼的共犯,撇清自己的責任。在定罪後,他利用司法制度所允許的每次上訴來咬定這個說法。他之所能接連上訴,是因為在最初的審判中作證的幾名證人決定撤回供述或改變說法,這點證明了保羅雖然人在監獄,但勢力猶存。
閱讀審訊紀錄時,我對警方深感佩服,他們想必趕在保羅集團恐嚇目擊者改變說法之前,迅速取得了證詞。不過當時我沒有太過在意這件事。我注意到的是,保羅在總分四十分的PCL-R量表中得到了三十八分!這代表他是所有囚犯之中,心理病態程度最嚴重的百分之一。
對許多人來說,監獄是個極其可怕的地方,充滿了限制、霸凌和侵蝕靈魂的無聊,這裡只有罪惡感、恐懼和寂寞和你常相左右。然而,對某些人來說並非如此。我所認識最能適應這種嚴苛環境的人,就非保羅莫屬。即便是安全等級最高的監獄,對他來說似乎就像另一個家。
保羅出身於犯罪家族,從小就被父親教導要做一個「絕不告密、絕不甩權威和絕不屈服」的人。保羅的外表帥氣迷人,他有一頭蓬亂的黑髮和碩大的頰骨,由於監獄生活相對緩慢平靜的步調,他的臉頰才稍稍變得豐滿一點。這表示著人們傾向於給予保羅過多的自由度,雖然那顯然不是他犯下可怕罪行之後應有的待遇。囚犯們和各層級的監獄官員幾乎就像聽命於保羅,彷彿監獄是他的場子和圈套。透過可疑程度不一的種種角色扮演,將全部的人吸納其中。因此,在我踏入的這個圈套中,在我剛完成「監獄安全訓練」的情況下,我試著瞭解「權力」在監獄中的意義,以及心理病態者的獨特人格如何在這種環境下助長這件事。
保羅對我的態度再友善不過。他似乎出現在我第一週所參加的每一個囚犯會議上,而且他定期出席吉他社團,是出了名的熱中演唱柯恩(Leonard Cohen)的經典歌曲,即使不那麼動聽。保羅察覺到我在這個陌生複雜又死板的監獄體制中有些茫然,他對我提出了幾個有用的建議,關於我應該參加的集會,「如果你想知道這裡真正發生的事。」他說。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同意在接下來幾週去參加獄方舉辦的社交和治療活動。
這些活動通常很成功,保羅總是表現合群,並熱心地幫助我跟大夥兒打成一片,
還讓我受到囚犯們和一些工作人員的歡迎。一切出乎想像的順利。我時常想,假使沒有喬西(Josie)的話,監獄裡會發生什麼事。喬西這個身高矮小的司法心理學專家,看起來勉強搆得到保羅的腰,卻摸透了他的底。只要有喬西在,她說能道破保羅每句話的言外之意:「當你那樣說話時,保羅,我聽起來有點像在威脅。」或者「我不知道為什麼,保羅,但我覺得你想辨法讓我在大家面前像個笨蛋。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嗎?」一來二去,保羅變得收斂不少,尤其喬西在場時,他學會更加謹言慎行。
我開始欣賞保羅在治療集會之外展現的隨和魅力。還有,他顯然看透了我的天真,並理解我是如此渴望瞭解並融入監獄的生活。在所謂非正式團體活動—烹飪課、下棋課(是的,心理病態者很可能是下棋高手),甚至只是進餐時的閒聊—只要保羅在場就絕不會單調沉悶,因為他總有一堆新鮮有趣的監獄八卦讓大夥兒震驚,就連工作人員也吃驚不已。
保羅最喜歡的話題和樂趣來源之一,是他所謂的「香腸俱樂部」,這顯然是囚犯們用來性交易的一個秘密社團。這些囚犯多半自認直男,並猖獗地展現出恐同的態度,但同時又認為能跟男人性交,總比沒有好。在這些話題中,保羅總是知道誰欠了誰某種性服務,或是誰在吃醋,因為某人在週一淋浴時讓別人替他吹簫,諸如此類。
不過,最後他總會以堅決的否認作為結語,例如「當然啦,我自己從未參與這些被禁止的行為。」在我看來,這番話的用意或許是為了讓工作人員覺得他們盡到了一點本分。然而同時我也納悶,為什麼一個不在意任何事、也不管別人怎麼想的人,會費心表明他沒有做任何不適宜的事。
起初我覺得這是件有趣的事,但當我花越多時間聽保羅說話,我就越對這個監獄的工作人員感到肅然起敬,尤其是喬西,因為他們必須管理這群極難相處的人。我也漸漸發現,保羅絕非是利用「一點戲謔」來讓大家辛苦的生活變得有趣。實際上,他到處散播毒素,選擇性地釋放謠言和酸言酸語,好讓監獄的工作人員有事可忙,同時讓其他囚犯因為擔心違禁行為被洩露,而無暇挑戰他。
當然,我遲早也會成為保羅編導的好戲中的受害者。
身為監獄的非獄方管理員,我最大的挑戰之一,是設法弄清在監獄工作人員經驗範圍以外的事。這些工作人員是按照朝九晚五的時間上班,他們的工作內容可謂安全且乏味,就像各行各業的一般上班族。然而,我的任務就複雜多了,我得定期參加早晨簡報,聽取晚班和大夜班期間發生的可怕故事。
我確定值「A班」是要瞭解各種狀況的唯一辦法,也就是在監獄裡出勤整整十二個小時的班,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體驗監獄管理員和囚犯們一整天的互動。我需要為此訂定嚴格的計畫:首先,我當時才二十五、六歲,不太習慣在一大早六點鐘爬起床。再者,我需要讓自己一整天都有事可忙,以免過於無聊或疲累而錯過蛛絲馬跡。於是,我向保羅尋求建議。
「老弟,你得一起來吃早餐和晚餐。那時每個人又餓又累,是真正亂成一團的時候。」接著保羅遲疑片刻,若有所思地又說:「你也得來參加隔間會議,時間定在下午兩點。還有哥兒們的談話群組,在下午四點,我會在場。啊對了,還有每天舉行的治療集會,那對你來說真的非常重要!你記下來了嗎?」是的,我記下來了,我相當認真地(或許過於認真)採納了這個嚴重心理病態的男人看似真心誠意的建議。
我一如預期順利值上「A班」,每天早早起床去和大家吃早餐,看著他們為了食物份量爆發半認真的爭吵。我得知有關「幽靈屎人」的事,他每天早上都會弄髒淋浴間。我還被介紹給另一名囚犯派屈克(Patrick),他罵起人來就像拉肚子一樣噴瀉而出,只要稍稍被激怒,他就忍不住吐出一連串令人雞皮疙瘩的髒話,聲音又大又急,但每個字都難以分辨:「操你媽的希望她因為肛門長癌而死翹翹」是相對低調的例子。
我參與每一場安全簡報,看著工作人員遞交大夜班和早班之間的安全資料,努力記錄並試著理解狀況,然後隔天重複所有的行程。另外,我會訪談幾名囚犯,瞭解他們的犯罪史,其中某個個案還涉及將人燒死在車內的罪刑。這是件辛苦異常的工作,當我每晚近八點回到冰冷的出租公寓,一進門只能倒頭就睡,完全顧不得要先完成當天的記錄。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有天我一如往常參加治療定向群組,走進會場時,我才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勁。保羅在場,他顯然對某件事非常、非常介意。
「你他媽的昨天人在哪裡?」他盯著我。
「呃,那個……我……」
「你說好了要來參加哥兒們談話群組!」
我想破了頭:我說過嗎?「我那時在參加治療集會,我以為那是……」
「才怪……什麼爛理由。你們全都一樣,你們這些爛傢伙。我說我會在談話群組等你,你還說你會去!」
我感到窘迫不已。以我的研究計畫的本質,我能參與這些活動,是所有工作人員和囚犯願意配合並接納我的結果。如果有人認我行事不公或缺乏職業素養,那麼我的研究將岌岌可危。
「我真的很抱歉。」我試著開口,「我不知道……」
保羅臉上出現我印象中最具威脅性的冷笑。「你的意思是,你認為你大可以只挑輕鬆的事情做,在你應該努力瞭解囚犯生活的時候,卻跟工作人員廝混在一起。老弟,我還以為你不是那樣的人。」
我環視著眾人,深感羞愧。沒有人迎向我的目光。保羅不屑地搖頭,而帶領定向群體的管理員露易絲更是一臉不以為然,似乎每個人都意識到不能指望我信守承諾。好了,現在還有誰會信任我,願意告訴我重要的事,好讓我完成研究計畫?
當天稍晚我回過了神,突然間明白到,我被一個古老的把戲給愚弄了。那是在電影《搬家》(Moving)中讓理查.普瑞(Richard Pryor)所飾演的角色上當的相同把戲,也就是用一堆玩笑和不相干的閒聊來混淆視聽,並隱藏你認為人們無法從一團混亂中辨識出來的訊息(就像保羅那天真正的目的)。
老實說,我對自己的失望更甚於對保羅的憤怒,我被「瞭解囚犯經驗」的想法沖昏了頭,忘記這些人會入監服刑不是沒有原因。畢竟,保羅並非自願被拘留,而且他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他都能愚弄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那麼一旦他能為所欲為和暢所欲言,該會如何興風作浪。
彷彿為了強化這個觀點,隔天,我設法避開了保羅。然而,當我終於在吉他社團又看見他時,他似乎沒有任何惡意,甚至完全不記得他前天對我的羞辱。他一如既往地親切迷人,只有露易絲似乎對我的態度變得冷淡不少。監獄管理員露易絲為人正派,她給人的印象是無法忍受一丁點違法的事,所以儘管我在技術上沒有犯錯,但道德行為的瑕疵已經得罪了她。至於同個隔間那些年輕男性管理員的不成熟和漫不經心的工作態度,也令她感到不快。
接下來的一週,由於保羅和我都喜歡樂團「電台司令」(Radiohead)的OK
Computer專輯,我們稍稍恢復了友好的關係。保羅問我能否替他從網路上列印一些吉他譜,例如‘Lucky’—正好是專輯中我們最喜歡的曲子—和‘KarmaPolice’等歌曲。我察覺這是一個與保羅重新交好的機會,我或許還能透過他,接通那條小道新聞和局內人消息的管道,因此當晚我盡職地從網路上下載、列印吉他譜並仔細裝訂起來,比準備自己的報告還用心。
然而隔天,當我到達監獄停車場時,我突然冒出一個念頭:監獄裡是否允許帶進訂書針?按刑事司法工作的規矩,最好不要冒這個險。此時成疊的吉他譜還放在我的汽車座位上,我決定拆下釘書針再帶進去,比較安全可靠。所幸事情後來有了轉折,我臨時接獲一個考核任務,必須離開監獄幾週。匆忙中,我完全忘了有關吉他譜的事。而當我回到監獄時,已經不再是當初的菜鳥觀察員,而被行政部門雇用為首席研究員,我成了真正的工作人員。至於那一大疊吉他譜,在雲端儲存和數位化時代來臨之前,早被湮沒在移來挪去、亂成一團的文件中。
我回到監獄的第一天,情況似乎有些不妙。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緊張,沒有人過來道賀我的新工作,甚至沒有跟我招呼。顯然發生了什麼事,但監獄運作一如往常:囚犯在七點五十分開始活動,八點三十分舉行晨會,早上工作,下午進行治療。當我來到隔間看見幾名新來的囚犯,我卻沒看見保羅。
這件事透著怪異,因為保羅理應待在無期徒刑隔間,因為他屬於高度危險性犯人,被判處長期刑期,以及有重度心理病態,不太可能移監,短時間內他哪兒都去不了。那麼保羅人呢?吉他社團要到下週才有活動,而且行程表上,治療定向群組並沒有運作,因此我無法向別的囚犯或工作人員打聽消息。
直到當天很晚,我終於找到了賈姬。打從我進入這所監獄,賈姬就是我的好同事。套用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電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的台詞:就任何監獄而言,她大概都都有點被「旋得太緊」,更別提在滿是心理病態者的最高安全等級監獄。但是她為人忠誠聰穎,深諳監獄的規矩,小道消息靈通,是個很棒的工作伙伴。
當時我在全國最高安全等級的監獄已經任滿兩年,早已見識過許多瘋狂情事,包括違反安全規定、拘禁時死亡、可怕的自殘,或是駭人聽聞的暴力行為。然而賈姬當說出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我依舊驚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