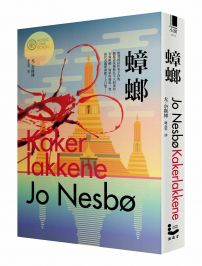1
一月七日,星期二
號誌轉綠,大卡車、轎車、摩托車、嘟嘟車吼聲隆隆,愈來愈響,蒂姆看見羅賓森百貨公司的玻璃都抖了起來。接著車陣開始移動,那面展示紅綢長洋裝的櫥窗就消失在他們身後的黑暗中。
她搭的是計程車,不是擠滿人的公車,也不是鏽跡斑斑的嘟嘟車,而是一輛有空調、司機嘴巴閉得緊緊的計程車。她往後靠上頭枕,盡力享受這趟車程。沒問題的。一輛小綿羊從他們旁邊衝出去,後座的女生穿著緊身紅T恤、戴著擋風鏡安全帽,茫茫然看了他們一眼。抓緊呀,蒂姆心裡想。
他們在拉瑪四世路,司機在一輛大卡車後面停下來。卡車冒出來的廢氣又濃又黑,遮得車牌都看不清楚。廢氣通過空調系統以後冷卻了,變得幾乎沒有味道。幾乎。她含蓄地擺了擺手,露出她的反應;司機瞄了瞄鏡子,把車切到外線。沒問題的。
她的人生向來如此。出身農家,家裡有六個女兒;多了六個,她父親說的。七歲的時候他們站在黃沙中一邊咳嗽一邊揮手,目送載著大姊的牛車顛顛簸簸走上和土色水圳並行的鄉間小路;人家給了姊姊乾淨的衣服、一張往曼谷的火車票,還有寫在名片背面的帕蓬街地址。姊姊的眼淚像瀑布一樣落下,就連蒂姆用力揮手揮得手要斷了也沒用。她母親摸摸她的頭,說那是不輕鬆,但也沒那麼糟,至少姊姊不必在一個又一個農家之間流浪,像她母親嫁人之前一樣,做人家的夸埃(kwai)。再說,黃小姐已經答應了,會好好照顧她。她父親點了點頭,從黑黑的牙齒之間吐出檳榔汁,又補了一句話,說酒吧裡的發郎(farang)願意花大錢買新來的女孩子。
蒂姆本來不明白母親說的夸埃是什麼意思,但她不打算問。她當然知道夸埃就是牛,他們家和周圍大多數的農家一樣買不起牛,該犁田的時候就雇用在附近一帶四處出租的水牛。後來她才知道牽牛的女孩子也叫夸埃,因為她的服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那是傳統。她希望自己可以儘早遇到願意要她的農夫,不會等到過了年紀。
蒂姆十五歲的某一天,父親叫了她的名字;那時他在稻田裡踩著水走,太陽在身後,斗笠在手上。她沒有馬上應聲。她直起腰,細細看著小農地四周的青山,閉上眼睛,聽著葉間喇叭鳥的聲響,呼吸桉樹和橡膠樹的氣味。她知道輪到她了。
頭一年她們四個女孩住一間房,床也好,食物、衣服也好,什麼都共用。衣服又特別重要,因為沒有漂亮衣服,就攬不到最好的客人。她自己學跳舞,自己學微笑,自己學著看哪些男人只想喝酒,哪些想買春。她父親已經跟黃小姐談好錢寄回家裡,所以頭幾年她沒見過幾個錢。不過黃小姐對她很滿意,時間一久,也就多留了一些給蒂姆。
黃小姐滿意有理。蒂姆工作賣力,而且客人會點酒。她還待著沒辭職,黃小姐就該慶幸了,有幾次就差那麼一點。有個日本人想娶她,但是她一開口要機票錢,他就收回提議。有個美國人帶她去普吉島,為她推遲了歸期,還買鑽戒給她;他走的隔天,她把鑽戒拿去當了。
有些人給錢很小氣,要是她抱怨,就會叫她滾。有些人叫她做這做那,要是她不全部照做,就會跟黃小姐投訴。他們不知道一從酒吧買走她的時段,黃小姐那份錢就入袋、蒂姆就是自己的老闆了。她自己的老闆。她想起櫥窗裡的紅洋裝。母親說的沒錯,是不輕鬆,但也沒那麼糟。
而且她做到了保持天真的笑容和開懷的笑聲。他們喜歡。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她才會得到王利在《泰國日報》刊登的那份工作,職稱叫「客戶關係專員」。王利是個皮膚黑的小個子中國人,在市郊的素坤逸路上開汽車旅館,客戶主要是有特殊要求的外國人;說是特殊,也不到她應付不來的地步。坦白說,她喜歡這工作,多過在酒吧跳幾個鐘頭的舞,而且王利給錢大方,唯一的缺點是從她住的邦蘭普區公寓到那裡,要花好長時間。
該死的塞車!車子又完全停住了。她跟司機說要下車,雖然這樣她得穿越塞得滿滿的六個車道,才到得了馬路另一邊的旅館。一下計程車,空氣就像一條又熱又濕的毛巾裹上來。她尋找能走的空隙,一手摀著嘴;她知道摀著也一樣,曼谷沒有別種空氣可以呼吸,不過至少可以擋擋臭味。
她在車陣中穿梭,一度得避開一輛皮卡;那上面坐了滿滿一貨斗的男孩子,都在吹口哨。又有一度她差點被一輛豐田神風勾掉高跟鞋的帶子。然後她到了馬路對面。
王利抬起眼,看著她走進空蕩蕩的接待區。
「晚上沒生意?」她說。
他點頭表示不高興。過去一年有過幾次這種情況。
「妳吃過沒有?」
「吃過了。」她騙他。他是好意,但是她沒心情吃他在裡間煮的稀稀糊糊的麵條。
「妳要等等,」他說,「那個發郎想先睡一覺,他好了會打電話。」
她唉聲嘆氣。「利,你明知道我午夜之前要回到酒吧。」
他看看手錶。「給他一個鐘頭。」
她聳聳肩,坐下來。要是一年前她這樣講話,可能早就被他轟出去,但是現在,能賺的錢他每一塊都得賺。沒錯,她大可走人,只是走掉的話,這一趟大老遠的就是白來了。而且她欠王利人情,比他差的皮條老闆她都遇過。
捻熄第三根菸以後她用王利的苦中國茶漱口,站起來用櫃臺上面的鏡子最後一次檢查妝容。
「我去把他叫醒。」她說。
「嗯。有沒有帶冰鞋?」
她提起她的袋子。
她走在旅館一棟棟矮房之間空蕩的碎石車道上,鞋跟咯吱咯喳響。一二○號房就在最裡面,她沒看見外頭有車,但是窗戶裡有光,所以他可能已經醒了。一股微風掀起她的短裙,卻沒讓她涼快一些。她渴望季風,渴望雨水,就像經歷幾個星期的水災、泥濘和洗晒之衣物發霉後,她會渴望乾燥無風的季節。
她用指節輕輕敲門,掛上她的靦腆笑容,「你叫什麼名字?」已經備在嘴邊。沒人應門。她再敲一次,然後看看手錶。那件洋裝應該可以砍個幾百銖,就算是羅賓森百貨賣的也可以。她轉轉門把,驚訝地發現門沒鎖。
他趴在床上,她乍看之下以為他在睡覺。接著她看見藍色玻璃的反光,玻璃刀柄從那件俗豔的黃外套上突出來。很難說腦海裡閃過的念頭哪一個最早,但肯定有一個是「這一趟大老遠的終究是白來了」。然後她終於動得了聲帶,不過那聲尖叫被洪亮的喇叭聲淹沒,素坤逸路上有輛大卡車正在鳴笛閃避粗心大意的嘟嘟車。
2
一月八日,星期三
「國家劇院。」喇叭傳出懶洋洋帶著鼻音的報站聲音,輕軌電車的門彈開,達格芬.涂魯斯踏入濕冷的黑暗中。空氣刺痛剛剛刮過鬍子的臉頰,藉著奧斯陸市內儉省的霓虹燈光,他可以看見嘴裡呼出凝結的水氣。
現在是一月初,他知道這冬天再過一陣子就會好過些,到時候峽灣結冰,空氣就會乾燥起來。他開始沿著德拉門路往外交部走。孤零零的計程車從他身旁駛過,就那麼兩三輛,此外街道彷如空城。對面大樓的互利人壽大鐘在黑暗的冬日天空中亮著紅光,告訴他現在才六點。
他在門口拿出他的門禁卡。「職務:處長」這行字印在達格芬.涂魯斯十年前的大頭照上方,照片裡鋼邊鏡框後面的眼睛盯著相機,下巴突出,眼神堅定。他刷了卡,按了密碼,推開維多利亞露臺大樓沉重的玻璃門。
涂魯斯簽了名,對警衛點點頭。警衛把他的報紙和一枚信封從玻璃窗底下推過來。
「有別人……?」
警衛搖頭。
「你最早到,涂魯斯,向來都是。信封來自通訊處,昨晚送過來的。」
大樓電梯一路往上,涂魯斯看著樓層號碼閃過一個又一個。他認為每一個樓層代表自己生涯的一個時期,所以每個早上都要回顧一遍。
二樓是外交學程的頭兩年,那些漫長又沒有明確答案的政治、歷史研討,還有懸梁刺股熬過的法文課。
三樓是分發駐外。他在坎培拉待過兩年,之後墨西哥市三年。說起來算是很棒的城市了。對,沒得抱怨。他是把倫敦和紐約列為第一志願沒錯,但這兩個派駐地是人人爭著申請的寶座,所以他也打定了主意,不把這件事看作失敗。
四樓,他回到挪威,少了豐厚的駐外加給、房屋津貼,和隨之而來的富裕無憂生活。他認識了貝莉特,貝莉特懷了小孩,等到可以申請外派職務的時候,她又懷了第二胎。貝莉特跟他出身同一個地區,每天都要跟她媽媽聊天。他決定再等一等,決定賣力工作,連篇累牘地寫報告分析與開發中國家的雙邊貿易,替外交部長擬演講稿,隨著一路往樓上爬,得到他應得的認可。國家體制裡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競爭像外交部這麼激烈,這裡的階級分隔好明顯,達格芬上班就像士兵上前線,頭低低的,背掩護好,看到人就開槍。有幾次也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知道他已經得到「關愛的眼神」,所以努力跟貝莉特解釋,自己可能弄得到巴黎或倫敦,但是貝莉特在他們平淡的婚姻有史以來第一次堅持己見,執意不讓。他屈服了。
他往上爬升的態勢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某一天早上他突然在浴室鏡子裡看見一個被推進支線軌道的處長,一個稍微有點影響力但永遠到不了六樓的官員;再過十年左右就要退休的人,怎麼可能到得了。當然啦,如果他能搞一條大的,那就另當別論,可是那種把戲弄得好是升遷,弄不好是滾蛋。
無論如何,他還是一如既往,努力搶在別人前面。每天早上他第一個到辦公室,可以安安靜靜讀報看傳真;開晨會的時候,別人剛坐下來揉揉惺忪睡眼,他已經想好結論,好像打拚的精神已經進入他的血液一樣。
他打開通訊處送來的信封,加密傳真的還原文稿蓋了「極機密」三個字,文中的訊息害他灑了咖啡,波及桌上四散的文件。短短的內文留下許多想像空間,但是箇中要義基本上是這樣的:挪威駐泰國大使奧特樂.墨內斯陳屍曼谷一處妓院,背上插著一把刀。
涂魯斯把傳真再讀了一遍才放下來。
奧特樂.墨內斯,前基督教民主黨政治家,前金融委員會主席(現在不管什麼身分都得冠上「前」字了)。實在太難以置信,他免不了往阿克爾旅店瞥一眼,看看窗簾後面是不是站著人。發文者是曼谷的挪威大使館,相當合理。涂魯斯罵了聲髒話。這事什麼時候不發生,偏偏是現在?哪個地方不發生,偏偏是曼谷?該不該先通知內閣大臣歐斯基德森?不用,他很快就會知道了。涂魯斯看看手錶,拿起話筒撥給外交部長。
畢悠納.莫勒輕輕敲了敲門然後打開,會議室裡的聲音都安靜下來,一張張臉轉過來對著他。
「這位是畢悠納.莫勒,犯罪特警隊隊長。」警察局長一邊說,一邊招手讓他坐下。「莫勒,這位是首相辦公室內閣大臣歐斯基德森,還有外交部人事處處長達格芬.涂魯斯。」
莫勒點點頭,拉出一把椅子,想辦法把那雙不可思議的長腿塞進橢圓大橡木桌底下。他好像在電視上看過歐斯基德森那張年輕光滑的臉。首相辦公室?一定出了大事。
「你這麼快趕過來真是太好了。」內閣大臣捲著他的捲舌音,用手指神經兮兮地敲著桌子。「局長,請妳簡報一下我們剛才討論的內容。」
二十分鐘前莫勒接到警察局長打來的電話。她一句解釋都沒有,只是限他十五分鐘內趕到外交部。
「奧特樂.墨內斯被人發現陳屍在曼谷,可能是謀殺。」局長開始說。
莫勒看見涂魯斯處長正在鋼邊鏡框後面翻白眼,等到聽完全部的敘述,他就明白了處長的反應。只有幹警察的才會把一個人背脊側邊插了一把刀、穿過肺臟又刺進心臟,說成「可能」是遭到謀殺。
「陳屍地點是旅社房間,發現屍體的是一名女性—」
「妓院房間,」戴鋼邊鏡框的人插嘴,「一名妓女。」
「我跟一個曼谷的同僚聊過,」警察局長說,「他是個明白人,已經答應暫時把消息壓下來。」
莫勒的第一個直覺是質疑,為何要延後公開謀殺案?讓媒體馬上報導,通常都可以引來線報,因為大家記憶猶新,證據都還乾淨新鮮。可是直覺告訴他這個問題會被看作幼稚得可以。他改問他們指望消息能壓多久。
「至少夠我們整理出端得上檯面的事件報告,」內閣大臣說,「現在這個版本不能用,你懂吧。」
現在這個?所以他們考慮過後,把真實版本否決掉了。莫勒這個犯罪特警隊隊長算是新官上任不久,目前為止還不必跟政客打交道,但是他知道職位升得愈高,就愈難跟他們保持距離。
「我懂現在這個版本很尷尬,但你說『不能用』的意思是?」
警察局長對莫勒使了個告誡的眼色。
內閣大臣看起來不為所動。「我們沒多少時間,莫勒,不過我給你上一堂政治實務速成課。當然,我現在說的每一件事都要嚴格保密。」
歐斯基德森想都不想就調整了一下領帶的結,莫勒記得在他的電視訪問中看過這動作。「打從大戰結束以後,我們第一次有中間路線的政黨得到夠大的機會存活下來。這不是因為有國會的基礎,而是因為首相剛好就快要成為本國最不討人厭的政客。」
警察局長和外交部的處長露出微笑。
「可是呢,他的民望高低建築在一個易碎的基礎上,也就是他們的主力商品:信任。所有政壇人士都是這樣,最重要的不是討人喜歡或展現領袖魅力,而是獲得信賴。你知道為什麼前首相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那麼受歡迎嗎,莫勒?」
莫勒不知道。
「不是因為她迷人,而是因為民眾相信她言行合一。信賴,信賴是關鍵詞。」
同桌其他人都點頭,這顯然是課綱的一部分。
「再來,墨內斯大使和我們現任首相關係密切,兩人不但是好朋友,政治之路也緊密交織。他們一起求學,一起在黨內崛起,從現代的青年運動打出生路;當時他們年紀輕輕就一起選上議員,兩個人甚至還合租一間公寓。兩個都成為黨主席熱門人選的時候,墨內斯自願退出聚光燈焦點,全力支持首相,我們才免去了一場折磨人的黨內對決。以上這些意思很明顯,就是首相欠墨內斯人情。」
歐斯基德森舔了舔嘴脣,往窗外看出去。
「換句話說,墨內斯大使沒受過任何外交訓練,要不是首相使力,他也不會去曼谷。這話聽起來可能有裙帶關係的味道,但是這種裙帶關係還是可以接受的,始作俑者是國家社會黨,廣為應用的也是國家社會黨。瑞夫.斯特恩(Reiulf Steen)當上駐智利大使的時候,也沒有任何外交部資歷。」
那雙眼睛重新聚焦到莫勒身上,一絲調皮的神色正在裡面閃耀。
「我確定我不必多加強調,你也知道這件事會如何破壞人民對首相的信賴,我是說萬一大家知道他的好友兼黨內同志、他親自任命的大使,被人發現身在妓院,而且還死於謀殺。」
內閣大臣擺擺手請警察局長繼續說,但是莫勒忍不住。
「誰沒有朋友去過妓院?」
歐斯基德森的微笑捲起嘴角。
戴鋼邊鏡框那個外交部處長咳了幾聲。「你該知道的都知道了,莫勒,請相信我們的判斷。現在需要有人來確保調查方向不會轉到……不恰當的方向。不用說,我們大家都希望緝凶歸案,一個也好,有共犯也好,但是謀殺案相關情節必須保密,到將來另行通知為止。為了國家好,你懂了嗎?」
莫勒低頭看著手。為了國家好。去你的。他家的人從來就不擅長聽命行事,他父親的警階從來沒有往上升。
「經驗告訴我們,真相通常很難隱藏,涂魯斯先生。」
「確實。我會代表外交部負責這項任務。你也知道,這件事有點難辦,需要跟泰國警方密切配合。因為事涉大使,所以我們多了一些緩衝空間,有外交豁免權什麼的,但我們走的還是條高空鋼索。所以我們希望派去的人辦案技巧熟練,有跨國警務經驗,又辦得出結果。」
他停下來看著莫勒。莫勒正在思考,為什麼自己對這位下巴很有衝勁的外交官莫名地就是沒好感。
「我們可以弄一個小組—」
「不要小組,莫勒,太顯眼。而且你們局長覺得派大隊人馬去,對於跟當地警方打好關係沒什麼幫助。派一個人。」
「一個?」
「局長已經有建議的人選,我們認為不錯,現在想問問你對這個人的看法。局長跟雪梨的同僚聊過,據說這個人去年冬天在那裡辦英格.霍爾特謀殺案,表現出色。」
「我在報上看過案情,」歐斯基德森說,「讓我印象深刻。應該就是他了吧?」
莫勒吞了吞口水。所以局長已經建議派哈利.霍勒去曼谷,叫他過來,只是要讓他保證哈利是最優秀的警力,是這件差事的最佳人選。
他環視會議桌。政治,權力,影響力。這是一場他根本沒辦法了解的遊戲,但是他知道這件事最後總有辦法替他加分,知道他現在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會左右他的仕途。警察局長建議了人選,就是把脖子伸了出去,可能他們哪一個人就要求找霍勒的直屬長官背書吧。他看著他的大老闆,想解讀她的表情。當然啦,哈利的狀況也可能會順遂起來,而且如果他建議不要派哈利,不是會害局長倒楣嗎?他自己也會被他們要求提出替代人選,結果換成「他的」頭在砧板上,如果那個警員搞砸的話。
莫勒看著掛在警察局長頭上的畫。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首任聯合國祕書長,挪威人,一副傲慢跋扈的樣子俯視著他。又一個政客。透過窗戶,他看見冬季微弱日照中的公寓屋頂、阿克修斯堡壘,還有佇立歐陸飯店頂端、在寒風中顫抖的公雞風標。
莫勒知道自己是個稱職的警察,但是這門遊戲不一樣,而且他不知道規則。他父親會建議他怎麼做?嗯,當時莫勒警員從來不需要應付政治,卻知道如果自己想要讓人家把他放在眼裡,什麼事情最重要,而且還規定兒子要完成第一階段法律學程,才能進入警察學院。他乖乖照父親說的做,畢業典禮結束後,父親情緒激動,一直清喉嚨,一直拍著兒子的背,拍到他不得不叫停為止。
「好建議。」莫勒聽到自己用清楚響亮的聲音說。
「很好,」涂魯斯說,「我們想要這麼快聽到意見是因為……當然啦,一切都很緊急。他得放下手上所有事情,明天就走。」
好吧,或許此刻哈利需要的就是這種工作,莫勒希望如此。
「抱歉,我們得拿走你的一員大將。」歐斯基德森說。
犯罪特警隊隊長畢悠納.莫勒得克制自己,才不會爆出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