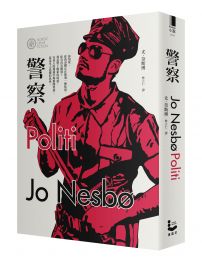序幕
它在門內沉睡。
轉角櫃裡瀰漫著老木頭、殘餘火藥和擦槍油的氣味。每當陽光從窗外照進房內,就會穿過櫃門的鑰匙孔,形成沙漏狀的光束,射進櫃子。陽光只要移動到某個角度,光束就會落在中間的層架上,讓它在層架上發出黯淡光芒。
它是一把敖德薩手槍,是小有名氣的斯捷奇金手槍的山寨版。
這把外型醜陋的自動手槍有一段流浪漂泊的過往,它曾被立陶宛的哥薩克人帶去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南部的多個厄爾卡據點之間移動,成為哥薩克領導人「阿塔曼」的所有物,後來被警察拿來殺了這個阿塔曼,再流落到下塔吉爾市一位喜歡收集槍枝的典獄長家中。最後魯道夫.阿薩耶夫把它帶來挪威。魯道夫外號「杜拜」,失蹤前曾以一種類似海洛英的鴉片類藥物「小提琴」壟斷奧斯陸毒品市場。如今這把手槍就在奧斯陸,就在侯曼科倫區,就在蘿凱.樊科的大宅裡。這把敖德薩手槍的彈匣可裝填二十發馬卡洛夫子彈,口徑9×18毫米,一次可發射一枚子彈,也可連射數發。目前彈匣裡還有十二發子彈。
已擊發的八發子彈中,三發用來瞄準競爭對手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藥頭,只有一發命中。
另外兩發子彈射殺了賈斯托.韓森,他是個少年竊賊,也是藥頭,曾竊取魯道夫的錢和毒品。
現在這把手槍依然飄散著最後三發射出子彈的火藥氣味。這三發子彈擊中了前任警官哈利.霍勒的頭部和胸部,當時他正在追查賈斯托命案,而他遭子彈擊中的地點正好就是賈斯托命案的現場:黑斯默街九十二號。
警方依然未能偵破賈斯托命案,案發後遭逮捕的十八歲少年也已獲釋,主因是警方找不到凶槍,也無法把少年跟任何武器連結起來。少年名叫歐雷克.樊科,他每晚都在睡夢中因為聽見槍聲而驚醒,瞪大眼睛看著黑夜。他聽見的槍聲並非來自射殺賈斯托的那兩發子彈,而是另外那三發。那三發子彈射中的警察在歐雷克的成長過程中對他而言如同父親。他曾夢想這位警察—也就是哈利—會娶他母親蘿凱為妻。歐雷克用灼灼目光望著黑夜,心思繫在房間另一側那個轉角櫃裡的手槍上。他希望自己永遠不會再見到那把槍,也希望沒有人會再見到那把槍。他希望那把槍就這樣靜靜躺著,沉睡到永遠。
他在門內沉睡。
這間病房有警衛看守,房裡瀰漫著藥品和油漆的氣味,床邊的監視器顯示他的心跳。
奧斯陸市政廳的社福議員伊莎貝拉.斯科延,以及剛上任的奧斯陸警察署長米凱.貝爾曼,都希望自己不會再見到他。
他們希望沒有人會再見到他。
希望他就這樣靜靜躺著,沉睡到永遠。
※ ※ ※
警員安東.米塔從紅色的奈斯派索D290小型咖啡機上拿起半滿的塑膠杯,彎腰放在地上,因為四周沒有桌椅可以放置。他拿起另一個咖啡膠囊,下意識地查看鋁箔包裝上是否沒穿孔,表示沒使用過,才把它放進咖啡機,然後拿個空塑膠杯放在噴嘴底下,按下一個亮燈的按鈕。
他看了看錶。咖啡機發出呻吟聲,噴出液體。午夜十二點的換班時間就快到了。她正在家裡等他。但他心想應該先教教新來的女同事熟悉這裡的規矩才行,畢竟她還只是個實習生。女同事的名字是不是叫西莉亞?安東看著噴出的液體。如果換作是男生,他還會不會主動幫忙拿咖啡?他不確定,反正無所謂,他早已放棄回答這類問題。房裡突然安靜下來,他聽見最後幾滴近乎透明的液體滴進杯子。膠囊裡的顏色和味道都用完了,但一定要連最後一滴液體也接住才行。對那位年輕女同事來說,這個大夜班將會非常漫長,沒人陪伴、沒有活動、無事可做,只能盯著國立醫院裡尚未上漆的光禿水泥牆,也因此他決定離開前要跟她喝杯咖啡。他拿著兩個塑膠杯往回走,腳步聲迴盪在四壁之間,穿過緊閉且上鎖的一扇扇房門,心裡知道門內沒東西也沒人,有的只是更多的光禿牆壁。至少這次挪威政府藉由擴建國立醫院來鞏固國家的未來,明白挪威人民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年老、衰弱、貪婪。政府做了長遠打算,一如德國人建造高速公路、瑞典人建造機場。但德國人和瑞典人是否有過這種感覺?三○年代穿過德國壯麗荒野而行駛在水泥巨物上的機車騎士,或是六○年代匆匆穿越過於龐大的阿蘭達機場的瑞典旅客,是否也有過這種感覺?他們是否感覺到鬼魂的存在?儘管這些大型建設全新落成,未遭破壞,尚未發生車禍或墜機,但鬼魂已然存在。汽車車燈隨時可能照到站在人行道上的一家子,他們茫然地看著車燈,身上淌血,皮膚蒼白,父親遭尖物刺穿,母親頭部扭向怪異方向,孩子失去一隻胳臂和一條腿。燒得焦黑的屍體穿過行李轉盤的塑膠簾,進入阿蘭達機場的入境大廳,身上依然發出高熱、引燃橡膠,張開的嘴巴發出無聲慘叫、冒著裊裊黑煙。沒有一位醫生能告訴安東說醫院這個側翼未來要做什麼用途,唯一能確定的只是未來有人會死在這些門內。這種氛圍已然瀰漫在四周,看不見的屍體帶著躁動不安的靈魂已被醫院收治。
安東彎過轉角,眼前出現另一條走廊,走廊上燈影稀疏、牆壁光禿、兩側對稱,給他一種彷彿看見立體錯視畫的奇特感覺。所謂立體錯視畫就是運用作畫技巧在平面上呈現出三度空間的畫作。走廊遠端坐著一名制服女子,看起來宛如牆上掛的一小幅畫。
「這杯咖啡給妳。」他說,在女子身旁停下腳步。她是不是二十歲?不對,應該再成熟一點,可能二十二。
「謝謝,我自己有帶。」女子說,從放在椅子旁邊的小背包裡拿出一個保溫瓶。她的語調隱約有一絲輕快感,可能是因為帶有北部方言的口音。
「這比較好喝喔。」安東說,手依然伸在半空中。
女子遲疑片刻,接過杯子。
「而且免費,」安東說,不動聲色地把手負在身後,將熱燙的指尖貼在冰冷的外套上。「那邊有台咖啡機我們可以隨意使用,就在走廊的……」
「我來的時候看見了,」她說:「可是依照規定我們不能離開病房門口,所以我自己從家裡帶咖啡來。」
安東喝了口咖啡。「想得很周到,可是通到這間病房的走廊只有一條,這裡是四樓,而且從這裡到咖啡機之間的門全都上了鎖,就算我們正在煮咖啡,也不可能有人通過而不被看見。」
「聽起來很安全,但我還是守規定比較好。」她對安東淺淺一笑,接著可能為了抵銷自己態度中所隱含的斥責意味,啜飲了一口咖啡。
安東有點惱怒,正想說經驗的累積可以促進獨立思考,話還沒到口邊,就注意到走廊深處似乎有動靜,彷彿有個白色人影朝這裡飄來。他聽見西莉亞站起身。人影逐漸清楚,原來是個豐腴的金髮護士,身穿寬鬆的醫院制服。安東知道這名護士今晚值夜班,明晚休假。
「晚安。」護士說,露出頑皮微笑,手拿兩支針筒,走到病房門前,伸手握住門把。
「等一下,」西莉亞說,上前一步。「我得看一下妳的證件,還有,妳有今天的密語嗎?」
護士對安東露出驚訝表情。
「除非我同事可以為妳擔保。」西莉亞說。
安東點了點頭。「進去吧,夢娜。」
護士把門打開,安東看著她走進門內。病房裡黑魆魆地,安東依稀看見床邊擺著儀器,被子底下有腳趾突出。這位患者很高,院方不得不調來一張加長型病床。房門關上。
「做得好。」安東說,對西莉亞笑了笑,同時察覺她不喜歡這種態度,也察覺她認為他是男性沙文主義者,把年輕女同事視為低等之人。可是老天爺,她不過是個實習生,受訓期間應該跟資深員警學習才對。安東身體微晃,不確定該如何處理眼前這種情況。西莉亞先開口說話。
「我剛剛說過,規定我都讀過了。你的家人應該在等你回家吧?」
安東把咖啡杯湊到口邊。她對他的婚姻狀況有什麼了解?難道她在暗示他跟夢娜之間有不尋常的關係?難道她知道他曾多次在夢娜下班後載她回家,而且還有進一步發展?
「你的包包上有泰迪熊貼紙。」西莉亞微微一笑。
安東喝了一大口咖啡,清了清喉嚨。「我沒什麼事,今天又是妳第一天值班,也許妳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提出疑問,妳知道,不是每件事規定上都有寫。」他變換站姿,希望她聽出他的言外之意。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囉,」西莉亞說,語氣中帶著二十五歲以下才有的狂妄自信。「裡面那個病人是誰?」
「我不知道。規定裡面有寫說他的身分不能透露,必須保持匿名。」
「可是你知道內情。」
「是嗎?」
「夢娜。你一定跟她聊過,才會用名字叫她。她跟你說了什麼?」
安東打量西莉亞。她頗有姿色,這點可以肯定,但她不親切,也不嫵媚,對他來說身材有點太瘦。她頭髮凌亂,上唇彷彿給太緊的肌腱拉住,露出不整齊的門牙,但仍青春無敵。他敢打賭,她黑色制服底下的肉體肯定緊實勻稱。如果他把知道的事告訴她,會不會是因為他下意識做了算計,希望順從的態度可以讓自己跟她上床的機率提高萬分之一?或者是因為像西莉亞這樣的女子五年內就能當上警監或警探?她們會成為他的上司,而他仍會是基層員警,位於晉升階梯的最底層,只因德拉門命案永遠會像一堵牆般擋在前方,是個難以抹滅的汙點。
「謀殺未遂案,」安東說:「大量失血,送進醫院的時候幾乎沒有脈搏,始終處於昏迷狀態。」
「為什麼要派人看守?」
安東聳了聳肩。「他撐過來的話可能成為證人。」
「他知道什麼?」
「跟毒品有關的事,層級很高,他如果醒來,提供的線索也許可以把奧斯陸的海洛英大毒梟繩之以法,我們也可以知道當初是誰想置他於死地。」
「所以長官認為凶手可能回來把他了結?」
「對。對方如果發現他還活著,又得知他在這裡,的確可能回來再度下手,這就是我們得在這裡看守的原因。」
西莉亞點了點頭。「他撐得過來嗎?」
安東搖了搖頭。「院方認為他們可以幫他維持幾個月的生命,可是他脫離昏迷的機率很低。反正呢……」安東又變換站姿,她追根究柢的目光令他覺得不自在。「在他醒來以前我們都得守在這裡。」
安東跟西莉亞道別,心情沮喪,從接待區步下樓梯,走進秋日夜晚,坐上他停在停車場的車子,這才發現手機在響。
是勤務中心打來的。
「馬里達倫谷發生命案,」值班人員說:「我知道你剛下班,可是他們需要人手搜查犯罪現場,你又已經穿上制服……」
「要多久?」
「最多三小時就會讓你離開。」
安東十分訝異。由於嚴格的規定加上預算限制,警方現在都盡量避免讓人員加班,就算為了方便調度也不能破例,因此他直覺認為這起命案一定有特殊之處,只希望被害人不是小孩。
「好。」安東說。
「我會把座標傳給你。」現在警方有了新配備,那就是衛星導航機,內建詳細的奧斯陸各區地圖和訊號發報器,可讓勤務中心追蹤位置。值班人員一定是根據位置資訊跟他聯絡的,因為他離命案現場最近。
「好,」安東說:「三小時。」
三小時後蘿拉應該已經上床睡覺了,但她習慣知道他會幾點下班回家,於是他傳簡訊給她,然後打入排檔,朝馬里達湖前進。
安東根本不用看衛星導航。伍立弗斯特路口停著四輛警車,再過去還拉起橘白相間的封鎖線,說明這裡就是命案現場。
他從置物箱拿出手電筒,朝封鎖線外的員警走去。樹林裡除了有閃光,還有刑事鑑識小組的探照燈燈光,這些亮光總讓他聯想到拍片現場。這些大陣仗其實一點也不愚蠢。現在鑑識人員不只拍照片,還拍攝高畫質影片,除了拍攝被害人,也拍攝犯罪現場,以便日後重複觀看,停格放大,查看先前以為無關案情的線索細節。
「發生了什麼事?」安東問一名員警,那員警雙臂交抱,在封鎖線旁簌簌發抖。
「命案。」員警話聲沉重,眼眶泛紅,臉色異常蒼白。
「我聽說了。這裡誰負責指揮?」
「鑑識中心的隆恩。」
安東聽見樹林裡傳來嗡嗡話聲,顯然鑑識中心來了很多人。「克里波和犯罪特警隊還沒派人來嗎?」
「等一下有更多同仁會來,屍體才剛發現不久。你是來接替我的嗎?」
有更多同仁會來。儘管如此,勤務中心卻還是把他調來加班。安東仔細打量那名員警,只見他身穿厚外套,身體卻抖得越來越厲害,天氣應該沒那麼冷才對。
「你是第一個抵達現場的?」
員警點點頭,默然不語,低頭用力跺了跺腳。
安東心想,媽的這小子還太嫩。他吞了口口水。
「安東,是值班人員派你來的嗎?」
安東抬頭望去,只見兩人穿過灌木叢走來,但他卻沒聽見他們發出聲音。他見過鑑識人員像笨拙的舞者般扭曲身體,在犯罪現場以這種姿態走路,小心翼翼踏出腳步,彷彿是在月球上漫步的太空人。讓他聯想到太空人的也許是他們身上的白色連身工作服。
「對,我是來接班的。」安東對女子說。他認得女子,警界裡應該沒有人不認得她,她就是鑑識中心主任貝雅特.隆恩,有「女雨人」的稱號,因為她擁有超強的臉孔辨識能力,經常在指認銀行搶犯或模糊破碎的閉路監視影片時派上用場。據說只要是前科犯,就算經過仔細偽裝,她還是認得出來,而且她那頭金髮底下的小巧腦袋儲存了數千張大頭照。看來這起命案一定很特殊,否則不會三更半夜驚動上級長官親自出馬。
貝雅特身形嬌小,面色蒼白近乎透明,但她身旁的男同事卻滿臉通紅。他面有雀斑,臉頰上留著兩片紅色絡腮鬍,雙眼略為突出,彷彿腦壓過高,讓他呈現出瞠目而視的表情。不過他全身上下最引人注目的,是當他除下白色兜帽時露出的一頂雷鬼帽,顏色是由綠、黃、黑組成的牙買加配色。
貝雅特拍了拍那名顫抖員警的肩膀。「你先回去吧,賽門。建議你喝點烈酒再上床睡覺,不過別跟人說是我叫你這樣做的。」
賽門點了點頭,三秒鐘後就消失在黑夜之中。
「現場狀況是不是很可怕?」安東問道。
「你沒帶咖啡來?」雷鬼帽男子問,打開一個保溫瓶。安東一聽男子的口音就知道他來自外地,不是奧斯陸人。一如大多數出身東部地區的挪威人,安東對方言既沒概念也沒興趣。
「沒有。」安東說。
「來犯罪現場最好自己帶咖啡,」雷鬼帽男子說:「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會待多久。」
「別這樣,畢爾,他也調查過命案,」貝雅特說:「是德拉門命案對不對?」
「對,」安東說,搖晃腳跟。其實應該說他「以前」負責調查命案。他沒想到貝雅特竟然會記得他。他吸了口氣。「是誰發現屍體的?」
「就是他。」貝雅特說,朝賽門駕駛的那輛警車點了點頭。引擎聲響起。
「我的意思是誰報案的?」
「死者的老婆,因為死者外出騎自行車卻遲遲沒回家,」雷鬼帽男子說:「他出去了一個小時,老婆擔心他心臟病發。他有用衛星導航,裡頭有發報器,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人了。」
安東緩緩點頭,想像這副情景:一男一女兩名警員按下門鈴,看著死者的妻子,咳了一聲,神情肅穆。這表情是為了告訴這位未亡人說,他們帶來的是難以開口的壞消息。未亡人露出抗拒的表情,一點也不想聽,但內在的情緒卻如潰堤般爆發出來。
安東的腦海中浮現妻子蘿拉的容顏。
一輛救護車駛來,沒開警笛,也沒閃藍色警示燈。
安東心裡逐漸明白:警方對失蹤報案快速回應,立刻追蹤衛星導航機的訊號,派出大批警力還要求人員加班,還有一位警員渾身發抖無法自抑只好先行返家。
「死者是警察對不對?」他低聲說。
「我猜這裡的氣溫應該比市區低個一度半。」貝雅特說,撥打手機裡的某個號碼。
「我同意,」雷鬼帽男子說,把保溫瓶蓋湊到嘴邊,喝了一大口咖啡。「皮膚還沒變色,所以大概介於八點到十點之間?」
「死者是警察,」安東又說了一次。「這就是為什麼會派這麼多人來這裡對不對?」
「卡翠娜?」貝雅特說:「妳能不能幫我查個資料?珊卓拉.譚維登命案,對。」
「該死!」雷鬼帽男子高聲說:「我叫他們等屍袋來再移動的。」
安東轉過頭去,只見兩名男子抬著一副擔架,費力地穿過樹林。白布底下露出一雙自行車鞋。
「賽門認識死者,」安東說:「所以才抖成那樣對不對?」
「賽門說他們在厄肯區一起工作過,那時費尼斯拉還沒調去克里波。」雷鬼帽男子說。
「找到日期了嗎?」貝雅特對手機說。
一聲大叫傳來。
「搞什麼……?」雷鬼帽男子說。
安東轉過頭去,只見一名抬擔架的警員在小徑旁的水溝裡滑倒,手電筒的光束掃過擔架、掃過滑落的白布,也掃過……那是什麼?安東凝目望去。那是頭部嗎?躺在擔架上的確實是一具屍體,但那真的是頭部嗎?安東在犯下那個「重大缺失」之前,曾在犯罪特警隊任職多年,也看過不少屍體,但卻從未看過這種狀態的屍體。那個沙漏狀的物體令他聯想到週日家裡的早餐,聯想到蘿拉煮的半熟白煮蛋,上頭依然掛著幾片蛋殼,從破掉的蛋流出的蛋黃已乾,沾在半軟的蛋白上。那真的是……一顆頭嗎?
救護車的後車燈消失在夜色中,安東呆呆望著黑夜,不斷眨眼。他突然發現這一切彷彿是重播。他見過類似的情景:身穿白衣的人員、保溫瓶、白布底下露出的雙腳。這些就跟剛才他在國立醫院看見的情景相仿,彷彿那是預兆一般。還有那顆頭……
「謝啦,卡翠娜。」貝雅特說。
「妳在問什麼?」雷鬼帽男子問。
「我跟艾爾倫在這裡工作過。」貝雅特說。
「這裡?」雷鬼帽男子問說。
「就在這裡。當時艾爾倫負責調查一起命案,那應該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死者名叫珊卓拉.譚維登,遭人強暴殺害。她年紀很小,還只是個孩子。」
安東吞了口口水。孩子。重播。
「我記得那件案子,」雷鬼帽男子說:「命運真是捉弄人,讓你死在自己調查過的命案現場。妳想想看,珊卓拉命案不也是發生在秋天嗎?」
貝雅特緩緩點頭。
安東眨眼,不停眨眼。他曾經見過那樣子的屍體。
「該死!」雷鬼帽男子低低咒罵一聲。「妳該不是那個意思吧……?」
貝雅特拿過他手中的咖啡,啜飲一口,再放回他手上,點了點頭。
「喔,靠。」雷鬼帽男子低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