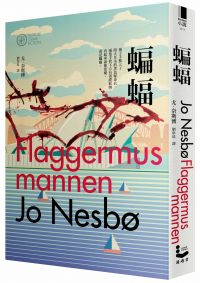1 雪梨
事情不太妙。
一開始,女入境官還滿臉笑容:「你好嗎,老兄?」
「我很好。」哈利.霍勒說謊。他從奧斯陸搭機飛往倫敦已經是三十幾個小時前的事了,在巴林轉機後,又再度坐在緊急出口旁那個該死的位置上。他的椅背出於安全理由只能稍微往後仰,抵達新加坡時,他的腰幾乎要斷了。
此時櫃檯後方的女人不再面露微笑。
她明顯對他的護照產生了興趣,仔細檢查,很難說是因為照片或他的名字,才使她突然變得如此興致盎然。
「出差?」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入境官,都會在句子最後加上「先生」二字,因此哈利有點懷疑這種一本正經的打趣方式,是否在澳洲特別普遍。這不重要。哈利原本就不太習慣出國旅遊,也不勢利眼──他只想儘快得到一個飯店房間與一張床。
「對。」他回答,手指在櫃檯上敲打著。
只見她噘起了嘴,變得難纏起來,以尖銳的語調一字一句地說:「那為什麼你的護照裡沒有簽證,先生?」
他的心一沉,正如同每次有麻煩將至時一樣。或許「先生」這兩個字其實只會用在事態嚴重的時候?
「對不起,我忘了。」哈利咕噥著說,拚命翻找內側口袋。他們為什麼不把特殊簽證用迴紋針別在護照上,就像平常的簽證那樣?他聽見微弱的隨身聽聲響自他身後隊伍中傳來,接著才意識到聲音來自他飛機上的旅途良伴。他在整個航程中,不斷播放同一卷錄音帶。為什麼他總是該死的記不得自己把東西放進哪一個口袋裡?就算現在快要晚上十點了,還是很熱。哈利覺得頭皮開始癢了起來。
最後他找到了簽證,放到櫃檯上頭,這才如釋重負。
「你是警察?」
原本低頭看著特殊簽證的入境官抬頭打量著他,但已經不再噘著嘴了。
「希望不是什麼挪威金髮女郎被殺了。」
她輕笑著,用力在特殊簽證上頭蓋了章。
「這個嘛,是有一個。」哈利回答。
機場大廳擠滿了導遊與接送司機,全拿著寫有名字的紙牌,但視線所及,卻沒半張寫著霍勒。他正打算去叫輛計程車時,一名身穿淺藍色牛仔褲與夏威夷襯衫的黑人男子,從眾多紙牌間開出一條通道,大步走來。那名黑人的鼻翼極寬,一頭深色卷髮。
「你一定是霍利先生!」他自信滿滿地說。
哈利暗忖,自己得決定在澳洲的前幾天,是否要糾正大家對他姓氏的發音才行,否則會搞不清對方是在叫他,或是在講投資的事。不管怎樣,「獲利」先生聽起來都太炫富了。
「你好啊,我是安德魯.肯辛頓。」那人綻開笑容,伸出巨大的拳頭。
手勁簡直與一台榨汁機相差無幾。
「歡迎來到雪梨,希望你旅途愉快。」這名陌生人的口氣帶有由衷之情,彷彿二十分鐘前空中小姐廣播內容的回音。他接過哈利破舊的行李箱,頭也不回地朝出口走去。哈利緊跟在後。
「你是雪梨警方的人?」他問。
「當然啦,老兄。小心!」
迴轉門打上哈利的臉,正中鼻子,使他痛得流出眼淚。就連一部差勁的胡鬧喜劇也不會這麼拍。他揉著鼻子,以挪威語咒罵。肯辛頓對他露出同情之色。
「這門真該死,對吧?」他說。
哈利沒回答。他不知道在澳洲該怎麼回答這種話才恰當。
停車場中,肯辛頓打開一輛又小又舊的豐田汽車後車廂,把行李箱塞進去。「你想開車嗎,老兄?」他驚訝地問。
哈利這才醒悟到自己坐在駕駛座上。對了,澳洲是天殺的靠左駕駛的。但副駕駛座上堆滿紙張、錄音帶與垃圾,哈利只好擠進後座。
「你一定是原住民。」車子轉上高速公路時,哈利這麼說。
「還真是什麼都瞞不過你,警官。」肯辛頓回答,瞥了一眼鏡子。
「在挪威,我們都叫你們澳洲黑人。」
肯辛頓直盯著後照鏡瞧。「真的?」
哈利開始覺得坐立難安。「呃,我的意思是,你的祖先顯然不是兩百多年前被英格蘭遣送到這裡的罪犯。」他想展現自己對這國家的歷史至少還有些許了解。
「沒錯,霍利。我的祖先比他們還早一點來到這裡。正確地說,是早四萬年才對。」
肯辛頓對鏡子露出笑容。哈利發誓,自己還是暫時閉嘴為妙。
「我懂了。叫我哈利就好。」
「沒問題,哈利。叫我安德魯。」
接下來的路上,都是安德魯在主導談話。他把哈利載到英皇十字區,一路上滔滔不絕。這裡是雪梨的紅燈區與毒品交易中心,其餘見不得光的交易,也大多在此進行。每一件醜聞,似乎都會與這平方公里內的某間旅館或脫衣舞俱樂部扯上關係。
「我們到了。」安德魯突然說,把車停在路邊,跳下車去,從後車廂拿出哈利的行李箱。
「明天見。」安德魯說完,立即開車離去。隨著痠痛感回來,就連時差也開始發揮作用。哈利與他的行李箱孤伶伶地待在一座人口數約莫與挪威一樣多的城市裡,站在外觀豪華的新月飯店外頭。飯店名字印在大門的三星級標記旁。奧斯陸警察局長對下屬出差時的住宿安排一向以吝嗇聞名,但或許這次不算太糟。哈利心想,這飯店肯定有什麼公務員折扣,八成還安排了最小的房間。
的確如此。
2 南岬公園
哈利小心地敲了敲薩里山重案組主管辦公室的門。
「進來。」裡頭有人大聲回答。
一名身材高壯、挺著大肚子的男子,站在橡木辦公桌後方窗前,像是想刻意讓人留下印象。稀疏的頭髮遮不住他的灰白粗眉,但眼睛周圍的皺紋還是能看得出他在微笑。
「我是挪威奧斯陸的哈利.『霍利』,長官。」
「坐,哈利。你看起來跟這個天殺的早上實在配極了。我希望你還沒跟緝毒組的小伙子打過照面。」尼爾.麥考梅大笑一聲。
「時差。我早上四點就醒了,長官。」哈利解釋。
「當然,只是我們內部的玩笑話而已。幾年前這裡有樁出名的瀆職案,十個警員被定罪,除此之外,他們還賣毒品──互相賣給對方。他們之所以受到懷疑,是因為其中兩個人總是隨時待命。不開玩笑,真的是隨時。」他一臉滿足地笑著,戴上眼鏡,輕敲著面前的文件。
「所以你是被派來協助調查英格.霍爾特的謀殺案。她是領有澳洲工作證的挪威公民,一頭金髮,照片上看起來很漂亮。二十三歲,對嗎?」
哈利點頭。麥考梅開始嚴肅起來了。
「漁夫在華生灣的海邊發現她,說得準確點,是在南岬公園裡。屍體半裸,從傷痕來看,是遭到先姦後殺,但沒發現精液。她在當晚遇害後被載到公園,扔下懸崖。」
他一臉不悅。
「她躺在岩石之間,直到讓人發現為止。要是天氣稍微差些,早就被浪沖走了。就跟我說的一樣,由於她的陰道跟剖開的魚一樣從中劃破,海水又沖得一乾二淨,所以沒能找到精液,也沒有任何指紋,就算有大概推估的死亡時間……」麥考梅拿下眼鏡,揉了揉臉。「但也找不到凶手。你打算怎麼處理這件該死的案子,霍利先生?」
哈利正要回答便被打斷。
「你要做的,就是在旁邊仔細看我們怎麼逮到這個混蛋。告訴那些挪威記者,我們配合得有多天衣無縫──確保我們不會冒犯到挪威大使館或死者親屬,除此之外,就是好好放鬆一下,寄一兩張明信片給你親愛的警察局長。對了,她還好嗎?」
「就我所知還不錯。」
「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想她應該有指示你要怎麼做吧?」
「講了一些。我是來參與調查──」
「好極了。把這些全忘掉。新規則如下。第一條:從現在開始,聽我命令行事,只准聽我的。第二條:在我沒指示以前,你什麼也不准做。第三條:就算只有一根腳趾越界,你也得給我搭上第一班飛機回去。」
他說這些話時面帶微笑,但訊息卻十分明確:把爪子收起來,在旁邊看著就好。或許他應該帶著泳具與相機來才對。
「我聽到消息說,英格.霍爾特是挪威的電視明星?」
「不算大明星,長官。她在幾年前主持過兒童節目。但我想在這件事發生前,早就沒人記得她了。」
「嗯,我得說,你們的報紙想把這樁謀殺案炒作起來。有幾間媒體已經派人來了。我們給了他們所有資訊,不過沒什麼重要線索,所以他們很快就會覺得無聊,接著打包回家。他們不知道你在這裡。我們有保姆管著他們,所以你不用和他們打交道。」
「感激不盡,長官。」哈利說,也真心這麼覺得。一想到有群氣喘吁吁的挪威記者在他身後探頭探腦,就讓人覺得煩心。
「好了,霍利,我就老實告訴你我們的狀況吧。我得到明確的指示,說雪梨所有市議員都希望能儘早破案。就跟平常一樣,全跟錢與政治有關。」
「錢?」
「這麼說吧,我們預估雪梨今年的失業率會攀升到百分之十以上,所以這座城市需要每一分能從遊客身上賺來的錢。我們就要拿下二○○○年奧運的主辦權了,到時會有很多北歐觀光客。而謀殺案,尤其是還沒偵破的那種,可不是什麼好廣告,所以得拼盡全力才行。偵查這件案子的小組成員有四名警探,外加優先分配的警方資源──包括所有的電腦、法醫、鑑識人員等等。」
麥考梅抽出一張紙,邊看邊皺眉。
「其實你應該是要與威金斯一組的,但既然你都特別選了肯辛頓,我也沒理由拒絕你的請求。」
「長官,據我所知,我並沒有──」
「肯辛頓是個好人。這裡可沒有太多原住民警員能爬到他這個位置。」
「真的?」
麥考梅聳肩。「事情就這麼定了。好了,哈利,如果還有什麼事的話,就再來找我。還有問題嗎?」
「呃,有個禮節方面的問題,長官。我不確定『長官』是不是這裡對上級的正確稱呼,還是這麼叫會有點……」
「正式?古板?對,或許是吧。不過我喜歡。這個稱呼提醒了我,我才是這個部門的老大。」麥考梅大笑出聲,用足以捏斷手骨的握手結束了會面。
「一月是澳洲的旅遊旺季。」他們在環形碼頭周圍壅塞的車陣中緩慢前進時,安德魯這麼解釋。
「每個人都來這裡看雪梨歌劇院,搭船繞港口一圈,欣賞一下邦代海灘上的女人。只可惜你還得工作。」
哈利搖頭。「沒關係。我一想到那些敲遊客竹槓的地方就會大冒冷汗。」
他們開著豐田汽車穿出車陣,抵達新南頭路,往東朝華生灣加速而去。
「雪梨東區跟倫敦東區有點不同,」安德魯在連續經過兩間精品店時解釋。「這一區叫德寶灣,我們都說是『多寶灣』。」
「英格.霍爾特住在這裡?」
「她跟男友在新鎮住了一陣子,分手後則搬到格里布的一間小套房。」
「男友?」
安德魯聳肩。「她男友是澳洲人,一個電腦工程師,兩年前她來這裡度假時認識的。案發當晚他有不在場證明,也不像是會殺人的人。不過誰知道呢?」
他們在南岬公園下方停車。這裡是雪梨眾多自然園區之一,需要登上陡峭石階才能抵達高處的瞭望區,北邊是華生灣,東邊則是太平洋。他們打開車門,熱氣襲面而來。安德魯戴上一副大墨鏡,讓哈利聯想到色情行業的人。不知為何,這位澳洲同事今天身穿緊身西裝。他搖搖晃晃地登上前方小徑,通往瞭望區,讓哈利覺得這名肩膀厚實的黑人看起來有些滑稽。
哈利環顧四周。西邊可以看見市中心的港灣大橋,北邊則是華生灣的海灘與眾多遊艇,再往遠一點,則是位於海灣北邊郊區,一片翠綠的曼利鎮。至於東方彎曲的地平線,則盡是深淺不一的藍色海浪。他們面前的陡峭懸崖,截斷了海水漫長的旅途,在岩石間發出如同雷鳴般的海濤聲。
哈利可以感覺到汗水順著肩胛骨之間流下。熱氣讓他起了雞皮疙瘩。
「你可以從這裡看見太平洋,哈利。再過去一千兩百哩,則是下一站的紐西蘭。」安德魯說,在懸崖邊緣吐了一口口水。他們看著那團口水往下落,直至被風吹散。
「還好她是死後遭人拋下去的。」他說。「她肯定在掉下去的過程中不斷撞到崖壁。她被發現時,屍體上有不少地方被扯掉了一大塊肉。」
「她被發現時已經死了多久?」
安德魯做了個鬼臉。「法醫說是四十八小時,不過呢……」
他做了個喝酒的手勢。哈利點點頭。那法醫顯然有個乾渴的靈魂。
「你之所以會懷疑,是因為這數字太剛好了?」
「她是星期五早上讓人發現的,所以我們不妨就說她是星期三晚上的某個時候遇害的好了。」
「這裡有任何線索嗎?」
「就跟你看到的一樣,車子可以停在下面,晚上沒有燈光,也比較冷清,因此沒有任何目擊者通報,說真的,我們也沒盼望這點。」
「那我們現在要幹嘛?」
「現在呢,就照著老闆的吩咐做,找間餐廳吃飯,花點警方的招待費。畢竟你可是方圓一千兩百哩以內位階最高的挪威警方代表呢。」
安德魯與哈利坐在一張鋪著白布的餐桌前。道爾餐廳位於華生灣盡頭,與海洋之間僅隔著一小片沙灘。
「美得誇張,對吧?」安德魯說。
「就跟風景明信片一樣。」一個小男孩與一個小女孩在前方沙灘堆著沙堡,背景則是深藍大海、遠方繁茂的綠色山丘,以及雪梨引以為傲的天際線。
哈利選了扇貝與塔斯馬尼亞鱒魚,安德魯則選了澳洲才有的一種比目魚,因此哈利自然未曾聽過這種魚的名字。安德魯點了一瓶蘿絲蔓夏多內白酒。「這酒跟這頓飯不太配,不過是白酒,很好喝,而且正好符合預算。」當他聽見哈利說自己不喝酒時,表情有些驚訝。
「宗教緣故?」
「不是,與這無關。」哈利說。
安德魯告訴哈利,道爾是間家族經營的老牌餐廳,公認是雪梨數一數二的。現在正值旺季,店內人滿為患,哈利猜想,這就是為什麼這裡的服務生很少與客人眼神交會的原因。
「這裡的服務生就跟冥王星一樣,」安德魯說。「全都繞著軌道跑,每隔二十年才出現一次,而且就算出現,也不可能用肉眼觀測得到。」
但哈利並未不悅,只是朝後靠在椅背上,心滿意足地吐了口氣。「不過他們的食物很棒。」他說。「所以這解釋了你為什麼會穿成這樣。」
「對了一半。你也看得出來,這裡沒有規定要穿成這樣。不過就我來說,最好還是別穿著牛仔褲與T恤來這種地方。由於外表的關係,我得要精心打扮一番才行。」
「什麼意思?」
安德魯看著哈利。「在這個國家,原住民的地位不高,說不定你自己早就感覺到了。多年以來,白種人始終一再強調原住民的酗酒與犯罪問題。」
哈利認真聽著。
「他們覺得問題出在我們的基因。有個人是這麼寫的:『所有原住民都極為擅長用空心吹管搞出各種非法勾當,也就是他們稱為迪吉里杜管的東西。』。這個國家自吹自擂,說他們把不同文化融合成一個具有凝聚性的社會。但他們凝聚了哪些人?這是個問題還是優點,你得自行判斷,本地人是看不出來的。
「在澳洲,原住民完全被摒除在社交活動之外,只有在選舉辯論會時,才會有人假裝關心原住民的利益與文化。澳洲人會花錢買原住民的藝術品,掛在家中牆上,以便做做表面工夫。不過,提到領取失業救濟金、自殺人口與監獄囚犯的話,我們這些黑皮膚同胞絕對是其中的代表族群。如果你是原住民,在監獄中度過餘生的機率,是其餘澳洲種族的二十六倍。好好品味一下吧,哈利。」
安德魯喝完剩下的酒,哈利則細細品味。事實上,這可能是他三十二年的生命中嚐過最棒的魚類料理。
「當然,在澳洲有種族偏見的人,並不比其他國家多。畢竟,我們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家,人民來自世界各地。這只不過代表當你想上餐廳時,換上一身西裝,絕對比惹上麻煩要來得划算。」
哈利再度點頭,不再談論這個話題。
「英格.霍爾特在一間酒吧工作,對嗎?」
「對。奧伯利酒吧,就在帕丁頓區的牛津街上。我想我們今晚可以過去看看。」
「為什麼不現在去?」哈利已經閒得不耐煩了。
「因為我們得先去跟她的房東打聲招呼。」
冥王星不請自來地出現在蒼穹之中。